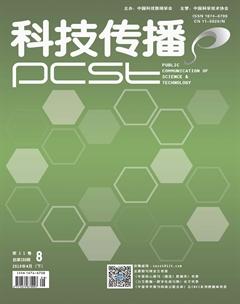“興觀群怨”:文化類原創綜藝節目的審美價值追求與社會功能
王家駒
摘 要 伴隨社會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顯著改善,在此背景下,他們對精神生活方面的追求日漸增多,尤其是能夠豐富他們日常生活的原創綜藝節目。更是成為其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文化類原創綜藝節目當中,不僅蘊含著豐富的情緒、戲劇因素,而且還充滿著審美價值,將其加入到社會架構中,還有著一定的社會功能,因此,其綜合價值功能突出。本文以《朗讀者》為例,分別從“興”“觀”“群”“怨”等角度,探討文化類原創綜藝節目當中所蘊藏的審美價值與社會功能,望能借此論述,為此領域研究有所借鑒。
關鍵詞 綜藝節目;文化類;審美價值;社會功能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9)233-0084-02
“不管是什么內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視角,電視上的一切都是為了給我們提供娛樂。[ 1 ] 1 0 6”大眾消費文化的娛樂化特征在電視綜藝節目中表現得更為明顯。緣于收視率、點擊量的考量,娛樂似乎成為眾多電視綜藝節目唯一的追求。或花費高額版權費引進國外綜藝節目,或靠制造花邊新聞,爆料緋聞提高關注度,或靠扮丑裝傻、懟名人博得觀眾一笑,片面追求娛樂化,造成了許多電視綜藝節目嚴重的同質化、低俗化的傾向。“電視是我們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的方式[2]112”。
隨著《中國詩詞大會》《朗讀者》等一批文化類原創電視綜藝節目的誕生并熱播,顯現出中國電視綜藝節目作為中國電視文藝的一大類別所應有的審美價值追求及其強大的社會功能,受到了業界和學界的普遍關注和討論。那么,中國電視綜藝節目應追求怎樣的審美價值,它們的社會功能又體現在哪里?
孔子在《論語·陽貨》中這樣談到過《詩》的作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興”是對藝術欣賞中美感心理特點的分析,“觀、群、怨”是表述藝術的社會作用。“興觀群怨”說認為藝術欣賞與構建和諧社會、加強民族凝聚力之間存在必然聯系。本文以《朗讀者》為例,結合“興觀群怨”說的理論,對文化類原創電視節目的審美價值追求和社會功能,展開分析和討論。
1 “興”:電視綜藝的審美特性
對于“興”,漢代孔安國的注解是:“引譬連類”;宋代朱熹的注解是:“感發志意”[2]50;清代王夫之的理解是:“興者,性之生乎氣者也”[2]51,結合三人的解釋就是,藝術作品通過藝術形象使觀賞者產生聯想和想象,從而對欣賞者起到激勵精神、凈化靈魂和升華心靈的作用。“興”不僅描述了藝術欣賞的美感特征,而且闡釋了現實生活、藝術形象和欣賞主體之間的審美關系以及審美主體的心理內容。
在“興、觀、群、怨”中,孔子把“興”放在首位,足以見出他對“興”的重視。清代王夫之也認識到“興”的重要性:“詩言志,歌詠言,非志即為詩,言即為歌也,或可以興,或不可以興,其樞機在此。”這就把“興”看成了詩、歌(藝術作品)之所以為詩、歌(藝術作品)的判斷標準[2]52。
“興”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觀、群、怨”的基礎,它規定了“觀、群、怨”是基于審美欣賞而生發的。辨別“興”的重要性具有現實意義。它強調了電視綜藝節目的審美性、藝術性特征,并進一步指出了電視綜藝節目的審美價值取向以及實現社會功能的路徑。
《朗讀者》作為國內文化類原創綜藝節目,帶有中國傳統文化基因,具有典型的中國式的審美價值追求。
意境論強調“象外之象”和“境生于象外”。《朗讀者》中,朗讀嘉賓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故事中主人公的形象就是具體可感“象”,這“象”與嘉賓所講述故事中的其情、其景共同引發了觀眾的聯想,從而在觀眾心中形成了與自己的某些生活和情感經歷關聯的、觸發某種情感的“象外之境”和“象外之象”。隨后的嘉賓朗讀文學作品時,觀眾心中的“象外之境”和“象外之象”又與文學作品中的具體的“象”相交織、渾融,產生更加深層的“象外之境”和“象外之象”。中國傳統藝術的審美觀照方式帶有“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要窺見整個宇宙、歷史、人生的奧秘[2]224”,“于有限見到無限,又于無限回歸有限[ 3 ] 4”的美學特點。通過“象外之境”與“象外之象”的兩次生成,觀眾從節目中所獲得的不僅僅是通過了解明星的個人軼事而得到的娛樂滿足,而是對時代、對生命、對生活的深層思考,產生“在俗世塵緣中把握和流連生命的一片真情[3]252”的渴望。
“朗讀是傳播文字,而人則是展現生命,將值得尊重的生命和值得關注的文字完美結合就是我們的《朗讀者》。”這是對人的個體生命意蘊的追尋和對人生藝術化的向往。對人的生命意蘊的追尋是為了“使現實的人生啟示著深一層的意義和美(宗白華語)[3]250”。人生的藝術化在于在世俗的生活中,發現生活的情趣,看到生活的本真,自由地、“詩意地棲居”。《朗讀者》的審美價值追求帶有濃濃的人文情懷,旨在為平凡、普通的生活注入蓬勃的生機。“觀、群、怨”也正是在此審美價值追求的前提下,形成了具有審美屬性的認識、文化聚合和情感表達三大社會功能。
2 “觀”:電視綜藝的審美認識功能
對于“觀”,東漢鄭玄的解釋是“觀風俗之盛衰”,宋代朱熹的解釋是“考見得失”[2]50。二人都強調藝術的認識功能,但主要還是從社會教化和政治制度的角度來闡釋“觀”,而實際上,《詩經》中的內容很難用社會教化和政治制度去概括。
“觀風俗之盛衰”,“觀”就是觀看、了解的意思,“風俗”從廣義上來理解,就是現實生活,是“天地萬物之情狀”。“盛衰”不是“盛”和“衰”兩種事物存在的境況,而是從“盛”到“衰”,或從“衰”到“盛”這一事物發展過程的表述。“觀風俗之盛衰”,就是對事物的全面的觀察、了解。
“考見得失”,也不能單從國家政治治理的角度來闡釋“觀”。姚斯指出:“閱讀經驗能使人們從一種日常生活的慣性、偏見和困境中解放出來,在接受活動中,藝術給予人們一種對世界的全新感覺。從宗教和社會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使他們看到尚未實現的可能性,為他們開辟新的愿望、要求和目標,為他們打開未來經驗之途。”[ 4 ]因此,“考見得失”是在“觀風俗之盛衰”的對事物全面認知的基礎上,而進入到的更新、更高程度的審美認識。
《朗讀者》首先具有對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的感性認識的功能。這一點主要是通過朗讀嘉賓所講述的故事來實現。朗讀嘉賓所講述的,有些是對重大事件的見證;有些是親人間的悲歡離合;有些是成長中的愛恨情仇;有些是生活中的溫情片刻;有些是逆境中的不屈堅持,有些是特殊的生活和工作經歷……這些內容已經形成了對世界、對生活、對人生的豐富的描述。
其次,《朗讀者》具有對現實生活審美認識的功能。朗讀嘉賓所講述的內容很多都已是塵封中的記憶,講述者之所以在多年后還能把它們回憶起來并且清晰的表述出來,說明這些往事在當時就已經觸動了講述者的心弦,并且在歷經人生的起伏和曲折當中,在講述者有意識的對生活、人生進行理性的不斷感悟中,這些往事都可能作為“復現的聯想”成為感性材料的一部分。在節目中,嘉賓所講述的這些往事,都承載了講述者對人生價值、生活真諦的理性思考。《朗讀者》中,白巖松說到自己在家鄉舉辦了小型婚禮后,將要離開家時,母親在做飯時的悄然淚下,其景其情描繪了一個獨自把兩個兒子拉扯大,當兒子離開時,卻默默吞咽著不舍和牽掛的母親形象。這個母親已經不是白巖松一個人的母親,她是全天下所有游子的母親。
情感與真實的統一,感性與理性的統一,個性與共性的統一,這是藝術形象的特點。因此,白巖松所描繪的自己母親的形象,已經具有了藝術性的效果。它與隨后的文學作品的朗讀同樣都具有審美認識的功能。
3 “群”:電視綜藝的文化聚合功能
對于“群”,漢代孔安國的解釋是“群居相切磋”,宋代朱熹的解釋是“和而不流”[2]51,都是主張社會人群通過藝術進行情感、思想的交流,從而形成社會的和諧秩序。“群”強調了藝術的社會功能。
“群”是指人群、群體。群體的劃分標準是多樣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地域、文化、民族、血緣甚至是經歷,都可以劃分出不同的社會群體類別。群體成員通過藝術作品實現審美信息的交換,從而形成某種共識,加強群體成員之間的凝聚力。
《朗讀者》通過制造群體成員共有的文化、價值、記憶、民族精神等方面的認同,實現群體的凝聚力。
2018年7月21日播出的《朗讀者》中,主持人董卿的開場語是這樣說的:“痛苦對我們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一語道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中國古代文人有多少沉郁頓挫的痛,就有多少達觀不屈逆境重生……”。
2018年8月4日播出的《朗讀者》中,董卿的開場語中的一句話:“……故鄉,是清明的那柱香;是中秋的那輪月;是春運時的那張車票……”。周文王、孔仲尼是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兩座豐碑;“達觀不屈逆境重生”是“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南西北風”的民族精神;清明的香、中秋的月、春運的車票藏在每個中國人的記憶中,它們是中國人親情、鄉情的表征。《朗讀者》正是通過對各種意象的情感性表達,不斷地喚起記憶,制造認同,構成了漢文化群體的共同文化想象,從而固化中華民族的整體凝聚力。
4 “怨”:電視綜藝的情感表達功能
對于“怨”,孔安國的解釋是:“怨刺上政”[2]51,是指對統治者不滿而怨恨諷刺。這實際上是對“怨”的狹義解讀。“怨”有很多種,如國運之怨、個人命運之怨、棄婦之怨等。從廣義來講,凡是對社會生活表達的帶有否定性的情感都可以稱之為“怨”。但是“怨”不是恨,并非是一味的表達不滿,發泄負面情緒。而是通過對憤怒、憂郁情緒的美的釋放,從而回歸到積極向上的人生追求上去。因此,葉朗教授把“怨”的外延進一步擴大,認為“可以怨”,就是“詩歌可以引起欣賞者對于社會生活的一種情感態度[2]51”,強調了藝術的情感性特征。
《朗讀者》在情感表達和情感宣泄上具有偏于顯、偏于詩意的情感升華的特點。
所謂“偏于顯”,是指在《朗讀者》中,通過朗讀嘉賓講述人生過往中的辛酸苦樂時,其情感外顯而熾熱。與《詩詞大會》中學者們的充滿理性色彩的講解不同,《朗讀者》中的朗讀嘉賓所講述的自己的經歷,本身就是一種感性的、情感的體驗。它們在多年以后被回憶、講述出來時,仍然伴隨著講述者的濃烈的情感。如在俞敏洪在回憶自己上高考補習班,母親與他的一番對話時,情緒依然難以控制;在回憶初入大學時,舍友投來的不屑的目光,仍然讓他耿耿于懷。
所謂“詩意的情感升華”,是指《朗讀者》中的“朗讀嘉賓訪談+嘉賓朗讀”的模式設置使嘉賓的個人情感體驗上升到具有可普遍傳達的共情。朗讀嘉賓的訪談,是在類似會客廳的具有個人屬性的場景中進行,嘉賓的對自己人生經歷的講述帶有濃烈的個人化情感的痕跡。而在隨后嘉賓朗讀環節中,嘉賓的個人情感化入了文學作品的意象之中,文學作品對情感的詩意表達升華了嘉賓的個人情感,更易于觀眾在心中產生共鳴。
5 結論
“興觀群怨”并非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聯系的整體。王夫之解釋說:“于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于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群者而怨,怨而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摯。[2]51”只有在堅持節目“興”的審美特性的前提下,綜合實現其審美認識功能、文化聚合功能、情感表達功能,才能把握正確的審美價值追求方向,體現強大的社會功能。這不僅是文化類原創電視綜藝節目的制勝之道,而且也是所有電視綜藝節目避免過度娛樂化、低俗化的一劑良藥。
參考文獻
[1]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06.
[2]葉朗.中國美學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50——52,224.
[3]凌繼堯.美學十五講[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4,250,252.
[4]胡經之,王岳川.文藝學美學方法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