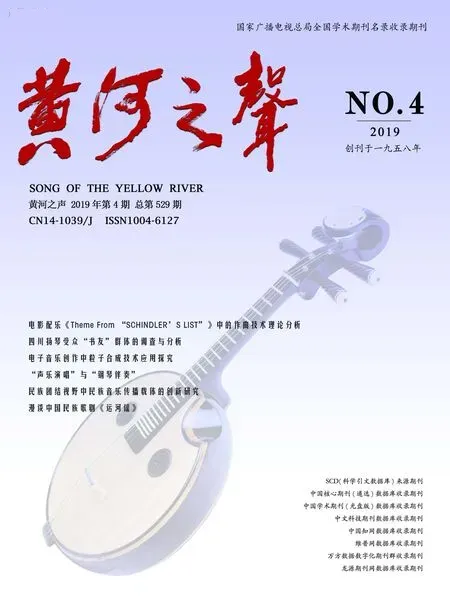四川揚琴受眾“書友”群體的調查與分析*
彭 勇
(四川音樂學院,四川 成都 610021)
揚琴作為一件舶來品,在歷經了幾百年歲月的洗禮和沉淀后,與中國傳統音樂完美接洽,成為了國內許多傳統曲種的伴奏樂器,并逐漸發展成為獨奏樂器。由此可知,揚琴音樂有著極強的生存力和影響力,其獨特的魅力使得它在國內發展出了多種各具特色的揚琴音樂。其中,四川揚琴,就是揚琴音樂的一種。四川揚琴,屬民間音樂中說唱音樂的一個曲種,因以揚琴為主奏樂器,因此而得名四川揚琴,它是國內揚琴音樂中最有影響力的曲種之一。
作為四川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傳統曲藝形式之一,四川揚琴以其獨特的表演藝術魅力而深得人們的喜愛。這種形成于清代的傳統說唱形式,從20世紀初伊始,在成都、重慶等地風靡開來,成都各地的茶館、劇場幾乎是場場爆滿,人們對于四川揚琴的喜愛程度相比眾多四川當地的傳統音樂形式而言,從某種意義來說,已經占據頭名,而更有人認為,四川揚琴甚至成了四川本土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傳統曲種,而過去人們則普遍認為這個頭名應該是非川劇莫屬。
自2017年開始,筆者有機會開始接觸到四川揚琴,并開始以四川揚琴為研究對象,長期進行田野作業,使得筆者深深感受到了四川揚琴音樂獨特的魅力,更為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發現四川揚琴音樂的受眾群體幾乎都為六十歲及以上的老年人群。在筆者看來,這群人不單單是簡單的聽眾,更是四川揚琴音樂幾十年來發展歷程的見證者,他們可以熟知臺上每一個演員的每一次表演中的微小的錯誤,他們也知道對于四川揚琴音樂來說,怎樣的演繹才能真正表達出四川揚琴的“靈魂”,所以筆者常常看到臺上演員表演完后,都會去跟臺下的一些聽眾交流,而實際上,他們是去接受“批評”的。在筆者的研究中,將這一類型的人稱為四川揚琴的“書友”,本課題主要就是針對這一“書友”群體的調查與分析。
對于四川揚琴而言,清楚其舞臺文化也即是演員與聽眾之間的關系,是真正了解四川揚琴的重要途徑之一。并通過在與其中某些資深聽眾“書友”的交流中,更是了解到了四川揚琴獨特的魅力。但,就目前的四川揚琴生存狀況而言,有些讓人“不滿足”,也有一絲絲的遺憾。不過,在當今如此浮躁的社會狀況下,能有一群靜心聆聽揚琴的人群,著實是四川揚琴音樂不幸中的大幸。所以,對于四川揚琴音樂的研究,必然需要全面的了解其資深受眾“書友”群體,了解其資深受眾“書友”的審美觀念的前提下,才能更好的理解四川揚琴音樂。
一、四川揚琴音樂研究現狀及生存狀態
(一)四川揚琴音樂的研究現狀
作為四川地區著名的傳統說唱形式,四川揚琴在學術界所受重視程度是與其地位不匹配的,與京劇、昆劇、京韻大鼓等樂種相比,學術界對于四川揚琴的關注程度遠遠不夠。國內學者對于四川揚琴的研究,除了肖前林在上個世紀60年代的著作《四川揚琴音樂》外,其它研究成果均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80年代初至21世紀初,研究成果相對較少;進入21世紀以來,關于四川揚琴音樂的研究開始增多。綜觀過去三十年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川揚琴的源流、唱腔、曲牌、律制、流派、曲目等方面的研究,也即是主要從四川揚琴音樂本體來研究四川揚琴。不過,僅從四川揚琴的音樂本體來理解四川揚琴,是遠遠不夠的。國外關于四川揚琴音樂的研究,經過筆者的文獻搜索,目前尚未發現國外學者研究四川揚琴音樂,關于揚琴的研究倒是屢見不鮮。因此,就關于四川揚琴的國內外研究現狀而言,還是以國內學者的研究為主,國外學者較少涉及。所以,在此一領域還有許多的工作需要做,也需要更多的學者進入到該領域,從不同的視角來更好的研究四川揚琴音樂。由此可見,過去學者對于四川揚琴音樂受眾的研究缺乏足夠的重視程度,而事實上,音樂的接受者對于音樂本體的研究來說,是不能缺少的研究因素。
(二)四川揚琴音樂的生存狀態
四川揚琴的生存空間,主要在川渝一帶,在四川地區,從早期的慈惠堂開始,就培養出了大量的盲藝人,而這些盲藝人又培養出了一批優質的學生,像傅兵、康先洪、王鐵軍等人。除了慈惠堂,由李德才先生創立的“德派”,也培養出了如劉時燕、徐述等四川揚琴的傳承人,由此可見,四川揚琴早期的藝人在數量上是很龐大的,而如此多的藝人,恰好也反映了當時的市場需求。據一些老觀眾說,“原來成都這邊好多茶館,到處都在唱揚琴,熱鬧得很”,這也證實了當時四川揚琴在成都地區確實很受歡迎。
而近些年來,在成都地區,目前還有揚琴演出的就只有大慈寺社區了,盡管有四川省曲藝研究院的人才培養與儲備,但四川揚琴的后勁始終有些不足,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缺少年輕演員,二是缺少聽眾。不過近幾年來,隨著非遺活動的開展,以及傳統進高校活動的實施,使得四川揚琴等相關傳統音樂形式更多的被人們所了解和認識,但這種認識和了解是很淺顯的,因為對于四川揚琴這樣“復雜”的音樂形式來說,如果不經過漫長時間的“浸泡”,是很難入門的,這也就使得四川揚琴很難被年輕人們所接受,而能夠接受的,只能是那些受多年熏陶的老一輩觀眾們。
經筆者在四川成都大慈寺社區一年多的田野考察來看,該社區每個星期表演一次揚琴,筆者初去時為每周四下午兩點至四點,后來改成了每周星期三下午兩點至四點。從演出人員來看,大多都是四川省曲藝研究院的演員,大多為老一輩的演員,偶爾有一兩個年輕演員,其中,有七至八名演員為常駐演員,其他演員不定時的會被安排過來演出。從每場演出的受眾上來看,除了少數音樂學院的學生會偶爾過來看一下,以及路邊的行人會偶爾進來拍個照片外,大多都是六七十歲的老觀眾,經過筆者這一年多的考察,這些老觀眾每次會坐在哪個位置筆者都已經了如指掌。除了大慈寺社區以外,經筆者多次與老觀眾聊天的詢問,目前成都地區再無四川揚琴的相關演出了,所以,大慈寺社區成了這些老觀眾每周翹首以盼的音樂日,所以每個星期都會看到這樣一種現象:一些步履蹣跚的老人多遠都要趕過來看,腿腳多不利索也不會阻擋他們看揚琴的熱情。由此可知,四川揚琴對于他們來說,早已成為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而筆者經常會問他們一個問題,“四川揚琴和四川清音哪個好聽的問題”,“他們都會告訴我說,都好聽,然后接著說,四川揚琴那個旋律啊,簡直太巴適了,就是聽了心里很舒服”。
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對于四川揚琴的傳承與發展而言,存在著巨大的阻礙和困難。四川揚琴在近十多年來的發展中,隨著老一輩演員和老一輩聽眾的漸漸離世,四川揚琴的市場正在急速縮減。一方面,四川揚琴的演出場所和演出場次都在近20年來快速減少;另一方面,四川揚琴的受眾也在不斷減少,而且其受眾老齡化嚴重,說得夸張一點,只要“走一名”老聽眾四川揚琴就又少了一名聽眾,且極少有新的聽眾加入,也極少有年輕的聽眾;第三,四川揚琴的演員目前也出現了斷代,老一輩的演員大多都七十好幾了,而中青年揚琴演員,卻少之又少,大多還不愿意從事這個行業,甚至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們不一定真正“能唱”。
筆者在長期的田野工作后,對大慈寺社區的受眾群體的男女比例、受眾年齡范圍、受眾職業、受眾聽琴年限以及受眾興趣范圍幾個方面分別做了一個簡單的數據統計,其中男女比例比較固定,筆者主要從剩下的幾個方面展開,統計結果如下:

一區間 二區間 三區間 四區間 五區間男女比例 5:1 5:1 5:1 5:1 5:1年齡范圍 20-40(2%)41-60(5%)61-70(40%)71-80(42%)81-90(11%)社會身份 教師(14%)行政(16%)管理(24%)個體(34%)其他(12%)聽琴年限 1-2(8%) 3-5(23%)6-10(29%)11-20(24%)21-50(16%)揚琴、清音、川劇、金錢板、車燈(10%)興趣范圍 揚琴(10%)揚琴、清音(35%)揚琴、清音、川劇(28%)揚琴、清音、川劇、金錢板(17%)
二、書友與“老師”:多重身份的統一
受眾研究是音樂研究的重要的一部分,要弄清某一音樂形式,就必須對其受眾有足夠全面的了解。對于四川揚琴音樂而言,它的資深受眾“書友”是我們必須了解的一個部分,因其受眾的特殊性,使得四川揚琴音樂的研究必須要涉及“受眾”研究,但就過去的學者關于四川揚琴音樂的研究而言,還未有學者關于資深聽眾“書友”這一群體進行研究,而本文筆者將要做的,正是對這一資深受眾“書友”的調查與分析,以此來更全面的認識四川揚琴。
(一)作為書友的資深聽眾
四川揚琴,也稱四川琴書,因其以揚琴為主要伴奏樂器,所以被稱為四川揚琴,是一種以說為主、以唱為輔、說唱相間的民間說唱藝術。[1]這里筆者的“書友”,就是指的四川揚琴的聽眾,之所以筆者稱之為書友,就是因為四川揚琴也被稱為四川琴書,是一種說書、唱書的形式,所以筆者稱其為“書友”。
這里的“書友”相比一般聽眾,是有所不同的,普通的聽眾只是純粹的娛樂,聽不聽揚琴都是隨著心情走的,很隨意,且對于四川揚琴的相關知識也沒有很清楚,也不關心四川揚琴的點點滴滴,如哪位老師收了個學生、哪位老師又去哪里演出了等等,他們都不關心。簡單說來,他們只是出于一種純粹的愛好而已。而“書友”,在四川揚琴的受眾群體中,已經算是四川揚琴的局內人了,他們對于四川揚琴的相關知識有很深的了解,能夠分辨臺上演員演唱水平的高低,也能夠清楚的知道每一個劇目的名稱,甚至是某一句說白或者唱詞他們都能夠清楚的記得,他們還偶爾會和身邊的人發表一下自己的意見和看法,會和自己的朋友談論相關演員的演唱,但一般不會主動去點評演員演唱的缺點,他們通常都會鼓勵和支持演員。這種人群在四川揚琴的聽眾當中,是占據絕大多數的。
筆者這里以筆者個人采訪過的一位阿姨來做為案例。這位阿姨讓筆者叫她陳阿姨,所以筆者也就沒有再問她的名字。陳阿姨同筆者一樣,除非有什么大事,不然每周都會去大慈寺社區聽揚琴,而且重點是,她每一次都會拍照,雖然拍得不多,有時候也會讓筆者幫她拍,然后會給筆者一些水果瓜子之類的作為答謝,然后她每次看完揚琴還要發朋友圈發表一下自己的心情。此外,她還同四川揚琴國家級傳承人劉時燕老師是很好的朋友,經常跟劉時燕老師一起出去散步游玩,同時,陳阿姨還特別喜歡字畫、書法,也很喜歡川劇等傳統音樂。陳阿姨現在是退休人員,以前是從事商業工作的,因為其工作單位在成都群眾藝術館附近,所以剛工作那時候,幾乎每天都有四川揚琴、清音、車燈、金錢板等相關演出,于是那時候就開始聽四川揚琴了,而經過筆者一年多來的觀察,筆者個人認為陳阿姨屬于此一類書友,因為她對于四川揚琴而言,不算貫通,但對于音樂本身的了解和演員的水平把握還是很有分寸的。
(二)作為“老師”的資深書友
作為“老師”的資深書友,主要是指一些資深級觀眾,他們往往是坐在臺下閉目養神,偶爾整一下眼,喝一口茶。他們多為退休的“文化人士”,有大學教授,有政府行政人員等等,這部分書友在整個四川揚琴聽眾群體當中是少數,他們對于四川揚琴的“喜愛”絕不僅僅是出于愛好。在筆者看來,在他們的心中,他們的肩上已經擔負起四川揚琴的一些責任了,比如四川揚琴音像資料的記錄與保存、四川揚琴的相關研究問題、四川揚琴青年演員的相關演唱等等方面,無論每周揚琴演出的當天是下雨還是天晴,無論他們腿腳有多么不利索,都是非來不可。可見四川揚琴對于他們而言,怎能用愛好來形容。
經筆者的考察,這一類型的書友往往在演員們的眼中都是很有地位的,因為他們知道的關于四川揚琴的東西,可能比一些演員知道的都還要多,他們不僅知道演員的某一句唱詞唱錯了,或者旋律唱錯了,或者是板眼弄錯了,他們甚至能唱揚琴,而筆者也是親眼見證這些“老師”跟演員一起演唱揚琴的,雖未在舞臺上同臺,但是臺下還是忍不住露了幾手。不過,這都不是最重要的,在筆者看來,最重要的是,這類人群的貢獻還在于他們能夠三言兩語說出每個演員的優缺點,而且能夠把四川揚琴的前世今生說個“三天三夜”,諸多年輕演員由于表演經驗不足,每次演出完后,第一件事,不是去問自己的老師今天唱得怎么樣,而是去問這些資深書友,而往往,這些書友也會很主動就說出他們今天哪里唱得好與不好,三言兩語就能把優缺點表達得清清楚楚。筆者也經常去跟他們請教相關問題,有時候也會問他們某個年輕演員唱得怎么樣,他會說,“味道還差了點,沒得啥子韻味”。這一人群,在大慈寺社區,往往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也許是不成文的規定,每次無論他們早來晚來,他們的位置基本上都沒人去坐(也不排除有第一次來的聽眾不知情所以會去坐)。而最讓筆者動容的就是,很多年輕的演員唱完后,都會自覺地蹲到“老師”們的旁邊聽聽他們的意見和看法,而這些老人也都會毫無保留的提出他們的表揚與批評。所以,在筆者看來,四川揚琴的發展是無論如何也離不開這些資深聽眾的,離了他們,也就再沒有四川揚琴的存在了。
筆者這里以筆者采訪過的彭家齊爺爺為案例來予以說明。從筆者去年九月份第一次去大慈寺社區開始,筆者就注意到了一個完全與眾不同的老爺爺,他坐姿端正,拿著很專業的攝影設備,時而拍一下某個演員,時而拍一下臺上的全景,每一場的演出,他幾乎都會錄像,換句話說,四川揚琴的音像資料,就目前來看,他那里無疑是最多的,也是最齊全的。而這個彭爺爺不僅僅是記錄,他還會把他拍好的照片打印出來免費送給演員們,也會將每一次的演出刻錄成光盤送給演員們。這位彭爺爺,以前是鐵路局的技術人員,改革開放前在錄音機上聽到李德才的演唱,便喜歡上了四川揚琴,而因為工作原因,不能全身心投入。退休后,才真正有時間全心聽揚琴,他對于四川揚琴的喜愛,用他自己的的話來說,“四川揚琴的音樂,那種律動感,給我的感覺就是猶如流動的泉水那般,十分優美,就是聽了覺得心里很舒服”,而彭爺爺更是能熟知每一個劇本甚至是每一句唱詞或者說白,有一次筆者親眼見證彭爺爺和四川揚琴省級傳承人康先洪老師一起在社區門口唱四川揚琴,唱詞竟然背得比康先洪老師還要熟悉,而且唱得很“到位”,就是有一點點的“羞澀”,因為畢竟不是演員。而彭爺爺也常常會去跟演員交流自己作為聽眾的心得,當然,更多的,是對年輕的演員提提自己的意見和看法。
三、接受美學視域下的四川揚琴受眾
四川揚琴在當下學界所受到的重視程度目前看來還遠遠不夠,像四川揚琴這樣一種具有地區代表意義的典型傳統音樂,應該得到更多“音樂學意義”的挖掘,而更重要的是,對于四川揚琴這樣一種傳統音樂形式,其受眾一直都被研究者們忽略,但事實上,我們應該知道的是,四川揚琴的受眾,乃至任何一種傳統音樂形式的受眾,都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因為,傳統音樂本身是以人為載體的,而這個載體,不僅僅是表演的人,更多的則是接受、聆聽和分享反饋的人,也即是我們一以貫之的“聽眾”、四川揚琴的“書友”。而這樣一種研究的形式或研究的觀念,在接受美學的核心觀念里,早已被提出,它又被稱為接收美學、接受理論或接受研究,誕生于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德國的康斯坦茨,以姚斯、伊塞爾為突出代表,是美學的一個分支流派,主要是針對文學研究而提出來的。
從接受美學的觀點來看,對于某一文學作品的研究絕不僅僅是去研究這部文學作品本身或者創作這部作品的作者,還應該對閱讀者加以研究,也即是應該包含創作者——作品——閱讀者三個部分的內容,應該將這三個部分看作同樣重要的部分,因為在接受美學奠基人姚斯看來,“在作者、作品和大眾的三角形中,大眾并不是被動的部分,并不僅僅是作為一種反應,相反,它自身就是歷史的一個能動構成。一部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如果沒有接受者的積極參與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只有通過讀者的傳遞過程,作品才進入一種連續性變化的經驗視野。在閱讀過程中,永遠不停地發生著從簡單接受到批評性的理解,從被動接受到主動接受,從認識的審美標準到超越以往的新的生產的轉換,才是完整的。”[2]而將這一美學觀念放到音樂的研究中,則應該體現為不僅僅是對創作者和作品本身以及演奏者的研究,還應該包含對于聽眾的研究,這同接受美學在文學作品中的用法相同,而過去的音樂研究中,大多的研究者關注的重心都在作曲家和作品本身,演奏者有少量學者會有所涉及,而關于受眾或者聽眾的研究,是鮮有案例的。我們應該意識到一個問題就是,對于傳統音樂乃至任何一種音樂形式而言,對于受眾的研究或許是我們認識音樂本身的另一種新的途徑,因為音樂作品總是寫給人聽的,不論是過去的人、現在的人、還是將來的人,總之,他們都是他們當下社會的人。
接受美學是從受眾出發、從接受出發,認為讀者在整個文學活動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讀者的接受不是被動的、消極的接受過程,而是一種主動的、積極的創作,沒有讀者能動的參與,文學作品是不完整的,只有經過讀者閱讀并接受了的作品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作品。[3]因此,從接受美學對于文學作品中讀者的定位來看,作為讀者的人群對于某一文學作品來說,有著同寫作者和作品本身同等重要的位置,我們決不能忽視讀者對于作品本身的反饋與思考。
近些年來,接受美學的相關觀念也逐漸被音樂學家所應用,如韓鐘恩教授的文章《對音樂分析的美學研究——并以“[Brahms Symphony No.1]何以給人美的感受、理解與判斷”為個案》一文,算是我國第一篇從人的審美接受角度談音樂分析的文章,作者認為“用審美判斷去連接現象與人本之間的關系,在合乎客觀規律的現象與合乎主觀目的的人本之間架設一座橋梁,使兩者通過人的審美判斷統一起來”。[4]文中雖未明確提到“接受美學”觀念,但其對于受眾者觀點的重視已經具有接受美學的研究意義了。上海音樂學院的鄒彥副教授,在2011年發表的文章《接受美學對音樂學研究的幾點啟示》中,就明確將接受美學的理論借鑒到音樂學的研究中,并提出相關的思考,他認為“在接受美學的理論中,文學作品的審美需要作者—藝術的成品—讀者三個階段;對于音樂作品的審美則需要在藝術的成品和聽者之間增加‘演奏者’這一環節。”[5]而事實上,接受美學帶給我們的思考,不僅僅是將受眾或者聽眾在音樂學研究中的重新定位,更是給我們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的思考,而我們同時也應該注意的是,盡管接受美學要求我們將受眾看作和創作者以及作品同等重要的位置,但我們依然需要在研究中把握好分寸,因為,畢竟音樂本體才是音樂的“魂”,接受美學的思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或許僅僅是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詮釋方式或者渠道。
對于四川揚琴音樂而言,我們一方面要加強對于音樂本體的研究,而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對四川揚琴的受眾有所研究,因為對于四川揚琴音樂而言,其生存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是依附于其受眾,他們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關系,兩者互為依存。對于音樂學的研究而言,從受眾的角度去了解四川揚琴,也是一個可以全方位了解四川揚琴音樂的一個有效的途徑,而這也是筆者在接下來的研究中所要嘗試去做的事情,因此,本文只是這個研究的一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