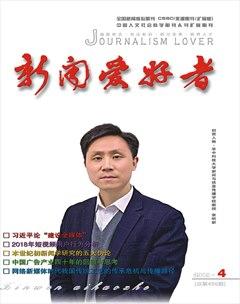后真相時代“新聞搭車”現象的成因及對策分析
邵超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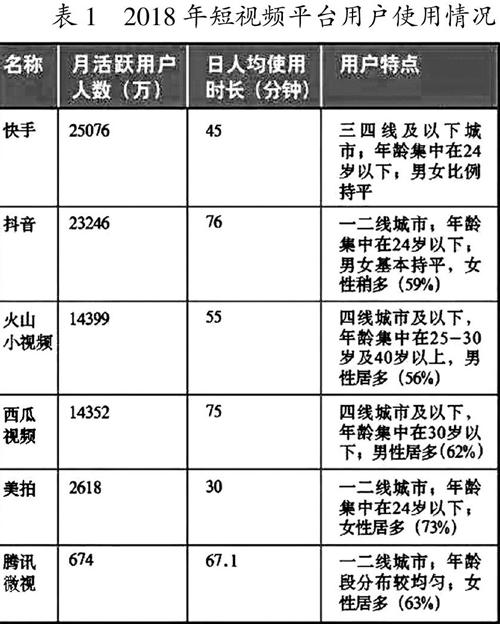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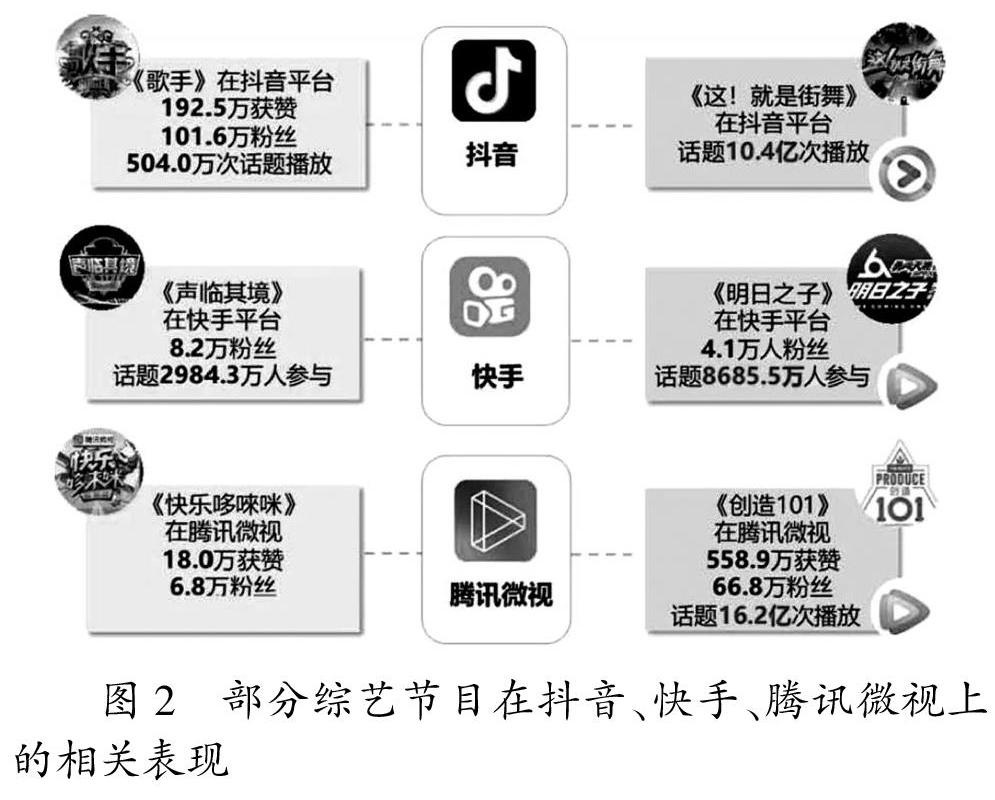
[摘要]重共鳴、輕真相,長情緒、短記憶的后真相時代,一件突發性事件可以在互聯網瞬間引爆輿論,在官方還未有所回應之前,一系列主體相似、內容相關的事件接連爆出,甚至引發二次輿論,新聞出現“搭車”現象。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媒體議程設置失焦和網絡受眾的不理性,造成后真相時代的“新聞搭車”現象頻發。而主體公信力下降、網絡民粹主義盛行輿論引導不力、議程失焦、網絡受眾缺乏理性,是“新聞搭車”現象形成的主要原因。要減少“新聞搭車”現象,必須從政府、媒體和公眾三個方面提出解決之道。
[關鍵詞]后真相;新聞搭車;原因分析;對策分析
一、后真相時代的“新聞搭車”:情緒感染大于客觀事實
“后真相”這個詞最早可追溯到1992年美國《國家》雜志上發表的一篇文章,文中批判了海灣戰爭政府操縱媒體,從而使美國大眾“生活在一個后真相的世界”。2004年,美國作家凱伊斯提出了“后真相時代”(Post-TruthEra)的概念,他認為人類社會不存在真實與謊言的清晰界限。介于真實與謊言之間,存在著一種情緒化的第三種現實。2016年11月,英國《牛津詞典》把“后真相”(post-truth)定為2016年年度詞匯,意為“陳述客觀事實對民意的影響力弱于訴諸情感和個人信念的情況”。后真相時代的信息傳播已經演變為一種情緒傳播,情感正取代理智逐漸成為信息內容本身。與此同時,真相在不斷地被掩蓋、消解、忽視,但它依舊存在,只是不再那么重要,因為人們所追求的是一種可以為情感所接受的“真相”。
后真相時代形成的一個主要背景便是新媒體技術革新所帶來的“傳受平權”。當一個社會事件發生,真相往往尚未浮出水面,官方還未給出明確回應,而公眾已經在社交平臺通過發文討論、點贊回復進行情緒化表達,將輿論推向高潮。這時主題相類似、與主體相關聯的新舊大小事件便如同磁鐵急速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新聞搭車”現象。喻國明教授較早指出此類現象為“新聞搭車”,即“當公眾把注意力集中到主體新聞事件時,與此地域相關的、以往難以受關注的問題集中爆發出現在公眾視野,舉報人會趁社會注意力和各方面力量聚集的時刻,尋求解決自身問題”吧。
二、“新聞搭車”現象的原因分析
(一)政府公信力下降,網絡民粹主義盛行
如果新聞當事人身居要位或身份敏感(如政府官員、演藝人員、網紅、教育從業者等),那么,他們的被關注度就要高于其他人。當媒體新聞內容具有較強的新聞價值和刺激性,特別是新聞涉及官員受賄、醫療事故、學校教育等與價值觀念社會管理、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時,一些網絡上不起眼的細節也能立即打開無法預知的后果的大門,從而引發大量的關注和高熱度的話題討論,掀起一波又一波輿情浪潮。在新聞主體事件發生后,新聞真相的水落石出往往需要時間,政府為了控制輿論發展,通常會采取刪帖、屏蔽和撤熱搜等強制性手段來打造輿論的“沉寂化”。根據回旋鏢效應,政府越是抑制,大眾挖掘真相的心情就越迫切。輿情長期的累積,容易使輿論從事件本身轉移到對政府發言的不信任與質疑,從而對政府的公信力產生影響,使得公信力陷入“塔西佗陷阱”。
當前,中國正處于社會結構轉型期,“民粹主義話語強占,正是看到輿論形成過程的復雜性,利用信息傳播中所謂的破窗效應,通過爆料、過激言論、假消息假事件等引起網民關注,從而控制輿論走向”。當輿情不受控或受到故意引導時,“新聞搭車”的概率便會大大提升。
(二)媒體輿論引導不力,導致議程設置失焦
1972年,麥庫姆斯和肖提出了議程設置理論,大眾媒體通過提供相關信息和安排相關議題來引導人們去關注媒體想要呈現的事實。在以前,傳統媒體作為權威的信息發布者、唯一的議程安排者和最終的決策發言者,不僅可以通過設置議程有效地把控輿情,還可以提供語境引導公眾的思考模式。在新媒體語境下,人人都有麥克風,信息的獲取由簡單的、單向性的線性模式轉化為復雜的、雙向性的網狀模式。公眾不只是被動地接收來自政府、傳統媒體發布的信息,還通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主動選擇和搜尋自己感興趣的各種信息,社交媒體也為公眾提供了“發聲”“討論”的渠道和平臺。議程的設置變為由傳統媒體、網絡媒體和公眾三方一起參與的過程,議程設置的效果出現了大大的弱化現象。
在后真相時代,“反轉信息、洋蔥新聞以及網絡謠言等網絡信息傳播的問題癥候已經成為互聯網的日常呈現”。不可否認的是,處于輿論風口浪尖上的主體事件提高了一些議論度低、尚未解決的同地域或同類型事件的曝光度,加速了“新聞搭車”事件的解決。但同時,部分夾帶著自身價值取向的自媒體文章以及一些添油加醋、鼓動情緒的不實謠言乘虛而入,使得輿論導向背離客觀事實,加大了輿論治理和事件處理的難度。微博大V和自媒體紛紛就自身立場表明觀點,引發狂歡群眾的站隊和圍觀。議程不斷擴張不斷更改,導致“議程失焦”,牽扯的事件越來越多,于是開始“新聞扎堆”。這對主體事件問題的解決并沒有起到推動作用,反而因過多的信息干擾核心議題的深入,造成輿情聲勢浩大而調查停滯不前的現狀。在后真相時代,一件又一件新聞事件的爆出不停地干擾公眾的注意力,甲事件的后續還沒有結果,立刻又有一個乙事件爆出轉移公眾的關注焦點,隨后又會有丙、丁事件覆蓋之前的事件。情感很多,真相太少,公眾輿論找不到釋放的通道,于是將突破口轉移到同議題事件或新聞事件的其他相關事件,使得“新聞搭車”現象愈演愈烈。
(三)網絡受眾回歸“本我”,缺乏理性
有關新聞之所以能夠成功“搭車”,與受眾的心理也密不可分。一方面,情感共鳴為相關新聞事件“搭車”提供了某種便利。近年來,虐童案件層出不窮,人們“唯恐自己成為這種行為的犧牲者”,出于心理上的恐慌,又苦于真相求而不得,于是將焦點轉向相關熱點事件,使輿論保持熱度。因此,北京“紅黃藍”事件爆出后,一系列涉及軍方、教育制度、經濟等方方面面的問題蜂擁而出。公眾希望多方輿論合力造成浩大的聲勢,對政府及媒體施加壓力,倒逼真相。
另一方面,認知偏見給予虛假消息滋生的空間。社交媒體平臺、智能算法、精準推送等合力形成了一個認識過濾的機制。如同麥克盧漢所言,社交媒體讓社會回到了一個重新部落化的狀態。在社交平臺中,個體所接觸到的人和事物都是依據喜好與興趣過濾篩選而來的,久而久之,那些不以致或是不感興趣的消息經由你的社交圈子被過濾掉,消失不見。那時人們就會陷入回音室式的信息閉環社會之中而不自知,認知偏見隨之加深。通常“被搭車”的案件都是受眾圍觀周期長、討論激烈且真相沒有及時公布的事件。公眾顯然對政府、企業等官方的回應存在明顯的懷疑和抵抗,這就給部分新聞發布者爆料類似事件創造了條件。不實信息操縱著民眾情緒和網絡焦點,將虛擬的情緒傳播轉化為媒介審判與網絡暴力。其實只需多方調查稍作比對便能辨別真偽。但在這樣的特殊節骨眼上,由于之前事件所帶來的認知,受眾對此深信不疑,不實消息混入其中,也使得輿論更加情緒化焦灼化。
三、“新聞搭車”現象的對策分析
一定程度的“新聞搭車”能夠引起政府、媒體和公眾的關注,有助于問題的盡快解決。然而在很多的“新聞搭車”現象中,逐漸演變出人肉搜索、網絡暴力、網絡民粹主義,使新聞傳播產生反功能的現實性意外后果,輿情陷入惡性循環,公眾處于一種輿情焦慮之中,失去信任,懷疑一切,不利于維護良好的網絡環境和社會穩定。彭鳳儀教授認為:“要防范和應對媒體的意外后果,化解和消除傳播危機,可以從建立事態預防機制傳播規范機制、危機管控機制和責任追究機制等方面入手。”呲外,要減少“新聞搭車”的出現頻率,筆者認為還應當從政府媒體和公眾三個方面來尋找應對之策。
(一)政府及時把握話語權,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
現在的信息發布形式似乎有這么一種套路,知情人或是當事人在網絡平臺發布,隨后引發公眾大量討論與轉載,然后傳統媒體介入其中,經過調查取證,進行報道,最后政府部門介入其中,進行發聲,回應相關事件或解決相關問題。政府似乎總是最后出面,普通公民既無法參與到決策中去,往往在長久的等待中等不到滿意的結果。知情權作為公民的最基本權利之一,是公民行使表達權利、監督權利的必要條件。如果知情權得不到滿足,長此以往,受眾會形成一種慣性思維,對政府部門的言論和觀點進行逆向思考和理解。政府應當聯合傳統媒體,及時把握話語權,運用新媒體技術,通過政務微博政府公眾號等平臺,第一時間公開信息,及時同公眾進行溝通,了解公眾的需求與疑惑。領導干部要以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六個及時”為準則,多上網了解民意,通過網絡走群眾路線,構建網上網下同心圓,更好地凝聚社會共識,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空間。
同時要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在一些存在較大爭議的事件中,發言人的缺位無疑是錯過了與公眾交流解釋的最好時機,雖然官方以文字和圖片信息第一時間做了公告,但是這種溝通是單向的,這種見事不見人的發言,在情感上的溝通幾乎為零。危機關頭,新聞發言人的發言,不僅是官方信息的回應,更是一種官方態度、官方立場的回應。后真相時代,公眾最關心的不是真相,而是一種對真相的態度和解讀。政府應在新聞事件被“搭”注意力的順風車之前,及時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降低“新聞搭車”的可能性。
(二)媒體要加強輿論引導,避免輿情積壓
在輿論風暴面前,傳統媒體和新媒體要找準自己的定位,各司其職,相輔相成。傳統媒體因為其守門人制度,為確保消息的準確性和真實性,消息的發布總是滯后于新媒體。新媒體時代,技術賦權,傳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轉化,傳統媒體的地位一度下滑,甚至面臨失語的現象。然而,傳統媒體的權威性與專業性依然是新媒體無法媲美的。在輿論爆發期,傳統媒體更應堅持新聞專業主義,堅持深度調查和持續報道,探索事件背后更深層次的動因,引導社會輿論往正確的方向發展“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另外,新媒體依據其特有的便捷性、及時性,實時向公眾公布最新結果,要避免虛假消息乘虛而入、混淆視聽。媒體應當密切關注社會熱點問題中折射出的大眾心理問題,及時進行有效排解,避免輿情積壓,使“新聞搭車”有機可乘。
(三)公眾需繼續提高媒介素養,理性看待“新聞搭車”
如今,受眾常常對傳播媒介中不合理的解釋提出質疑,主動探索追尋事件真相,這顯然是媒介素養提升的結果。2011年出版的《真相》一書的封底寫道:“現在是新聞最多的時代,也是新聞最差的時代。我們似乎更容易看見“真相”,但追究真相更難。新聞素養已經不單單是新聞從業人員必須具備的素養,在新媒體時代,公民在享有發言權的同時也應承擔提高“新聞素養”的義務,做有判斷力的信息公民。后真相時代,由于社交媒體的去中心性和匿名性,發聲渠道多元,信息魚龍混雜,造謠成本降低,信息的真實性有待考究。現在的問題不是有沒有信息,而是信息太多太濫,無法分辨。因此受眾需要提升媒介的批判意識形成媒體信息的辨別能力,避免被操控,成為信息的囚徒。
理性觀望、全面而客觀地瀏覽信息和聽取意見,避免“情感”站隊,避免盲從盲信,對“新聞搭車”現象會有良好的導向作用。后真相時代,當主體事件引發輿論熱議時,人們討論的重點已經發生偏移,比起所謂的真相,似乎情感上的共鳴更加重要。“大師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大眾不是想看你怎么表達你自己,而是想看你怎么表達我。”在注意力經濟社會,不少意見領袖為了吸引眼球,以誘導性的標題和言語引導受眾,形成輿論共同體。參與輿情討論的網民面對主體事件,往往缺乏一種獨立思考和理性判斷的能力。因此,在“新聞搭車”現象面前,我們必須保持弗洛尹德所說的代表理性與常識的“自我”,以防情緒和立場引導思維甚至行動,從而避免在網絡環境中的“狂歡”行為增加“新聞搭車”的概率。
四、結語
“新聞搭車”現象能夠在短時期內吸引大量關注,有助于增強輿論聲勢,引起政府和媒體的關注,從而加速主體事件的解決。但后真相時代頻繁的“新聞搭車”現象也加劇了新聞的同質化和碎片化,過度消費了受眾的注意力與情感,不僅會引起受眾的視聽疲勞,還會加劇社會的心理恐慌,更會導致輿論生態的固化和惡化。在信息繁蕪的后真相時代,突發輿情是不可避免的,“新聞搭車”現象也無法杜絕。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并非束手無策,而需各方齊心協力:政府及時準確把握話語權,完善網絡發聲制度,給予公眾訴求釋放的渠道;新舊媒體通過互動聯合形成一個良好的輿論引導機制,避免輿情的積壓;受眾只有不斷提高自身媒介素養,不被虛假非理性的信息所左右,理性看待“新聞搭車”,才能進一步構建起良好的新聞傳播新秩序。
參考文獻:
[1]江作蘇,黃欣欣.第三種現實:“后真相時代”的媒介倫理悖論[J].當代傳播,2017(4):52—53+96.
[2]林斐然,程媛媛.慶安槍擊案輿情“拔蘿卜帶泥”N].新京報,2015—05—14(A16).
[3]陳曉瑩.網絡傳播中的“新聞搭車”現象研究[D]長春:吉林大學,2017.
[4]陳龍.話語強占:網絡民粹主義的傳播實踐[小國際新聞界,2011,33(10):16—21.
[5]解迎春后真相語境下網絡信息傳播的問題癥候與應對策略[I].東南傳播,2018(11):126—127.
[6]柏拉圖理想國[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2.
[7]彭鳳儀.論新聞傳播的意外后當代傳播,2013(6):18—20.
[8]比爾.科瓦奇,湯姆.羅森斯蒂爾真相:信息超載時代如何知道該相信什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