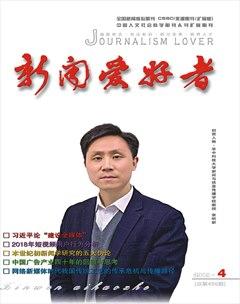社會問題類電影創作的類型策略
黃文欣
[摘要]從印度電影《摔跤吧!爸爸》到中國電影《我不是藥神》,近兩年一系列關注社會問題的電影獲得了口碑和票房的雙豐收。究其原因,除題材原因之外,這些影像文本之間還存在著一套相同且完整的類型化操作方案。通過對電影《我不是藥神》中的沖突構建、敘事模式、雙重主題等方面的拆解和研究,試圖找到社會問題類電影創作的類型策略。
[關鍵詞]社會問題;電影;我不是藥神;類型;策略
從中國電影《親愛的》到韓國電影《辯護人》,從印度電影《摔跤吧!爸爸》到美國電影《達拉斯買家俱樂部》,近幾年,一系列關注當下現實、聚焦社會問題的影片引起觀眾關注,并獲得票房和口碑的雙重肯定。2018年上映的《我不是藥神》再創社會問題類電影傳播效果的新高度。該片以真實事件為原型進行改編,展現了草根群像式的社會現實和小人物堅韌的生命意志。上映7周,票房累計超過30億元排名2018年豆瓣華語電影評分榜第一位,并獲得了第55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最佳原著劇本獎等獎項。成功的背后,有沒有創作規律可循?本文以《我不是藥神》為例,通過對其沖突構建、敘事模式、雙重主題等方面的拆解和研究,試圖找尋社會問題類電影創作的類型策略。
一、沖突構建:從社會到個人的創作路線
美國劇作大師麥基曾說:“沖突是故事的靈魂,故事是生活的比喻,活著就是置身于沖突之中。生活就是沖突,沖突就是生活。”正是沖突的出現,才賦予了影視作品以強烈的邏輯性和起伏性。社會問題是社會實際狀態與社會期望之間的差距,表現為社會全體成員或部分成員的生存和發展,與現有的社會價值、倫理、規范等之間的沖突。以社會問題為表現對象的電影,天然地處于各種社會矛盾沖突的交織和糾葛之中。如何處理這些矛盾沖突,并使社會問題中的沖突與故事創作中的矛盾沖突兩者融為一體,是社會問題類電影處理的首要問題。
(一)社會悖論、社會正義的雙重沖突選擇
社會悖論是指社會成員或社會部分成員的每個個體都在為自己作一個謀求最優支付的選擇,但這種選擇卻導致總體利益下降,使群體甚至整個人類遭受損失,最終也會損害個體本身。在電影創作時,將社會悖論作為沖突選擇的環境基礎,電影會從根本上帶有一種宿命感和悲壯的色彩。將社會正義缺失的事實作為沖突選擇的題材來源,會在雙重沖突的作用下,使社會問題類電影中的沖突更為激烈,更有深度和魅力。
這種沖突選擇策略成為眾多社會問題類電影創作的原始出發點。例如印度電影《小蘿莉的猴神大叔》,它以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間的沖突為背景,立足于一位純真的小女孩想要回家的合理愿望得不到實現的矛盾中,以這種雙重沖突作為故事創作的出發點將印度所特有的民族宗教社會生活和觀念融入電影的沖突解決當中。而在電影《我不是藥神》中,也是以個體利益與人類整體利益的社會悖論為前提的,每一個白血病患者都期待有價格低廉的特效藥品,然而這種期望卻不利于制藥公司持續研發新藥,進而阻礙了人類整體的未來健康利益。這種宿命式的社會悖論使影片從一開始就有一種悲壯的色彩。同時,面對已有的法律制度、既得利益的商人、利欲熏心的假藥販子所造成的社會正義的傾斜,使處于天平最低端的這些白血病人,面對“生”的最基本需求被阻礙,不得不發出最強烈的訴求一走私買藥賣藥。在這種雙重沖突中,中國文化的隱忍精神、家庭觀念和社會生活的多個層面融入沖突之中,表現出主人公負重前行的艱難。
(二)社會沖突下主人公三個維度的沖突構建
主人公三個維度上的沖突包括具體沖突、精神沖突和情感沖突,三個維度的沖突構建是好萊塢電影創作的基本特征,也是社會問題類電影類型化策略的必然要求。美國電影劇作大師Jeffrey Alan Schechter將故事規劃的核心定義為“中心問題”的解決,實際上即是現實與期望之間的沖突。他基于主角在生活上的三個目標將中心問題分為三個組成部分,即電影中主人公現實的具體目標、精神上的目標和情感上的目標凹,電影主人公三個維度的沖突構建就與這三個目標息息相關。在具體目標上構建的具體沖突,是主人公的主要行動和在故事中的主要使命,它牽動著整個故事的前進,影響著其他目標的進程;在精神目標上構建的精神沖突,它存在于主人公理性的層面,是主人公所必須面對的內心深處的恐懼悔恨或者心魔,并最終獲得某種稱號、榮譽,或者成為某種英雄;在情感目標上構建的情感沖突,是主人公對個人情感的追求,例如友情、愛情等。在社會問題類電影中這三個維度的沖突對于主人公來說缺一不可,是主人公完整存在的基本條件。具體沖突是在社會層面,主人公與社會悖論和社會正義之間的沖突,是故事的主線。精神沖突和情感沖突是故事的副線,伴隨著具體沖突的進展而不斷發生著改變。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進,交叉前進。
在電影《我不是藥神》中,程勇的初始狀態是一個面臨事業危機、家庭危機、社會認同危機的多重loser(失敗者)。而呂受益的出現成為人物轉變的契機,成功地將社會問題的沖突移植到程勇的身上。于是,主人公程勇的具體沖突起初是走私藥品掙錢和法律、社會的沖突,之后變為走私藥品救人和法律、社會的沖突。隨著具體沖突的發展也引發了精神和情感方面的沖突。精神沖突起初是程勇和這些白血病患者之間的認同沖突,之后是良心的自我救贖沖突。情感沖突是程勇與自己團隊之間的情感沖突,特別是程勇與劉思慧之間的愛情,隨著具體沖突的不斷變化,兩人從賣藥認識并產生好感,程勇不再賣藥兩人關系中斷,接著呂受益死亡,程勇不敢面對劉思慧,更不敢面對他們的愛情。最終,隨著故事的進程,三個維度的沖突走到一起,并得到一化解。
二、內容構建:“金羊毛”的敘事模式和四種人格的成長策略
社會層面的沖突選擇以及個人層面三個維度的沖突構建,為社會問題類電影的創作準備了充足的動力。然而電影的類型化需要具備更多的元素,一方面它要求各種線索下的沖突能夠一步步地積累、碰撞高潮,最后得到解決或和解;另一方面它又要求具有某種強力的接近性,而不是冷眼旁觀式的間離,觀眾能夠緊隨故事的發展,被電影所表現出來的形態所強烈感染,并產生認同。于是,希臘神話中“尋找金羊毛”的敘事模式和主人公四種人格的成長模式,成為社會問題類電影內容構建的重要策略。
(一)基于“金羊毛”敘事模式的“追尋”構建
社會問題是社會成員或部分成員所面臨的沖突,問題的解決要求所涉及的社會成員共同參與其中。社會問題類電影也并非是主人公單槍匹馬的戰斗,它要求主人公與其他代表性的社會成員組成“追尋”性的臨時團隊,雖然他們內部也會有各種矛盾,但矛盾會使團隊變得更加緊固,從而一同來化解大家所面臨的共同社會問題。
“金羊毛”的敘事模式為社會問題類電影的敘事策略提供了參考模型。“金羊毛”來自于古希臘神話《阿爾戈英雄紀》,講述了伊阿宋和眾英雄組成的團隊去遠征,克服重重困難最終奪取金羊毛的故事。這一“追尋”的結構,是對現實人類尋找人生意義道路的類比化概括,具有原型意義,也成為后世眾多文學作品的參考對象。美國著名編劇布萊克·斯奈德(BlakeSnyder)對這種模式概括為:主角“上路”尋找某物,歷盡艱辛最終發現別的東西——他自己。這種模式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即是沖突事件如何影響主人公并推動其內心成長。通過對“金羊毛”敘事模式的移形置換,社會問題類電影以社會沖突為基礎,主人公為了解決“具體問題”開始了自我的旅程,他需要召集自己的團隊,來彌補自己所不具備的品質、能力,同時在追尋過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精神問題和情感問題。通過不斷的求索,主人公和自己的團隊不斷克服困難,自我的內心也獲得了成長。最終,主人公和自己的團隊使具體問題,也即社會層面的沖突得到合理解決,自我也得到了意外的獎品——最原始最根本欲望的滿足。
“金羊毛”已成為眾多成功影視作品采用的敘事策略,特別是迪士尼的動畫電影,用“金羊毛”的敘事策略完成了童話和現實的雙層建構。而社會問題類電影也能夠天然地與“金羊毛”敘事有機結合起來,完成1+1>2的內容建構。這種建構在韓國電影《辯護人》、印度電影《廁所英雄》美國電影《達拉斯買家俱樂部》等中都有明晰的體現。而在電影《我不是藥神》中,這種“金羊毛”的敘事模式依托于社會沖突,得到了更充分的發揮。作為loser的程勇為金錢開始自己的旅程,途中集結了年輕丈夫、單親媽媽、老神父、青年混混,他們各有所能,又具有廣泛的社會代表性,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團隊。程勇成為團隊的核心,并與團隊的成員產生友情、愛情的情感紐帶,為共同的目標前進。在這個旅程中,我們隨同程勇一塊進入了白血病人這個鮮為人知的世界,也見證了程勇內心的成長與轉變,并在最后發現自己,得到與最開始的期望不同的獎品——使自己的良心得到救贖。
(二)旅程中四種人格的成長歷程構建
主人公四種人格的成長歷程,是依托于社會問題,并超脫于故事層面的旅程建構。定位在電影的不同階段,這四種人格的成長歷程按順序一般包括孤兒、流浪者、武士、殉道者甲。在社會問題類電影中,孤兒是主人公被拋棄、孤獨無助的狀態,正因為此,他必須出發;流浪者是主人公進入社會沖突中,逐步開始有自己的目標,他一步步地探索、行動、收獲情感或者小的成功,但這些成功并不是主人公真正想要的,這個階段也是游戲的階段,驚險、搞笑、動作等元素不停地刺激著觀眾的感官;武士是主人公真正發現自己想要的東西后,面對社會沖突中更強大的敵人,無所畏懼,不斷地戰斗前進,也是主人公真正開始不斷蛻化的過程;殉道者是主人公為了終極的目標,即對自身三個維度沖突的化解,面對不可能戰勝的敵人,放下一切,抱定必死的決心,為真正的自己獻身,這個階段也是最讓觀眾動容的階段。同時,不同階段的人格特征,也奠定了這一時期影片的情感基調和造型特色。
在電影《我不是藥神》中,這種內在人格的成長過程也表現得非常明顯。影片一開始,程勇面臨著事業和家庭的失敗,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孤兒。他衣衫襤褸頭發蓬松,在強調表意性的畫面中,永遠處于鏡頭的一角,并被環境中的其他東西所擠壓或遮擋。呂受益的出現使程勇踏上了買藥掙錢的“流浪者”旅程,也開始真正進入到社會沖突中,并逐步完成自身三個維度的沖突構建。他召集團隊,在走私、賣藥、打假的過程中一步步實現掙錢的目標。在這一過程中,追逐、動作、笑點、小的成功接連出現,成為影片中最有意思的橋段之一。但錢真的是他想要的嗎?程勇一人孤獨站在岸邊的場景,好像是在說明作為流浪者的心境。緊接著在高價藥下,老呂的死去、一個個病人的眼神使程勇逐漸發現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他開始成為一個“武士”,面對藥品貨源被封、假藥販張長林被抓、勢利商人和依法辦案警察的圍追堵截,程勇義無反顧。最后,在法大于情以及不可戰勝的社會悖論中,程勇放棄所有,成為一個真正的“殉道者”,觀眾也無不為他的偉大義舉所動容。
三、雙重主題構建:人性考問與社會正義的價值追求
社會問題類電影以人為主體,以社會問題為背景,包含了人性的問題和社會的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辯證思考,是實現電影思想深度、審美趣味和社會價值的內在要求。
(一)人性考問下善的選擇
“人性”是社會問題類電影的顯性主題。朱光潛曾說,文藝與作品的價值高低取決于它摹仿(表現、反映)自然是否真實凹,這里的“自然”主要指的是“人性”。社會問題類電影中的人,在面對自我需要與社會道德、制度、法律發生沖突時,會不自覺地發揚人道主義精神,在自我的徘徊中選擇“善”摒除“惡”,具體表現為舍己為人、舍小家為大家的行動。這種人性主題的選擇,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現代傳媒無限地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卻也造成了人際關系的冷漠,每個人都好像生活在自我的玻璃罩中。于是,電影中對人際關系“善”的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人與人之間的安全缺失。
在眾多社會問題類電影中,如香港電影《籠民》、韓國電影《辯護人》《熔爐》、西班牙電影《萬福瑪利亞》、印度電影《廁所英雄》《護墊俠》等,主人公都在人性的考問中選擇了“善”。電影《我不是藥神》對人性考問下“善”的選擇更加鮮明。在家庭層面,面對死亡和家庭的矛盾選擇,劉思慧和大多數家庭一樣選擇即使傾家蕩產也要救助親人,黃毛選擇離開家庭獨自面對死亡,呂受益為了不拖累家庭選擇跳樓自殺。他們無不舍己為人,放下自我選擇了更高的“善”。同時,在社會層面,沒有生病的第三者成為“人性”多次轉變的踐行者。程勇從最開始置身事外的第三者,單純為了掙錢的偽善,到逐漸真正了解病人的難處,最后程勇為了救人不惜傾家蕩產、放棄自己的自由,實現了自我對社會的更高層面的善。影片中的其他人物,例如起初賣假藥的張長林、嚴格執法的警察等,也有著同樣的舉動。這種以“善”為中心的人物構建,使觀眾產生了強烈的心理認同和共鳴,并隨著劇情的發展不斷地積累,直到最后的高潮。
(二)社會正義的價值追求
“社會正義”是社會問題類電影的隱性主題。社會問題類電影的最終歸宿是社會問題的解決或者推動其問題的解決,其中包含了社會悖論和社會正義所引發的問題,
在電影《我不是藥神》中,最不利者當然是看不起病的病人,他們具有選擇生存的合法期望和作為“人”的資格,社會正義的實現必然要求在不違背社會公眾更大利益的同時,使更多的醫療和藥品資源能夠向這些弱勢群體傾斜。所以程勇的所作所為,具有道德和社會正義的雙層正當性。另外,這種對社會正義的訴求是以含蓄的方式隱藏在電影故事之中的,它沒有用大聲疾呼的方式對社會問題采取強硬的批判,而是將這種對正義的訴求融入對人性的考問中,融入程勇作為一個社會小人物對正義的無私付出中,以更柔和的方式來打動觀眾,并使觀眾對這些弱勢群體產生廣泛的同情引起社會的廣泛討論。
法國電影理論家巴贊曾說“電影是現實的漸近線”,現實是電影的本質所在,而其“漸近線”的附加值卻是電影的魅力所在。社會問題類電影以社會現實中的問題為基礎,在類型化創作的附加值中與觀眾一道,完成了對現實的摹仿和揭示,以及心理情感和社會內在真實的構建,是一場對社會本質的藝術化演繹。對其類型策略的研究,能夠為今后更多社會問題類電影的創作提供一個可供參考的創作范式,使電影創作與中國社會現實更好地結合起來,創作出兼有經濟價值、藝術價值、社會價值等多重特點的優秀電影。
參考文獻:
[1]effrey Alan Schechter.我寫的劇本勝過你[M].吳碧玉,吳浩,吳明,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3:25.
[2]布萊克.斯奈德.救貓咪:電影編劇寶典[M].王旭鋒,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27.
[3]effrey Alan Schechter.我寫的劇本勝過你[M].吳碧玉,吳浩,吳明,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13:58—63.
[4]朱光潛.關于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和共同美問題[J].文藝研究,19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