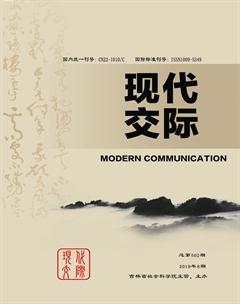大學生自我評價與“朋友圈”依賴的相關性定量研究
張楠
摘要:本次研究以米德的符號互動論和戈夫曼的擬劇論為視角,用spss對在延邊大學內(nèi)回收的183份問卷進行數(shù)據(jù)分析,得出大學生的自我評價與對社交依賴性、印象管理的程度等變量之間有較強的相關性,并得出“自我評價較低的人更在意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和印象,所以會通過刻意的自我美化來獲得同輩群體的關注和認同感”的結(jié)論。
關鍵詞:大學生 自我評價 社交依賴性 朋友圈 印象管理
中圖分類號:G4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9)08-0144-02
大學生群體在朋友圈的互動有個很有微妙的現(xiàn)象,有的人發(fā)朋友圈過了一會兒發(fā)現(xiàn)沒有被點贊或者評論就會偷偷把它刪除。這就好像話劇演員上場卻發(fā)現(xiàn)場下竟然沒觀眾,他可能會選擇灰溜溜地下場。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朋友圈大賽中的刷屏者是一個“表演者”,是一個“人設”的過程。人們在發(fā)布內(nèi)容的過程是建立并經(jīng)營這個假想人設即印象管理的過程。本次研究旨在發(fā)現(xiàn)大學生自我評價對于朋友圈的依賴性和印象管理程度的影響。戈夫曼認為:“每個人都在無時無刻,或多或少地,有意識地扮演著一個角色。”他結(jié)合符號互動論,提出了自我呈現(xiàn)的概念,闡述了個人是如何有目的性地通過控制有關自身信息的行為來引導和控制他人對自己印象的形成。
一、變量的設計及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的是《大學生自我評價與朋友圈印象管理》自制量表。本次的自制量表中關于自我評價的測量是基于Judge的核心自我評價量表(CSES),其他問題的設置是根據(jù)微信的固定功能和使用“朋友圈”的用戶群體習慣而設計的,經(jīng)spss檢測篩選后,最終信效度較高的變量包括六個維度的16個問項。
因子分析結(jié)果顯示,變量1(朋友圈活躍度)的因子位次賦值各為0.884、0.763、0.785;變量2(自我肯定程度)的因子位次賦值各為0.799、0.838、0.616;變量3(發(fā)言把控度)的因子位次賦值各為0.799、0.694、0.786;變量4(有意識打造理想人設)的因子位次賦值各為 0.730、0.829、0.597;變量5(調(diào)節(jié)消極情緒的能力)的因子位次賦值各為0.845、0.810;變量6(對互動與反饋的重視程度)的因子位次賦值各為0.804、0.864;其個子變量的因子為此負責都是0.6以上,在統(tǒng)計學上可視為有效變量;信度的分析結(jié)果顯示,變量1的 Cronbach's Alpha值是.762,變量2的 Cronbach's Alpha值是.698,變量3的Cronbachs Alpha值.688,變量4的Cronbachs Alpha值為.603,變量5的Cronbachs Alpha值是 .697,變量6的Cronbachs Alpha值是.685。信度分析結(jié)果,構(gòu)成各子變量的下位問項的內(nèi)部一慣性的Cronbachs Alpha系數(shù)都是在0.60以上,較為合適。
二、研究對象的社會人口學特性
本研究對象的社會人口學特征如表1所示。
基于社會人口學特征的“對互動與反饋的重視程度”差異u為檢驗基于社會人口學特征的“對互動與反饋的重視程度”差異,算出各平均和標準偏差,為了解各群間平均差異的統(tǒng)計意義上的顯著性,實施了t-test和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其結(jié)果如表2所示。
表2說明,雖然女大學生群體的均值2.7718高于男大學生2.1875,雖然都是在平均3分以下,但在上傳朋友圈文字或照片時,女大學生更重視別人對自己在朋友圈發(fā)布的內(nèi)容的反饋和彼此的互動。體育藝術類大學生的均值3.3077明顯高于其他三類專業(yè)的大學生,在對朋友圈中的互動與反饋的重視程度上與其他專業(yè)學生有顯著性差異。
三、雙變量的相關性分析
表3是基于雙變量之間相關性數(shù)據(jù)分析。結(jié)果顯示其中三對變量之間呈正相關、三對變量呈負相關。
1.朋友圈活躍度與發(fā)言把控度呈較強的負相關(P<0.01)
這說明,在微信使用中越傾向于“頻繁更新動態(tài)、上傳照片或者轉(zhuǎn)發(fā)鏈接”“盡量上傳可能引起更多好友興趣和評論的照片”“喜怒哀樂通常都表現(xiàn)在朋友圈中”的研究對象在發(fā)布言論時的把控度越低。
在社交平臺中發(fā)言越活躍的人越不在意自己的言論影響,對于在自己不熟悉領域的相關話題中的發(fā)言焦慮程度更低。在朋友圈活躍度高的大學生即使發(fā)布了針對別人的看法以及明顯帶有負面情緒的的內(nèi)容,也不擔心會引來他人的誤會和猜測,以自我為中心的意識更強。
2.朋友圈活躍度與對互動和反饋的重視度呈較強的正相關(P<0.01)
這說明,在朋友圈越活躍的人越重視互動與反饋。互動與反饋重視度的測量包含問項“當我發(fā)的內(nèi)容沒有被點贊或評論時,我會刪除掉這條動態(tài)”和”我經(jīng)常刪減自己過往的相冊內(nèi)容,選擇性地展示自我”。
也就是說,大學生群體中活躍在朋友圈的這部分人是會刻意地進行自我塑造,在虛擬社交中進行著精細化的刻意的印象管理的,對于他人點贊或者評論的期待更高,更希望獲得他人的好評和認同。這現(xiàn)象背后所隱藏的實質(zhì)是個人獲取愛與關注的需要。人們需要通過贊與評論數(shù)量證明自己是被在乎、被關注的。朋友圈中刷屏,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尋求被關注、被認可。
3.自我肯定程度與對互動和反饋的重視度呈較強的負相關(P<0.01)
這個結(jié)果能說明,自我評價越低的人更在意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和印象,所以會通過刻意的印象管理、美化自我來吸引別人的關注和認同。自我評價越高的人更能夠肯定自我,自我效能感更強,由于這些人在現(xiàn)實生活中自我價值能夠充分地實現(xiàn),對朋友圈這個展示自我的平臺的依賴感就低。換言之,自信的人相對于自卑的人對于微信社交的期待更低。
當我們對他人的朋友圈內(nèi)容進行解讀時,“秀、曬、炫”的的內(nèi)容能客觀地說明發(fā)布者內(nèi)心的自我肯定程度偏低,對于生活和學業(yè)上的成功把握性不高,現(xiàn)階段的心理狀態(tài)是比較不自信的。
4.發(fā)言的把控度和有意識打造理想人設呈正相關(P<0.05)
這說明,較少發(fā)言的人更在意自己給別人留下的印象,也可以說發(fā)布內(nèi)容相對是精心設計的,圖片和文字都很用心的人可能不經(jīng)常發(fā)言,但是如果發(fā)言那么一定是對發(fā)布的語言有過仔細雕琢,圖片也是精挑細選后發(fā)布的。而這個現(xiàn)象不難解釋:“朋友圈的自我呈現(xiàn)是無止境的,人設也需要相對應的內(nèi)容來維護,而當缺乏內(nèi)容維護的時候便會產(chǎn)生身份焦慮,身份焦慮聚焦于對自身角色和地位的不確定性,過多看重他人對自身的評價”。(田娜娜,2015)
5.自我調(diào)節(jié)消極情緒能力與對互動和反饋的重視度呈負相關(P<0.01)
自我調(diào)節(jié)消極情緒能力越強的人,在現(xiàn)實生活中越能排解負能量,抗壓能力和獨立性也更強,對微信社交的依賴感更低。
四、結(jié)語
大學生在朋友圈印象管理的過程中,成就感的主要來源就是他人對自己所“扮演”的社會角色的持續(xù)認可,這種認可在社交平臺上的表現(xiàn)即為點贊與評論數(shù)量。基于米德的理論,人的意識的產(chǎn)生視為外向的互動溝通和內(nèi)向的主、客我對話的雙向發(fā)展過程。
研究結(jié)果就如米德的符號互動論所說,大學生群體中確實有一部分人在朋友圈有意識地自我美化,刻意地進行自我塑造,在虛擬社交中進行著精細化的刻意的印象管理;但也有自我評價比較高、自我效能感很強的另一部分群體,對于朋友圈互動的依賴性不高,所以對于這一部分人,并非刻意地進行自我塑造,這其實已經(jīng)和米德的符號互動論的原初理論有一定的區(qū)別了。本次研究也有一定的創(chuàng)新性,帶入了自我核心評價這一概念,這是對于整個研究至關重要的一個變量,通過定量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關于這方面研究的自我呈現(xiàn)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的空缺。
參考文獻:
[1]徐曉蕾.自我同一性狀態(tài)和自我呈現(xiàn)技巧與大學生社交網(wǎng)站受歡迎程度的關系研究[D].復旦大學,2010.
[2]辛文娟等.大學生社交網(wǎng)絡中印象管理的動機和策略——以微信朋友圈為例[J].情報雜志,2016,35(3):190-194.
責任編輯:孫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