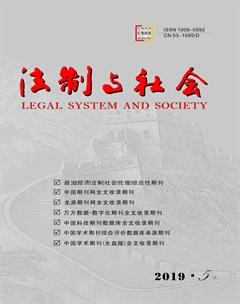農村留守婦女的社會支持網絡再建構與網內資源流向
余洋 王春蓉
摘 要 留守婦女作為城市化、工業化發展中的必然產物,一直以來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扮演著及其重要的作用,但在當下留守婦女在生產與生活過程中仍然面臨諸多壓力,如何解決當前留守婦女的基本困境,本文在實證調查及文獻梳理的基礎上,重新反思了留守婦女的社會支持網絡 ,進一步解釋了“精準扶貧”背景下留守婦女社會支持網絡的再建構,同時針對社會支持網中的資源流向,本文基于社會支持網絡再建構的過程,提出了網內資源流向由“資源分散型”向“資源閉合型”轉變的觀點。進一步強調了當前對于留守婦女提供正式的社會支持,建構弱關系組成的社會支持網的重要性。
關鍵詞 社會支持網絡 資源流向 精準扶貧
作者簡介:余洋、王春蓉,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社會學碩士。
中圖分類號:C91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5.183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得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偏差,導致城鄉之間截然不同的二元結構,農村傳統的生活模式發生巨大變化,越來越多的農村群體外出務工,催生了中國最龐大的農民工群體,他們作為城市發展建設的中堅力量,參與著城市化發展的所有過程,并作為時代進步的見證者,實現著自身身份的遷移與變化,同時,在農民工誕生的背后,相比于繁華現代的城市生活,在傳統的中國鄉村社會也誕生了一個新的群體,他們就是留守群體,簡單來說包括留守婦女、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這其中留守婦女,作為丈夫外出后仍然獨自或者與家庭成員生活在原籍地的女性群體無疑成為了時代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產物,依靠固守傳統的生活方式,遵循著傳統的生活理念,在傳統的中國鄉村社會關系網絡中,承擔著延續家庭、家族文化精神的重要作用。事實上,留守婦女,在丈夫外出前和外出后所承擔的使命和自身身份都存在著巨大的變化,換句話而言,在傳統的中國鄉村社會,女性群體的角色主要存在于“幕后”,而隨著丈夫外出,留守的女性群體不得不從“幕后”走向“臺前”開始承擔部分丈夫在家原本所承擔的工作。正是在此背景下,農村留守婦女普遍面臨較大的生活壓力,并且由于丈夫的常年在外,夫妻間缺乏有效的溝通交流,因此在情感上也缺乏相應的安全感。也因此使得對于農村留守婦女問題的關注與重視意義非凡。早在2007年周慶行、曾智等人就基于重慶市留守婦女的調查研究,發現絕大多數農村留守婦女都承擔著生理與心理的雙重壓力,幸福感普遍較低;黃安麗的研究也發現農村留守婦女勞動強度高,娛樂生活單調,身心健康狀況令人擔憂。正是針對留守婦女所面臨的諸多問題的現實狀況,諸多學者開始轉向研究如何進一步解決留守婦女的相關問題,并且如何為其提供必要的社會支持。
就目前的研究來看,我們可以按照支持主體將社會支持分為四類:由政府和正式組織(非政府組織)主導的正式支持;以社區為主導的“準正式支持”;由個人網絡提供的社會支持;由社會工作專業人士和組織提供的專業技術性支持。這四類支持互有交叉,但在更多層面相互補充,已經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導、多元并舉的社會支持系統框架。充分發揮各項社會支持的作用,有效緩解留守婦女的生存壓力刻不容緩,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新農村建設開始邁入新篇章,隨著而來的也是政府對農村問題的關注與重視,各類社會資源也開始從城市流向農村,但在短期內農村留守婦女所獲得的社會支持網絡仍然存在諸多問題,難以完善,牛芳在2011年針對西北五省農村留守婦女的研究中就指出“規模偏小,以強關系為主,異質性較低,趨同性較高” 是當前西北地區留守婦女社會支持網絡中的顯著特征,同時社會支持的提供對象也多來自親戚朋友鄰居等熟人關系,缺乏相對正式的社會支持。如今面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時期,農村留守婦女問題也呈現出新的特點,尤其是隨著精準扶貧工作的落實開展,“三農問題”正迎來全新的機遇期,隨著“村村通工程”、“駐村干部幫扶”、“婦女能力建設培訓工程”等利民工程的開展,傳統的農村留守婦女的生活狀況也在面臨極大的改善 。
在此背景下,傳統農村留守婦女在社會支持網絡中角色也發生著巨大轉變,她們開始面臨新的處境,即隨著血緣關系向地緣及業緣關系的轉變,傳統的非正式社會支持正逐漸淡漠,即農村留守婦女的社會支持網絡將面臨再建構的過程。而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就是隨著丈夫外出農村留守婦女的社會支持網絡再建構的過程是怎么樣的?再建構的結果呈現出怎樣的特點?以及再建構后社會支持網絡中資源的流向問題?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實地調查和文獻研究的方法,通過對西北地區留守婦女群體進行問卷調查和訪談,進一步收集材料,詳細考察西北地區留守婦女的社會支持網絡的現狀。同時,通過分析文獻,尤其是通過對我國“精準扶貧”相關政策文件的考察,思考新時期留守婦女群體的社會支持網絡所進行的再建構過程,從而反應社會支持網絡中資源流向的問題。
三、農村留守婦女傳統的社會支持網絡構成
幾千年來,中國傳統鄉村的社會生活網絡一直以來主要以血緣關系、地緣關系為紐帶加以組織,親戚之間的熟人交往占據了其中的絕大部分,人情世故也大多依據關系的親疏程度來加以衡量,往往一族一姓即組成一村一莊, 即使同一村莊有雜姓居住, 也常常是世代為鄰。地緣關系與血緣關系相互交織, 呈現出兩個彼此不同的關系取向:在本村內部, 相互間的交往強調和睦相處, 止息紛爭;對外村外鄉, 則抱著提防和疏遠的心理。鄉民重視地緣關系的另一個表現是, 離開家鄉之后, 鄉民們在外地總會依賴其地緣關系構造一個以同鄉為紐帶的亞社會結構 (陸緋云, 2001 ;閻云翔, 2000)。因此依靠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傳統中國鄉村得以編織一個錯綜復雜的以初級關系為主的社會關系網絡,這種關系也正如美國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所提出的其中充滿同質性的強關系,大多來自共同的姓氏,共同的血緣,共同的文化程度和共同的思想觀念。這也符合中國鄉村相對封閉的特點,所接觸的人群有限,強關系所連接的才是人們日常勞作生活中所需要的各類資源。正因如此,農村留守婦女所能獲得的社會支持也大多來自于傳統社會關系網絡中的強關系,即主要還是依靠親戚以及鄰里。
(一) 血緣、地緣關系維系的熟人支持網絡
在針對西北地區的調查中可以明顯的發現,在基本的社會支持中絕大多數還是來自于自己的親戚以及與自己距離較近的鄰里朋友,具體體現在留守婦女平時面對的生產勞動壓力以及情感壓力上。
在留守婦女日常的生產勞動中,有53.80%的人是獨自完成的,親戚鄰居幫忙完成的占16.00%,丈夫回來幫忙的占11.04%,雇傭幫忙以及租用機器幫忙的的只占3.90%、5.70%,靠留守姐妹幫忙的也只占4.80%,而村干部幫忙的僅為0.10%。由此可見在日常的生產生活過程中,留守婦女大多獨自完成生產工作,在此過程中為留守婦女提供支持的只有親戚朋友占據較大的比例,來自政府的正式社會支持還無法體現,幾乎難以獲得。
同樣在相對農忙時節,留守婦女在生產勞動過程中往往面臨更大的壓力以及挑戰,也更加需要相應的支持幫助。在西北五省的調查中發現農忙時節留守婦女的生產勞動獨自完成的占24.40%,親戚鄰居幫忙的占25.10%,丈夫回來幫忙的占21.7%,這三者占據了絕大部分。剩下雇傭幫忙、租用機器幫忙、留守姐妹幫忙僅占據相當少的比例,村干部等的幫忙則幾乎沒有,可以完全忽略不計,由此可見留守婦女的主要支持仍然來自于丈夫以及自己的親戚鄰居,正式的有組織的社會支持較少甚至幾乎沒有。
通過與留守婦女的交流溝通中發現,留守婦女自身獲得社會支持的方法也有自己的考慮和理解,她們更加愿意依靠的是親戚和鄰居,首先所尋求的也是親戚和鄰居的幫助,而針對村干部等相關組織的支持和幫助甚至是沒有考慮或者說不敢考慮。
因此在生產勞動強度大,一個人忙不過來時,19.40%的人會選擇向婆家人求助,31.40%的人選擇求助親戚鄰居,13.70%的人選擇向娘家人求助,21.40%的人會向丈夫求助,只有8.80%的人選擇向留守姐妹求助,向村干部求助的更是僅有0.10%。由此可見對于留守婦女群體自身而言,她們更愿意相信的還是自身的親戚和鄰居,親戚鄰居的支持永遠占據相當大的比重。這也是當前中國農村留守婦女社會支持網絡普遍的現狀,主要依靠親戚鄰居等初級關系構成,血緣和地緣成為了社會支持網絡中的關鍵變量。
(二) 傳統的社會支持網絡中的資源流向:資源分散型
依靠血緣和地緣維系的傳統社會支持網絡相對而言更加符合情感性價值,往往更加雙方關系的親疏程度來決定提供支持的程度,并且這種以強關系構成的社會支持大多呈現同質性強的特點,個體之間的相似性較高,因此這種非正式的社會支持的實質其實是一種相互的社會交換網絡,即這其中各種資源流向都呈現出雙向流動的特點,當留守婦女從某一群體中獲得相應的社會支持,同時她也會在不同方面給予相對的回應,例如農忙時節的生產勞動往往存在互換功夫的情況,即今天在其中一家幫忙,明天大家在統一去另一家幫忙,而要想獲得這種支持,前提就是自身參與到這種支持活動中去,因此了這種來自于親戚鄰居的社會支持大多是充滿功利主義的,本質上仍然是一種等價交換的價值邏輯。
丈夫外出務工的目的是最大程度的獲得經濟效益,因此留守婦女的出現也是為了進一步節省家庭成本,但在丈夫外出后留守婦女所獲得的非正式的強關系的社會支持則是有代價的社會支持,在這種傳統的社會支持網絡中,必須的一部分開支則是用于維系這種熟人關系,在中國農村有這樣一句諺語“人情大似債”,這種針對人情世故的支持力度則是在農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在這種非正式支持為主的社會支持網絡中,資源流向呈現的是一種分散循環的狀態,難以集中到留守婦女家庭之中。
四、農村留守婦女社會支持網絡的再建構
(一)業緣關系維持的弱關系社會支持網絡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國正進入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我國社會、經濟、文化等各種領域都迎來了百花齊放的迅速發展期,工業化、城市化所帶來的巨大發展也給傳統的農村生活帶來了巨大轉變,城鄉二元結構在新時代下也迎來了嶄新的發展,因此我國留守婦女群體在新的社會環境也將面臨新的挑戰。
早在2013年11月,習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時首次作出了“ 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 ”的重要指示,精準扶貧的重要思想開始生根。2014年1月,中辦詳細規制了精準扶貧工作模式的頂層設計,推動了“精準扶貧”思想落地。2014年3月,習近平參加兩會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實施精準扶貧,瞄準扶貧對象,進行重點施策。進一步闡釋了精準扶貧理念。2015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新年首個調研地點選擇了云南,總書記強調堅決打好扶貧開發攻堅戰,加快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5個月后,總書記來到與云南毗鄰的貴州省,強調要科學謀劃好“十三五”時期扶貧開發工作,確保貧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脫貧,并提出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精準扶貧” 成為各界熱議的關鍵詞。也正是在此背景下,農村扶貧建設開始進入新時代,精準到戶 、精準到人,政府開始針對性的進行脫貧攻堅工作。農村廣泛的婦女群體也作為重點扶貧對象,因為相對而言,女性在同等條件下更難獲得與男性相等的社會資源。于是一系列針對女性的扶貧工作逐漸開展,在集中連片特困地區新建200個全國巾幗現代農業科技示范基地、“三八綠色工程”示范基地、婦女手工編織示范基地、巾幗家政培訓示范基地等全國巾幗扶貧示范基地;創新扶貧模式,通過推動創辦巾幗合作社、家庭農場、電子商務、農家樂等,培育10萬名巾幗致富帶頭人;以推動貧困婦女持續增收為核心,以各項扶貧政策、措施為手段,每年脫貧人口中婦女比例不低于40%。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傳統農村留守婦女的社會支持網絡也在精準扶貧政策大背景下迎來新的變化,開始由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為主的強關系維持的社會支持網絡轉向依靠政府以及相關社會組織等提供的弱關系為主的社會支持網絡。
正如諸多農村地區開始開辦系列婦女職業培訓班,業緣關系開始作為重要的一部分,在留守婦女群體社會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在調查中可以發現,在西北地區留守婦女群體中,當人身財產安全收到侵害時,有13.5%的西北農村留守婦女會向婆家人求助,有27.6%的西北農村留守婦女會向親戚鄰居求助,有9.6%的西北農村留守婦女回想娘家人求助,有8.4%的西北農村留守婦女會向朋友求助,有4.2%的西北農村留守婦女會向留守姐妹求助,有7.5%的西北農村留守婦女會向村干部求助,有13.8%的西北農村留守婦女會向丈夫求助,有13.7%的西北農村留守婦女會向警察求助,有1.7%的西北農村留守婦女會向其他人求助,總分分析發現,西北農村留守婦女求助對象的前四位是親戚鄰居、丈夫、警察與婆家人。因此,警察開始納入到留守婦女的考慮范圍內,并且占據相當的比重。正式的社會支持網絡開始在“精準扶貧”的大背景下逐漸在留守婦女群體中重新建構。
(二) 再建構社會支持網絡中的資源流向:資源閉合型
隨著正式社會支持網絡的不斷建立, 留守婦女群體所能獲得的資源也呈現出新的特點,相比較于傳統的社會支持網絡中留守婦女所能獲得的資源,再建構社會支持網絡下,顯然依靠正式的弱關系所編制的支持網絡中,資源流向也呈現出新的特點。
相比于傳統社會支持網絡中留守婦女資源分散反哺的現象,再建構的社會支持網絡中資源主要來自于政府和社會組織,留守婦女群體所獲得的資源是純粹的來自于政府和社會組織,并且在此過程中無需對獲得這種資源所給予相應的代價。
五、結論與討論
本文對留守婦女的社會支持網絡的討論,依據我國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對于傳統的社會支持網絡進行了一定的總結,同時根據新時期我國社會發展的新境遇,對留守婦女社會支持網絡再建構進行了嚴肅的思考。同時針對不同時期社會支持網絡中資源的流向問題進行了一定的討論,提出了資源流向中“資源分散型”向“資源閉合型”轉向的觀點。但本文在資料收集上仍然過于片面,對于理論的理解與運用也具有一定局限性,這是今后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地方。
注釋:
牛芳.西北地區農村留守婦女的社會支持網絡特征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基于甘肅省農村的調查[J].科學經濟社會,2011,29(3):71-78.
曹菁. 西北地區留守婦女政治參與問題研究[D].西北大學,2014.
閻云翔.禮物的流動——— 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參考文獻:
[1]牛芳,康翠云.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留守婦女社會支持網絡構成及其特征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18(3):33-44.
[2]黃粹.農村留守婦女生存困境:身份認同與組織化發展[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17(5):4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