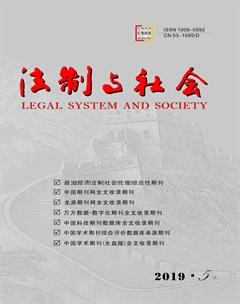試論宋儒的生態價值觀
摘 要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到了新的高度。這是基于我國發展所面臨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作出的歷史抉擇,同時又根植于中國傳統生態智慧。本文嘗試從生態文明的角度切入,通過分析我國古代宋儒觀念中“民胞物與”的樸素生態理念和“萬物一體”的仁學核心內涵,重在發掘傳統思想中所蘊含的生態思想,對于當下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和諧共生 民胞物與 萬物一體
作者簡介:彭藍君,南昌大學人文學院。
中圖分類號:B24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5.228
黨的十九大將“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作為重要議題,強調“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 可以肯定的認為,對于我國這樣發展速度較快的大國來說,在此階段強調生態文明建設是高屋建瓴,符合人類社會科學發展規律的,也為我國接下來的可持續發展確定了正確的道路和目標。實際上,關于發展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上個世紀就已經開始備受討論。如20世紀末來自全球各國的上千位科學家聯合發表的《世界科學家對人類的警告》,就嚴肅地指出了人類不恰當的發展方式對自然的傷害極大。這個警告振聾發聵。如今盲目開發、濫砍濫殺、破壞植被等問題愈加嚴重,甚至已經開始出現反噬人類的端倪。環視全球,“環境問題”儼然是一個亟需解決的大問題。中國傳統思想中關于“天”“地”“人”關系的詮釋,為我們新時代推進生態文明具有借鑒意義, 因此,我們可以從儒家文化特別是宋儒的探討中汲取積極的生態價值信息,并對它作出適應現實社會生活的新詮釋。
一、民胞物與的生態價值觀
張載於《西銘》有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段話將天人關系看作是宗法血緣關系的泛化。其“天人”秩序建構以“家庭”為單位,把人作為“天地之子”實現了從“小我”向“大我”的過渡。實際上,張載這種物我統一的宇宙觀是《易經·序卦傳》中“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的延伸,放眼宇宙,把宇宙萬物看做和自己息息相通的整體,人類的智力如何發達也只是萬物的成員,因此人類不應傲視萬物。這種早期樸素的自然觀實際上已經蘊含了人在自然面前應該如何自處的正確觀點,是符合現代生態學規律的。自然界萬物皆可以 “吾體”“吾性”“吾同胞”“吾與”來自稱,于自然界而言,物與人無異。因為世間的萬物都有其存在的價值,都有其不斷地在自然界中延續下去的基因密碼,而正是這樣的價值和不斷延續的力量造就了我們的生活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作為自主性最強的人類來說,億萬年來的演變和文明的創造更體現了自然界的生命力和創造性。在所有的自然演進當中,盡管人類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痕跡,但不能否認人類只是自然循環中的一個環節,我們生生不息的繁衍能力和創造能力源于自然,也歸于自然。人類的發展浸潤在自然所孕育的輪回中。所以,無論從保持生態圈的和諧、穩定發展還是人類自身的生存需求來看,我們都需要更加友好地對待孕育、包容我們的自然。在這里,張載從本體論的高度視“天地”為萬物“父母”,把人類都無差別地視作“同胞”,而與人類生活密不可分的自然更像是我們的“朋友”。這種說法的重點并不在于對傳統宗族意識觀念的套用,更非從工具理性的立場出發,而在于從中所能找尋出“人”如何扮演好“天地孝子”這一崇高的角色的內在依據,是一種超出了狹隘的功利性要求的“忘我”境界,這種境界需要充分的道德修養來加以培壅。從宇宙本體的高度,使人們才可以對自己的道德義務有一種更高的了解,這種統攝萬物有的義務論才有了確證。實際上,人與自然萬物之間的關系遠遠高于人類社會中的“親情”,但是這種“親情”的類比能夠幫助人們體悟到天地人倫的存在,意識到自己的責任。這種 “視天下無一物非我”所傳遞出來的自然觀,也是古人“天人合一”的信念之所在。
鑒于此,有人認為張載似乎側重于強調個人對他人的義務而忽視個人的權利,過于強調自然至上的觀念。可實際上,張載的觀念雖然強調了“自然價值”的重要性,但其思想中究竟強調的是自然的核心作用還是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關于這兩者的看法并不相同。從自然主義的環境倫理觀看,自然高于人與萬物,人類只是自然的一個部分,這是人與萬物無差別的看法,這種觀點無疑蘊含著對人類的貶斥。而后一種觀點便有所不同,雖然也強調了“自然價值”,但這種看法中人與萬物之間是平等的,“民胞物與”的倫理觀明確肯定了人類作為自然一部分的重要性,包含著人類價值的高度肯定。這種看法不能等同于人類高于萬物,肯定人類的價值并不代表人類可以為所欲為,擁有特權,肯定人類所表示的是對人類作為一種靈長類生物,其對自然的反哺和推動的作用相比其他生命體來說更大,因此維護自然的使命也就更多。從這個角度來看,同其他生物相比,人類自身價值就顯得更為突出了,達到“與天地參”。宋代另一位大儒邵康節更有明確地說法:“唯人兼乎萬物,而為萬物之靈……唯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類則不能也。”(《皇極經世·觀物外篇》)人類能夠“兼乎萬物”,成為萬物之靈,是因為人類能夠最大化自然在其身上的作用,能夠利用自然規律來發展自己,能夠意識到世間萬物之于人類的重要性,然后擔負起參贊萬物創化,使其生生不已這一使命。
樸素而睿智自然觀的出現,豐富了傳統儒家的思想內涵。從“民胞物與”的倫理觀出發,可啟迪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對萬物的體悟,更是與《周易·彖辭》中“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這一目標不謀而合。這種生態智慧閃爍在歷史的銀河當中,至今能夠給人以深刻警示。總書記指出,改善生態環境,要順應自然,堅持自然修復為主,減少人為擾動。現代社會的自然觀,歸根到底就是物與我和諧相處這一樸素的思想,其質之純,經千年滄桑而未變,為百代所追尋。
二、萬物一體的生態價值觀
“萬物一體”的說法源于程顥,其所追尋的正是“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的灑落境界與“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的仁者情懷。這也是宋明時期上百代儒者畢生所追尋的目標,因為其中蘊含著儒家思想的終極境界。從本質上看,這種“萬物一體”的生態價值觀所傳遞出來的就是人與自然相通、相互作用這一理念。“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想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二程集·遺書》卷二上)“莫非己也”是將“天地萬物”視為同人類個體息息相通,無法拋棄的部分。這種觀念程顥用傳統的中醫理論當中的“手足麻痹”作為一種病癥與“不仁”相聯系,人無法感知到麻痹后的手足,因而無法確認是否為自己身體的一部分,這就是“不仁”。而一個真正實現仁德境界的人,必然真切地感受到“萬物同體”,“莫非己也”。這種人道主義關懷與張載“民胞物與”“視天下無一物非我”的精神氣質相類。
在朱子看來,“萬物一體”之要在于“愛物”,而其將仁釋為“本心之全德”。(《論語集注》卷六)仁之真體作為“本心之全德”存在于人心,而愛物則是仁的外化。存于本心的仁德是所有行端的來源,能夠自內而外地照拂世間萬物,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這便是“萬物一體”的精髓,是人與自然最佳的相處模式。反之,如果沒有能夠將仁德存于本心,無法自內而外的流露出對自然的關愛,那么便是 “人欲之私心”,成為一個無恩之徒,此時其內心空虛而又膨脹的自我欲望就會不斷地“戮物”、“戕物”,結果只能是破壞生態環境,讓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更加不可調和。所以,在朱子看來,“仁”在這一過程中起著關鍵的作用,能夠讓人產生對自然萬物的關愛,所以對自然的仁就是人內心最純粹的仁,那么怎么才能形成“仁”?朱子認為“仁”既是“愛”,仁與愛相通相釋。但是仁心這個“體”并非簡單直接就可以發用,由于私欲障蔽,仁體不能全現,這需要克除私心私欲的工夫,克盡己私,使仁心完全實現而做到“仁民愛物”,才能夠讓人心與萬物之間沒有隔閡,達到“萬物一體”境界。
“萬物一體”不僅是人與自然的和諧,更是指人類社會中各種不同身份之間的和諧共處,體現在 “親親”(家庭)、“仁民”(社會)、“愛物”(自然)。實現“萬物一體”,其核心在仁。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一方面體現了社會發展的需求,從另一方面來看,也詮釋了儒家思想當中最核心的內容,即對世間萬物普遍的認可與肯定。朱子又言:“‘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理”。(《朱子語類》卷十五)這里,朱子所要表達的“至理”,正是自然創造萬物的共通之理,此理適用于人,適用于物,凡人間花草樹木,飛禽走獸都蘊含著此理。所以,只要意識到人與萬物之間存在相同的本質,就能夠推己及他,將自身的認知落實到真正的行動當中去。所以,殺生難為,殀夭難行,不忍覆巢,能夠取之有度,用之有節,此便能做到合內外之理,實現“萬物并育而不相害”。
從朱子的思想中,可以知道他并沒有忽視對人類自身的思考,但是朱子本身并不是人類至上觀點的推崇者,因為在他心中,人類與自然的最終利益是等同的。正如他所說,“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蓋不欲專以利為言,恐人只管去利上求也。”(《朱子語類》卷六十八)“蓋‘利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利。”(《朱子語類》卷三十六)孔子很少談及利益的原因并不是他不需要,而是他不愿意觸及。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因此小人往往很難擺脫對利的追尋。如《易傳·乾文言》中“利者,義之和也”,有人就會理解成義離不開利,義一定要有利才合乎人情,這就歪曲了圣人經典。所以,講利字一定要謹慎。“義之和”并非不義之利更非害義之利,而是以義調和利。如同“愛物”,人也要“惜物”“利物”。只有“利物”,人類自身才能得到合理的利益,這就是“義之和”。在對待自然界萬物的問題上,如果從“愛物”“利物”的仁心出發,充滿“只去利物,不言自利”的情懷,那么就可以避免出現因為一些蠅頭小利而過度向自然索求這樣的事情,而更愿意與自然和諧共生,讓萬物都有其生長的權利,肯定所有生命的存在,在合理的前提之下適當地運用自然規律進行創造,讓人類在自然之理的運作之下繁衍生息,不斷發展,從而反哺自然,二者相互依存,達到“萬物一體”的境界。
三、結語
“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中國在面向新時代、開展新征程的過程中,旗幟鮮明地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建設和諧生態家園,建設美麗中國”這一議題納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確保在黨的指引下,舉國上下都能形成正確對待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共識,建立起一個健全的生態文明制度,將我國建成一個高效而又綠色環保的現代化強國,實現世世代代中華兒女的可持續發展。這既是黨帶領著大家一路向前所擲下的諾言,更是所有炎黃子孫所需要履行的使命與責任。隨著時代的變遷,眾多往事云煙一掠而過之時,如若能夠抓住貫穿了千百年的儒家文化之精華,并用其滋養當代社會,那么我們對自然的理解必定會更加深刻,必定能夠讓生態文明的建設更加完善。
參考文獻:
[1]黨的十九大報告學習輔導百問[M].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學習出版社,2017年版.
[2]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
[3].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N]. 人民日報,2017-10-28(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