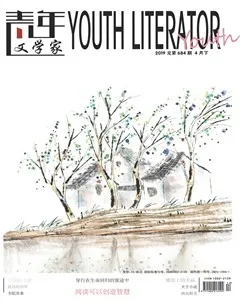從論語看孔子思想的辯證性
李月
摘? 要:孔子作為中國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和教育方法流傳至今,仍對后世具有啟發意義。同時,孔子所建構的以禮樂制度和道德教化為紐帶的倫理體系中也蘊含著豐富的辯證色彩。本文從《論語》一書出發,從政治觀、天命觀、人才觀、仕隱觀及中庸之德這五個方面進行闡述,深入發掘孔子思想中豐富的辯證法精神。
關鍵詞:孔子;論語;辯證法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12-0-02
作為儒家學派的源頭性典籍,《論語》中所蘊含的啟發性思想影響了幾千年來中國人的思維觀念和行為方式,孔子的學說和思想現今主要收存其中。通常來說,儒家從根源上影響了中國人的思維習慣,使人們從整體而圓融,和諧而中庸的角度認識世界。
《論語》的思辨性體現了孔子的通見具有博大的包容性和協調性。戰國時期的孟子、荀子分別從“仁義”和“禮法”兩個角度發展了先秦孔子的學說。到了漢代,董仲舒結合公羊家和五行思想,發展出“天人感應”理論。宋代從二程、朱熹的理學,再到陸九淵、王陽明的心學,都代表了儒家發展歷程中的不同階段。這些看似矛盾的學派,正是孔子思想在不同時代所產生的新發展。孔子思想世界和多面性和復雜性也體現在它能夠適應各個時代的需要,演繹出各種不同的新學說。經典的意義并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能夠從不同層次和角度對其進行理解和闡釋,能夠作為先導與啟蒙廣泛而又深刻地影響后世。孔子的智慧便是如此,即使是在今天的社會,我們仍能發現其中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天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仕與隱的辯證關系
一般談及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就不能不提到老子,老子的哲學把人類思考的范圍由人生擴展到了整個宇宙,實現了從宇宙論到人生論再到政治論的延伸,盡管他的形而上學是為了迎合人生與政治要求建立的,但他對于哲學發展的貢獻卻是不可磨滅的。而孔子的思想也對老子的哲學思想有所繼承和發展,史載孔子曾向老子問過禮,《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稱老子對孔子說:“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孔子大概接受了老子的教誨,所以既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憲問》)”的入世精神,也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退隱念頭(《公治長》)。孔子深明進退、見隱的辯證關系, 既不像隱士們那樣走極端一味地退隱,也不主張激進的殺身成仁式的入世。可見,孔子的仕隱觀是辨證的,孔子的思想在本質上是積極入世的,所以主張入仕、從政、行仁。但他也沒有排除隱逸之路,只不過是以“道不行”為前提,以“求其志”為條件而已。
在辨證的仕隱觀的指導下,孔子在求仕的同時也心存逍遙之愿。“天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泰伯》)”孔子的這種歸隱思想一定程度上受到道家的超脫避世,自然無為的啟發。這與孔子思想體系的思辨性分不開,既能夠積極入世,又能夠在“道不行”時隱退,既需要有對原則的堅守,也需要有變通的智慧。
“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憲問》)”作為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仁人志士,不能僅僅坐而論道,對亂世袖手旁觀,而必須入仕參政,才能實現“博施于民而能濟眾”的仁政理想。當仕與隱產生沖突時,他能以靈活的方法去處理。表面看來孔子的態度似乎是沒有原則,其實正體現了一種睿智的理性,變通的思辨,在出處、進退、行藏等問題上都不固執一端,而是因時而異,這是君子的通達。“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這是對孔子的仕隱觀的提煉和概括。
盡管孔子不被視為隱士,但孔子與隱士接觸時的態度,他的出仕與歸隱的矛盾糾葛,他對隱逸問題的深刻思考都對后代儒士的仕隱觀及中國隱逸文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點在阮籍的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從骨子里來說,阮籍其實是有著“入世”的政治理想的,他提倡孔子所說的倫理道德與禮樂秩序,這與儒家的理論一脈相承。但社會的黑暗又使他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抱負以求在亂世中保全自己,因此他“博覽群籍,尤好老莊”,由儒入道,由“入世”轉向“出世”。
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孔子天命觀的思辨性
孔子敬畏天命,他說的命分兩種,一種是死生壽夭,性命之命,“生死有命”的“命”,郭店楚簡《性自命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一種是窮達福禍,命運之命,“富貴在天”的命。對于前一種命,孔子認為是窮人力,竭智巧,最終不能控馭的東西,所以他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顏淵》)。“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這里的天命,則是命運之命,是人行為處事不可違背的準則。
另一方面,孔子又能夠發揮主觀能動性改變自己的命運。他說“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君子知其天命而為之。”(《憲問》)。這種人生態度既務實又樂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天命不可言說,自己想成為什么樣的人就會認為被賦予什么樣的命運,這都來自于人內心的訴求,用以鼓勵自身在逆境中也能夠以君子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天命”成了人前進的動力和精神支柱。這使得每個人都能夠依照自己的需求去發展他的稟賦。我們經常可以見到一個人處于禍患的境遇中,反倒激發他發奮的心智,使他邁向廣闊的道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泰伯》)在這樣的天命觀指導下的積極進取的精神也是孔子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
從孔子自身的經歷來看,當時的社會現狀是“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八佾》)“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微子》),社會混亂而無道,隱士們在這種“道不行”的現狀下返于野不問政事。而孔子卻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具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積極入世。因而一直處在漂泊不定,奔走列國卻難受重用的境地。政治抱負和社會理想難以實現,郁郁不得志,只得從轉向教書育人做學問,修習詩書禮樂。孔子對此只能以“天生德于予, 植魏其如予何” (《述而》),或者“ 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子罕》)這樣的話來自我解嘲。正因為始終處于這種顛沛流離的境地,人生的窘迫教會了孔子用辯證的眼光識人論事。
三、“過猶不及”的中庸之德
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 其至矣乎。”(《雍也》)把中庸之德,譽為“ 至德”。中庸至德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弟子及其后繼者子思和孟子等受其影響很大。“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過與不及,都是極端,不得其“中”。朱熹釋《中庸》之“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就是常,中庸即“ 中和可常行之道”,反映了孔子對合乎常理的理性原則的信奉,常識常情常理中體現了他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因為這個世界本身是按照辯證規律運行的。
孔子辯證法集中體現在他視自己整個思想言行都“依乎中庸”。中庸作為一種方法論,指的是不偏不倚、恰到好處的一種為人處世原則。其要義在“致中和”,認知與行為既無過,又無不及。《禮記·中庸》指出了中庸方法論的本質內涵,即“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這里的“中”,并非喜怒哀樂本身,而是指喜怒哀樂未發時的適中狀態,即“中”;平時能持中,一旦表現出來,能夠取中,即適度、無所偏倚,就叫“和”。由此可見,效果的“和”取決于方法的“中”。孔子的中庸之道講究處世為人要把握好“度”,根據特定的情況,在特定的地點或場合,對特定的人或事,為特定的目標,以與之適宜的方式方法來感受應對,就是合乎“度”的,反之,即為失度。孔子的中庸之道,表現為適時適度和循序漸進。中庸方法論由于著眼于矛盾雙方的統一,強調事物發展中平衡、穩定的一面,所以,它又體現了事物質與量的統一,這其中也蘊含了豐富的辯證法思想。
中國古代的哲學大致都與社會現實有所聯系,關注更多的也不是形而上學的世界,而是現實人生的境遇。孔子辯證的人生哲學和處世哲學給予了人們極大的指導意義,其中所蘊含的智慧影響了世世代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孔子的思想是一種變化的、活的文化,值得我們用發展的眼光對其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