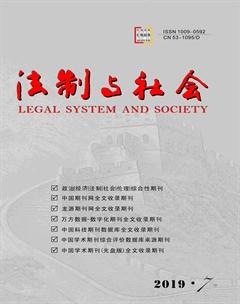試論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制度的完善
摘 要 2004年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后,我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及法律制度建設方面作出了一系列積極的探索并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下稱“非遺法”)于2011年的頒布,在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立法上有著里程碑意義,為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提供堅實的法律保障,更是我國履行國際公約義務的重要體現。中共十九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治國理政的系列重大理論和基本方略,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邁入新時代,呼喚著法學理論的創新。同時,回顧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實踐過程中的報規經驗,展望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的新方向,需要不斷創新與完善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制度,夯實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制基礎,增強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關鍵詞 非物質文化遺產 法律保護制度 國際公約義務
作者簡介:楊穎君,中國人民大學。
中圖分類號:D92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7.130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制度現存問題
(一)尚未就非遺法制定實施細則,配套法律制度缺失
非遺法出臺以來,各地大多均出臺了相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條例,但非遺法實施至今,仍未有配套的實施細則或司法解釋,使得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制度框架略顯單薄。同時,在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下稱“非遺項目”)評審規則、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代表性傳承人(下稱“非遺傳承人”)的認定方法以及相配套的流程、認定時限等具體實施細則方面,亦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立法空白。
此外,我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發展方面出現了系列的新變化及新趨勢,如:“名錄制度”建設、非遺館建設、構建系統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評估機制等。針對上述方面的新變化及新趨勢,我國現行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制度亦未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亟待立法上的呼應,以適應新時代的變化。
(二)非遺法護過分強調政府主導性,缺乏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等救濟途徑
非遺法第二十二、二十三條對非遺項目的審議及公示方面做出了規定,第二十九條對非遺傳承人的認定方面做出了規定,第三十一條對非遺傳承人資格的取消或重新認定做出了規定,但以上種種,均由政府主導,政府僅就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的項目予以公示并征求公眾意見,或將所認定的代表性傳承人名單予以公布。但就非遺項目審議不通過、非遺傳承人認定不合格或取消、重新認定非遺傳承人資格等事項,并未引入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等救濟途徑。
2017年,蘇州市首次公布了市級非遺傳承人評估結果,其中9名傳承人評估不合格,此事激起了截然不同的社會回響。一部分人士認為,此舉是一次不錯的嘗試,取消不能起到帶頭展示和宣傳作用的非遺傳承人的資格,是對非遺技藝正常展示和發展的保護;一部分人士認為,這樣一刀切的評估標準并不適用于所有類別的非遺傳承人,違背了立法保護初衷,且此次考核標準、范圍并未征求社會公眾的意見,加上,被認定為非遺傳承人后又被取消資格,過于兒戲,損害了非遺傳承人資格認定的嚴肅性。
綜上所述,無論從非遺法立法規定角度看,還是從社會實踐角度看,在非遺項目的審議、非遺傳承人的認定或者非遺傳承人資格的取消、重新認定方面,存在決策過程均由政府部門“一錘定音”之嫌,過分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忽視了非遺權利主體以及社會公眾的民間聲音,不利于非遺保護工作的全民參與。
(三)非遺權屬主體不明確,非遺權利主體合法權益未能落到實處
云南省大部分非遺是由當地民族集體創造出來的文化成果,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極大地推動了當地旅游業發展。但據當地非遺專家表示,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權利主體,當地人民因云南非遺獲得的經濟輻射利益非常有限,基本上都是通過簡單的商品貿易取得有限度的經濟收入,并未能全方位地享受到當地非遺開發、利用和發展產生的經濟效益。且這樣的問題,在國內并非特例。更有甚者,一些外國公司或個人利用我國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空白,惡意搶先注冊商標或申請相關專利,謀取暴利。
上述情形的產生,與非遺法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權屬主體規定不明不無關系,導致非物質文化遺產權利主體民事權益保護落空。而結合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發展方面出現的系列新變化及新趨勢,上述情形可能進一步加劇,甚至挫傷非遺權利主體保護和發展非遺的積極性,對非遺的可持續發展及法制建設產生不利影響。
(四)未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損害賠償機制及價值評估制度
非遺法第五條以及最高法發布的《關于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審判職能作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和促進經濟自主協調發展若干問題的意見》,均指出“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要堅持尊重原則,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應尊重其形式和內涵,不得以歪曲、貶損等方式使用非物質文化遺產。堅持來源披露原則,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應以適當方式說明信息來源”。
上述立法規定及意見,僅作出了原則性規定,未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損害賠償機制及價值評估制度,存在立法空白。損害賠償具體標準的缺乏、司法救濟程序的缺位等一系列問題,將導致非物質文化遺產權利主體難以依法維權,有關民事權益保護亦隨之落空。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制度完善的構想
(一)完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立法配套制度,引入行政復議及行政訴訟等救濟途徑,夯實依法行政的法律基礎
結合我國非物質遺產保護工作多年來的寶貴實踐,以及我國非遺保護的系列新變化及新趨勢,有針對性地完善非遺法配套法律法律制度,如:制定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實施細則或司法解釋等,進一步明確非遺項目及非遺傳承人在認定方法、流程、認定時限等具體實施細則,使非遺法更具實操性。同時,引入行政復議及行政訴訟等司法救濟途徑,從而改變現在過分強調政府主導作用的局面,夯實依法行政的法律基礎。
(二)界定非遺權利主體,創立新型的非遺知識產權制度
參考我國非遺保護專家趙曉瀾、全國政協委員蔡自興等專家、學者所言,針對我國非遺保護特點,應積極借鑒和利用我國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中有益的成分,將非物質文化遺產權定義為一種新型民事權利,明確非遺權利主體,構建一套關于非遺的知產專門法,打破現行法律框架的局限與不足,完善和增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知識產權保護的可操作性,實現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制度的創新。
(三)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損害賠償機制及價值評估制度,保障非物質文化遺產權利主體的民事權益落到實處
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四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六十五條等我國現行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中有關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的規定,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損害賠償機制,界定侵害非物質文化遺產行為的邊界,并制定明確、具體的損害賠償標準以及司法救濟程序。同時,借鑒《資產評估準則——無形資產》以及《關于加強知識產權資產評估管理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評估制度,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實施許可使用、質押融資、賠償責任追償時進行價值評估提供法律依據。
(四)引入公益訴訟制度,完善非物質文化遺產權利救濟途徑
貴州省安順市文化和體育局訴張藝謀、張偉平、北京新畫面影業有限公司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一案,有“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第一案”之稱,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該案中,貴州省安順市文化和體育局作為原告,以張藝謀電影《千里走單騎》侵犯了安順地戲的署名權(誤將“安順地戲”表述為“云南面具戲”)為由,將《千里走單騎》影片發行方北京新畫面影業有限公司、制片人張偉平以及導演張藝謀一并告上了法庭。本案終審判決雖駁回了貴州省安順市文化和體育局的訴訟請求,但本案積極意義在于政府部門主動作為,通過司法途徑主張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安順地戲”權利,喚醒了社會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權利保護意識。
然而,現有法律制度框架并不能有效地保證各地政府部門均與貴州省安順市文化和體育局一樣,及時采取積極措施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權利。當出現政府部門行為失范,如:政府不作為等情形,將導致非物質文化遺產權利保護處于真空的危險局面。引入公益訴訟制度,完善非遺權利救濟機制,對于非遺法制建設意義深遠。
(五)建立非遺機構的常年法律顧問制度
結合新時代的變化及發展趨勢,我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展館建設、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文旅融合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化形成等方面均有著不同程度的發展訴求。但囿于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意識覺醒較晚,非物質文化權利主體及社會公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律意識相對薄弱。針對非遺機構(如:非遺運營單位、行業協會、基金會等),建立常年法律顧問制度,為非遺權利主體及運營機構等進行保駕護航,既有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全面開展,更可利用法律顧問團隊在民商事法律實踐過程中的有益經驗,從而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制度的建設與創新。
參考文獻:
[1]穆伯祥.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知識產權保護模式研究[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
[2]劉云升,劉忠平.非物質文化遺產產業化法律規制研究[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7.
[3]宋俊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發展報告(2018)[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4]史家家.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立法的不足與完善[J].山西:法制博覽,2014.
[5]馬嘉會,宗泳彬.當非遺傳承人不再是終身符號[N].北京:北京商報,2017.
[6]韓小兵.非物質文化遺產權——一種超越知識產權的新型民事權[EB/OL].北京:首都法學網,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