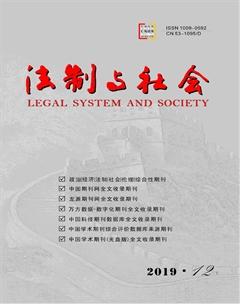人身保險合同中自殺條款之探討
李寒勁
中圖分類號:D923.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12.339
一、自殺的界定及自殺條款的適用范圍
(一)自殺的界定
自殺一詞作為一般日常用語,雖然人人皆知,其含義幾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對于究竟何為自殺并沒有統一的界定。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迪爾凱姆在《自殺論》中提出,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會產生這種結果的某種積極或消極的行動直接或間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殺①。通常而言,自殺是行為人自主終結自己生命的行為,應當包含行為人的自主決定要素。
對于自殺的概念,刑法領域研究成果較多,如陳興良教授將自殺定義為“基于意志自由,自我決定結束生命的行為”。在保險法上,自殺主要是作為保險人的免責事由或除外責任加以規定,出于防范道德風險的需要,保險人對于被保險人故意引發的死亡及其他保險事故免于承擔保險責任。因此,自殺條款中的“自殺”應指故意自殺,即被保險人自殺時主觀上應為故意而非過失,其主觀上認識到自殺行為的結果且意欲追求死亡結果的發生,且客觀上自主自愿地實施了導致自己死亡的行為。這就意味著,若行為人主觀上并沒有自愿追求死亡結果的發生,即使客觀上實施了導致自己死亡的行為,也并不屬于保險法上的自殺。對于保險法上自殺概念的理解不同,存有爭議的主要問題就是間歇性精神病人、抑郁癥患者在發病期間的“自殺”是否構成保險法上的自殺。
(二)自殺條款的適用范圍
依據我國《保險法》第44條的規定,自殺條款適用于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從體系上看,該條文居于“人身保險合同”這一節,含有以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內容的人身保險合同包括人壽保險合同、意外傷害保險合同與健康保險合同,但并不能由此得出自殺條款在這三類保險合同中均得適用的結論。
自殺條款不適用于意外傷害保險。自殺條款中的“自殺”僅指被保險人主觀上為故意而實施的自殺行為,而意外傷害保險所保障的“意外”是指非本意的、外來的、突發的及不可預見的意外事故,自殺顯然不屬于“意外”。且意外傷害保險合同中都將被保險人自殺死亡明確列為除外責任,無論被保險人何時自殺,保險人均不承擔賠付責任,因此自殺條款對該險種并不適用。
自殺條款不適用于健康保險。長期健康保險中也包括死亡保險責任,但自殺條款并不適用于此。這是因為,一方面,自殺本身并非疾病,不屬于健康保險的保障范圍,即使被保險人因身患承保的重大疾病痛苦不堪而選擇自殺死亡,由于自殺條款的適用僅考慮被保險人對于自殺行為的認識能力和控制能力,并不考慮自殺行為的具體原因,故仍然不得適用;另一方面,健康保險合同中的除外責任部分通常明確將被保險人故意自殺而致殘、致死作為內容之一。因此,自殺條款對健康保險也并不適用。
因此,我國保險法上的自殺條款僅適用于人壽保險,這與德國、美國、我國臺灣地區等國家和地區的保險立法規定是一致的。
二、自殺條款的理論基礎
自殺條款并非人壽保險的固有內容,而是隨著對于自殺是否屬于可保風險這一問題的認知及理論的不斷發展,最初由美國法院通過一系列保險判例加以確立,并在后來的人壽保險實踐中逐步發展與完善的。
在18世紀的歐洲,受“自殺即為犯罪”觀念的影響,大多數國家在立法中明確自殺為犯罪行為,而且還規定了對自殺者的諸多嚴厲的刑罰措施。加之保險法上的公共政策又要求“被保險人一般不能從自己犯罪行為的后果中得到保險補償”,由此將被保險人自殺死亡完全排除在人壽保險的可保風險之外,保險人得以絕對地免于承擔賠付責任。在這一時期,歐洲各國的保險立法及學說均認為自殺不具有可保性。進入19世紀以后,隨著古典刑法理論的發展,自殺不再被視為犯罪行為,立法上也廢除了對自殺者的嚴厲刑法措施,但保險經營的技術性依然排除了自殺的可保性。保險經營的技術性主要體現為以大數法則為技術基礎來測定危險發生率并計算保險費率。大數法則以大量的、在一定條件下重復出現的隨機事件為基礎,基于隨機事件呈現的規律性與穩定性,保險人能夠較為準確地預測危險的發生,公平合理地厘定保險費率。使其在保險期限內收取的保險費與賠付的保險金及其他費用開支能夠保持基本平衡。而被保險人自殺是基于其自主意思的故意行為而非隨機事件,不具有偶然性,且大量因故意造成的損失發生,不僅使保險人對于危險發生難以準確預測,也使保險人沒有足夠的危險單位來預測未來的損失。因此在這一時期,自殺仍然不具有可保性。
從20世紀初開始,隨著美國保險理論與判例的發展,自殺危險在保險的技術性上不可測定這一理論不斷遭到學者質疑。實際上,在人壽保險經營實務中,自殺所造成的死亡一直被納入死亡率的統計中,保險人假定的預計死亡率也高于實際死亡率,保險人這么做的目的在于防止收取的保險費不足以抵交死亡保險金的情況發生。保險費率的確定是以死亡率的統計為基礎的,既然自殺本身并未影響保險費率的確定,在被保險人按照保險費率繳納保費而又自殺死亡的情況下,保險人對其自殺所致的死亡給付保險金并不會影響保險業的風險精算。有學者批評指出:“人壽保險是一種以保障經濟生活為目的的組織制度,具有安定被保險人遺屬生活的社會功能;然而,曾有一段時間,人壽保險契約完全排除自殺的風險。非常不幸的是,這與購買保險的目的——保護受扶養家屬——相違背。自公共政策的立場,社會并不希望在被保險人死亡時遺留缺乏生活保障的受扶養家屬,而這正是人壽保險契約的基本目的。”②因此,這一時期的主要觀點在于,不僅自殺危險本身從保險技術上是可以被測定的,而且從人壽保險的目的在于為被保險人的遺屬提供生活保障這一角度而言,自殺的可保性也應得到確認。
由上可知,關于被保險人自殺之可保性的學說基于保險經營的技術性和人壽保險的目的性而彼此對立,也即“技術說”與“目的說”這兩種理論相互沖突。美國法院在一系列保險判例中試圖對這兩種沖突的理論進行調和,最終在“里特訴美國人壽保險公司(Ritter v.Mutual Life Insurance U.S)案”中找到了折中點③。在該案判決中明確指出,保險人是否應當給付保險金,應以被保險人在締約時是否有自殺的意思為判斷依據。由于被保險人在締約時主觀上是否有自殺的意思難以判斷,故法律或保險單可以規定,即使自殺發生于保險合同生效一定期間后,仍在保險人的承保范圍內。該判決所指的“保險合同生效后的一定期間”即為自殺免責期間,被保險人在自殺免責期間內自殺的,保險人得免于承擔保險責任。被保險人在自殺免責期間經過后自殺的,保險人仍應承擔保險責任。這一判例的觀點是現代保險法理上自殺條款的依據和基礎。“調和說”的折中點在于自殺免責期間的設置。
自殺免責期間的設置,不僅有利于防范道德風險,也符合人壽保險為因被保險人死亡遭受損失的遺屬提供經濟保障的制度目的。自殺免責期間的設置是在保險人防范道德風險的經營需要和受益人獲得保險金給付的經濟保障之間利益平衡的結果。
三、自殺條款的立法檢討
(一)自殺條款的除外規定
依據《保險法》第44條第1款的規定可知,在二年的自殺免責期間內,被保險人自殺時為無民事行為能力的,保險人仍應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也就是說,被保險人為不滿八周歲的未成年人或不能辨認自己行為的成年人時,不論其是否在自殺免責期間內實施自殺行為,保險人均應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保險法》的此條規定以民法上的民事行為能力制度為基礎。
以被保險人有無民事行為能力來判斷其自殺是否適用自殺條款的例外規定,學者多從自殺行為的性質和自殺本身含義等方面否認這一標準的合理性。一方面,自殺行為屬于事實行為而非法律行為,自殺者并無產生民事法律關系的意思,不能套用民事行為能力的一般標準;另一方面,自殺條款的“自殺”不包括缺乏自由意思決定能力者導致自己死亡的情況。決定自殺條款例外情形的標準應當是意思能力。④如前所述,自殺條款中的“自殺”是指被保險人在對自殺行為的性質和結果有正常認識能力的情況下自主決定實施導致自己死亡的行為,自殺判斷的著眼點并不是被保險人客觀上實施了導致自己死亡的行為,而是被保險人在自殺時主觀上是否明確認識到并自愿追求死亡結果的發生。若被保險人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但因過量吸毒或患有精神疾病導致其自殺時并不具有認識自己行為結果并自主決定的能力,不能由此認定被保險人有以自殺來詐取保險金的意圖,其自殺不屬于保險法上的“自殺”,保險人仍應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假如被保險人為未滿八周歲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但其自殺時已具有認識自己行為結果并自主決定的能力,則其自殺符合保險法上的“自殺”概念,保險人應得以免于給付保險金。
在保險司法實踐中,間歇性精神病人、抑郁癥患者在其發病期間自殺是否能夠認定為保險法上的“自殺”,保險人是否應承擔給付保險金責任是爭議較多的問題。依據第44條除外規定所確定的“無民事行為能力標準”來判斷,就可能將因精神疾病導致缺乏正常認知和判斷能力下實施的自殺認定為“自殺”,使保險人得以在自殺免責期間內免于承擔責任。對于間歇性精神病人、抑郁癥患者在發病期間自殺是否為保險法上的“自殺”不能一概而論,應當根據個案具體情況,對被保險人在自殺時的精神狀況、認知能力和控制能力等進行全面評估,若被保險人確實處于發病期間且在不具有認識和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情況下實施自殺,并不是主動追求死亡結果的發生,不屬于保險法上的故意“自殺”,保險人應承擔保險金給付責任。
綜上所述,在自殺免責期間內,依據被保險人自殺時有無民事行為能力來確定保險人是否應承擔給付保險金責任并不合理,應當根據被保險人自殺時的認知能力和控制能力來進行判斷,才更符合保險法上“自殺不賠”的真正意旨。因此,我國《保險法》第44條中“被保險人自殺時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除外”的規定可修改為,“被保險人自殺時處于精神失常狀態,以致不能正常控制其行為的除外”。
(二)復效保險合同自殺免責期間的起算
我國《保險法》第44條第1款規定:“以被保險人死亡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復之日起滿二年后,被保險人自殺的,保險人應當按照合同約定給付保險金。”對于自殺免責期間的起算問題,保險法學界的爭論焦點在于,保險合同復效后,自殺免責期間從合同復效之日起重新計算是否合理。
我國《保險法》第36條和第37條是關于人身保險合同中止、復效條款的規定,保險合同的“復效”是指效力中止的人身保險合同恢復合同效力。對于復效保險合同的自殺免責期間應從何時開始起算,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人身保險合同的復效在性質上應為訂立一個新的保險合同,原保險合同失效后,保險合同中約定的有關期間中斷,自殺免責期間也即中斷,應從復效之日重新起算二年的自殺免責期間。另一種觀點認為,因投保人未能按期支付保險費導致合同效力“中止”而非“終止”,在投保人與保險人達成協議并補交保險費后,原保險合同效力得以延續,保險期間并未中斷,而非訂立一個新的保險合同,故復效后自殺免責期間仍應從最初合同成立之日開始起算。顯而易見,前一種觀點對于保險人更有利而對受益人不利,后一種觀點則更有利于受益人。
主張從復效之日重新起算自殺免責期間,主要目的在于防范被保險人在保險合同效力中止前或中止期間,為使受益人獲得保險金而萌生自殺念頭,在補交保險費及其他費用使保險合同恢復效力后即實施自殺行為。考慮到這種可能性,不重新起算自殺免責期間勢必導致被保險人的逆向選擇,有違保險制度的宗旨。但為了防范這種道德風險發生,將自殺免責期間的起算點重新起算實際上延長了法定的免責期間,這對于大多數由于經濟壓力、職業變化不能及時交納保險費致保險合同中止后又復效,且無自殺騙保意圖的被保險人并不公平,若其在復效后兩年內因各種變故而實施自殺行為,受益人或被保險人的繼承人卻無法獲得保險金給付,這與人壽保險為被保險人遺屬提供經濟保障的基本功能相悖,也使保險人在某種程度上逃避了應當承擔的保險責任。除此之外,保險法上自殺免責期間為二年的設置本身已經對被保險人在訂立合同時可能存在的“自殺換錢”的意圖進行充分考量,是平衡保險雙方利益而確定的折中點,若復效合同重新起算自殺免責期間,將使利益保護的天平大大地向保險人傾斜。何況就復效條款的性質而言,效力中止的人身保險合同恢復合同效力只是原保險合同效力的延續,保險合同中的有關期間并不中斷,自殺免責期間也不需重新起算。
因此,《保險法》第44條關于復效保險合同的自殺免責期間自合同效力恢復之日起算的規定對被保險人和受益人非常不利,過于偏向保險人的利益和經營需要,應當予以刪除,不論保險合同是否存在復效,均應從合同成立之日開始起算二年的自殺免責期間。
四、自殺認定的舉證責任
在保險實務中,自殺認定的關鍵在于被保險人的死亡原因究竟是自主實施自殺行為所致,還是由于意外事故發生所致。在死亡原因并非顯而易見的情況下,合理分配訴訟雙方的舉證責任至關重要。
在人身保險中,自殺條款主要適用于人壽保險合同這種以被保險人死亡作為給付保險金條件的合同。對于壽險合同,只要不是合同中明確規定的除外風險所造成的被保險人死亡,保險人對于其他原因造成的被保險人死亡均負有保險金給付責任,故索賠請求人只需證明被保險人死亡這一保險事故在保險責任期間內發生即可,保險人則必須證明被保險人死于自殺或屬于其他除外責任才能拒絕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在自殺免責期間內被保險人死亡的,若其死亡是由“非本意的”意外事故所致,保險人仍應承擔給付保險金的責任。對于“非本意的”由誰承擔舉證責任存在不同認識:一方面“非本意”本是構成意外傷害的必備要件,似乎應由被保險人一方來證明;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強調“非本意”實際是為了排除“故意行為”,而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通常被列為除外責任,似乎又應由保險人負舉證責任。學界對此問題有兩種不同觀點:
應由索賠請求人負擔舉證責任。主要理由為:(1)如果由保險人承擔舉證責任而使受益人一方最終承受消極的裁判結果,將會使保險金不正當請求事件發生,進而危害保險制度的健康發展;(2)相較于保險人,由與被保險人生活聯系更為緊密的請求權人收集證據更為容易,由此承擔舉證責任更為公平合理。
應由保險人負擔舉證責任。主要理由為:(1)故意免責條款具有決定舉證責任歸屬的特殊法律意義。故意免責條款從設置目的上而言,是保險人基于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而免于承擔保險責任,由保險人承擔舉證責任更容易完成舉證;(2)相對于保險人舉證“故意”,“非本意”的證明對于索賠請求人來說屬于消極事實,當事人只有通過間接證據才能完成舉證。極有可能因為舉證該事故“并非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困難,導致保險合同目的難以達成;對于保險人來說只要能證明被保險人自殺就可免除給付責任,屬于有利于保險人的事實,因此將“非本意”的舉證責任分配給保險人較為妥當。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三)》第21條規定:“保險人以被保險人自殺為由拒絕給付保險金的,由保險人承擔舉證責任。受益人或者被保險人的繼承人以被保險人自殺時無民事行為能力為由抗辯的,由其承擔舉證責任。”在此條規定中,明確了保險人對被保險人的自殺認定承擔舉證責任。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保險立法亦有如此規定,如《法國保險合同法》第62條第3項規定:“被保險人自殺之證明,由保險人負舉證責任。被保險人無意識之證明,由受益人負舉證責任。”我國臺灣地區的司法實務也將“非本意”的舉證責任分配給了保險人,“非故意”的認定對于被保險人而言實屬困難,且保險人通常較被保險人具有更高的舉證能力,證明被保險人的死亡為自殺所致本也屬保險人得以免責的要件,因此由保險人對被保險人的“故意”自殺負舉證責任更為合理妥當。
此外,該第21條還規定,“被保險人自殺時無民事行為能力的舉證責任由受益人或被保險人的繼承人承擔。”在自殺免責期間內被保險人自殺的,若保險人以自殺為由拒絕給付保險金,而要以被保險人實施“自殺”時無民事行為能力為由提出抗辯時,由受益人或被保險人的繼承人承擔舉證責任也更為恰當,理由有二:一是只要能證明被保險人自殺時無民事行為能力,即使發生在自殺免責期間,就能使受益人獲得保險金給付,這是有利于受益人或被保險人繼承人的事實,由其承擔舉證責任較為妥當;二是被保險人有無民事行為能力,實施自殺行為時是否具有相應的認知和判斷能力,是否自愿地追求死亡結果,受益人或被保險人的繼承人基于生活聯系的緊密性更容易收集證據。
注釋:
①[法]埃米爾·迪爾凱姆著.自殺論[M].馮韻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1頁.
②[美]肯尼思·布萊克、哈羅德·斯基珀著.人壽保險(上冊)(第12版)[M].洪志忠,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頁,第154頁,第150-151頁.
③樊啟榮.人壽保險合同之自殺條款研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44條為分析對象[J].法商研究,2009(5).
④吳定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釋義[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頁.
——兼評《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第42條第1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