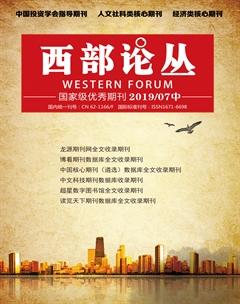民族文化旅游視角下的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包茹婷
摘 要:當今隨著旅游產業的推進,全民進入了休閑旅游新時代,文化與旅游的深度融合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傳統文化的創新與發展,為當地的經濟收入注入了新的力量、為當地的發展提供了新思路。廣西作為少數民族自治省份,多彩的民族、多元的文化在這里熠熠生輝。本文選取廣西省恭城瑤族自治縣作為田野點,以龍虎“河燈節”作為本研究的切入點,重點關注旅游作為一種資本力量介入后,重點關注旅游場域中該地區傳統節慶文化發展的傳承面臨怎樣的機遇和挑戰。
關鍵詞:傳統文化 旅游 傳承 困境
一、介紹恭城瑤族自治縣的文化傳承與發展現狀
恭城瑤族自治縣隸屬于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位于廣西東北部,桂林市東南部,東與富川瑤族自治縣及湖南江永縣交界,南與鐘山縣、平樂縣毗鄰,西接陽朔縣、靈川縣北臨灌陽縣,縣城距桂林市108公里。恭城瑤族自治縣版圖總面積2149平方公里,截至2016年,下轄5個鎮、4個鄉,總人口30萬人,其中瑤族人口約占60%。恭城瑤族自治縣境內地形以山地、丘陵為主,河流沿岸有較為平坦的小沖積平地,全縣東、西、北三面為中低山環抱,中間為一條南北走向的河谷走廊;屬中亞熱帶季風氣候,主要特點有夏濕冬干、夏長冬短、四季分明,光熱充足,雨量充沛等。恭城瑤族自治縣先后獲“中國長壽之鄉”、“全國生態農業示范縣”、“國家級生態示范區”、“國家級可持續發展實驗區”、“中國月柿之鄉”、“中國椪柑之鄉”等榮譽稱號。2018年12月,獲評國家氣候標志。關于傳統文化的特別之處就不得不提到龍虎“河燈節”了。
“河燈節”,是中華民族的傳統活動,也是瑤族兒女的傳統習俗。所屬恭城瑤族自治縣的龍虎鄉龍虎村在每年的農歷七月十四都會舉辦龍虎河燈文化節,至今已經舉辦到了第八屆。龍虎河燈文化節的流程安排每年可能會稍微做些改動,可是大致流程不變,龍虎河燈文化節的主要流程安排有:舞龍舞獅表演、龍虎河燈文化節文藝晚會、龍虎河放河燈以及最后舞龍、水族、排燈的上街游行。
龍虎“河燈節”的表演晚上才開始,下午的時候村民們會在自家門前點紅燭、貢香、燒紙錢,放紅鞭炮然后開飯。晚上的時候,各家各戶就會一同前往會場觀看文藝晚會。龍虎“河燈節”的文藝晚會會場搭建在龍虎村小廣場,晚會開場是龍虎兄弟醒獅團帶來的舞獅表演,表演者都是十幾歲的年輕人。接著再是舞龍隊進入會場,舞龍隊成員則主要是由本村的志愿者和義工團組成。舞獅舞龍表演結束之后,文藝晚會便正式開始了。文藝晚會的節目主要都是以歌舞表演為主,文藝晚會的節目大部分都出自龍虎村文藝隊,除此之外,還有來自其它鄉、村的文藝隊或是恭城縣城的健身隊,甚至還有來自湖南的文藝隊。
文藝晚會開展結束以后,村民們便聚集到龍虎河乘船放河燈,表達對逝去親人的思念,并許愿祈禱。河燈的款式多種多樣,主要以紅色紙燈為主,另外還有五顏六色的蓮花燈,甚至還有發光的塑料河燈。村民游客全都圍在河道邊,成千上萬的河燈漂浮在龍虎河上,形成了非常壯觀美麗的景象,也非常突出地展現了當地的傳統文化特色。
放完河燈,游行便開始了。游行的起點是從龍虎村的關公廟開始游行,一群人浩浩蕩蕩地出發,游行的舞龍隊由志愿者們組成,游行的水族(包括烏龜、蚌、蝦等)都是由本村村民扮演,木偶人游行隊則是由龍虎村木偶藝術團成員組成,排燈游行隊則是由本村村民組成。四種游行項目排列成一條長隊,開始繞著龍虎村敲鑼打鼓進行游行。游行途中,本村村民除了駐足觀看,還有跟著游行隊伍一起走的,游行繞村一圈,最終回到關公廟結束。游行結束,整個“河燈節”就算是告一個段落了。
龍虎“河燈節”無論是從形式和內容,還是舉辦周期來說,都很好地展現了龍虎村的傳統文化特色,也實現了對本村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眾所周知,河燈節并不是恭城縣瑤族所特有的活動,地方的傳統文化明顯帶有地方的特征,在恭城縣龍虎鄉,每年的農歷七月十四,恭城縣龍虎鄉都會舉辦盛大的“龍虎關河燈民俗文化節”來慶祝一年一度的河燈節。河燈節是當地一項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化節日,在節日當天,當地村民們自發攜燈,讓其沿河漂流。河燈萬盞思故人,老百姓通過放河燈的形式寄托對親人的思念,表達對生活的祝福。
傳統河燈節的文化內涵就是老百姓以放河燈這樣一種儀式感的方式來寄托哀思,表達對親人的思念和美好生活的憧憬與祝福,自從單純的民族民間環境變化為旅游場域以來,地方政府與民間學者積極溝通參與,共同聯手打造,將這一個儀式感的活動賦予旅游民俗節慶的意義,推出了民俗文化節,使其不在是簡單地幾盞“燈”,而是更具有了集會、觀賞的價值。現在龍虎河燈節內容豐富多樣,有民俗歌舞表演、放河燈祈福、游龍舞獅、祭祀巡游、品傳統美食等十余項民間活動共同組成,每當盛大的集會當天都會吸引上萬名外來游客前來參與觀看,熱鬧非凡。在河燈節當晚,龍虎鄉民眾與游客們一同來到龍虎河邊放河燈祈福,萬盞河燈沿河漂流,燈式多樣,有飛禽走獸、寶蓮賜福、燃燭其間,滿江輝煌,觀燈人群相互喝彩,共祈祖先保佑,賜福消災,風調雨順。當地群眾與游客們一同放河燈、看表演、嘗美食,歡慶河燈節,讓他們乘興而來,盡興而歸。此次盛會傳承和發揚了龍虎鄉放河燈的優秀傳統文化,賦予其豐富的文化內涵,結合新時代新旅游的北京,同時將當地特色美食、民俗歌舞表演結合為一場豐富的盛宴以廣為廣泛的受眾程度,新的傳播方式,吸引了大眾參與,提高了觀賞性,表現出新的時代特征。這是旅游給予地方優秀傳統文化的新機遇,同時帶動了龍虎鄉旅游經濟發展。
結合當前的時代背景,隨著經濟迅速發展,少數民族地區傳統文化、信仰意識、宗教祭祀等性質的節慶活動被加以開發和利用,是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新途徑,也成為一種地區符合,在旅游場域中被賦予了新的時代特征和更多的內容與內涵。這樣的一種開發和利用,對傳統文化來說是一把利弊共存的雙刃劍,一方面,與時俱進是當代時代背景中各種社會文化發展與生存的必要手段,以更為廣泛的受眾性加之現代化的傳播方式,在保留原生場域中的傳統文化精髓的前提前,更加適應時代的發展、迎合大眾的審美與品味,使其不被淘汰。另一方面,在傳統文化與旅游結合擦出新的火花的同時,對文化本身來說也是新的挑戰,祭祀祖先的活動一直以來是中華民族各個地區所堅持的傳統習俗,有著其本身的嚴肅性與不可娛樂性,就河燈節活動最初的含義來說是向親人表達思念和對美好生活的愿景,這樣的活動在傳統的觀念中是靜謐的,在旅游場域中,被填充了新的內容,與民族民間飲食、歌舞、篝火等集體活動的結合,在活動中,所有的程序如不按照傳統進行,甚至是對信仰的褻瀆,使其在原有的內涵中加入了更多的娛樂性,相反,其神圣性就會有一定程度的弱化。如果丟失了傳統的精髓和民俗活動最初的文化內涵,久而久之,就會被異化的面目全非,甚至丟失其原生性。“神圣性”是人類學一直在探討的概念,它普遍存在于人類社會之中,卻沒有一個量化的標準來進行定義。“神圣”總是與宗教、儀式、信仰聯系在一起,在靈性的基礎上,加上了更高、更絕對的權威感。
筆者看來,在民間傳統信仰儀式進行時,神圣性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空間,傳統文化本身的內涵會隨著不同的時空發生變化,但是在這個場域中,始終彌漫著讓人敬仰、畏懼、神秘的超時空的氛圍是不會被改變的,伴隨著的神圣權威會讓信仰者,自覺地遵守規范。
龍虎“河燈節”已經舉辦到了第八屆,從各方面來說已經比較成熟了,但是通過籌備與全程參與龍虎“河燈節”,我發現了有關龍虎“河燈節”文化傳承的一些不足,具體如下:
第一,從龍虎“河燈節”的流程來看,對比了之前幾屆舉辦的活動內容,現在的流程精簡了許多,變得過于簡單了,以至于感覺內容有點不夠充實,整個“河燈節”下來就只有晚會、木偶戲、放河燈、游行這四項活動。僅靠這四項活動去支撐整個文化節的活動內容,感覺在文化傳承方面沒有突出重點,也沒有形成較為深刻的影響。
第二,從龍虎“河燈節”的舉辦過程來看,總體來說整個活動的順序稍顯混亂,有點條理不清。首先,舞龍作為首場演出展示,按理來說應該最先受到大家的關注,可是舞龍還未登場,舞獅卻已經在舞臺上進行表演,圍觀群眾全都在戲臺前觀看舞獅表演。以至于后面從街上過來的舞龍隊都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直到登臺了才得到大家的關注。其次,木偶戲作為當地的一個特色演出,演出的時間卻和文藝晚會、放河燈的時間重疊了,導致觀眾分流,沒能完整觀看整個文化節的活動節目。
第三,從龍虎“河燈節”的宣傳力度來看,政府對于龍虎“河燈節”的活動開展有一定的宣傳,會在村子集市進出口擺放展牌告知今晚即將舉辦“河燈節”,舞臺也會提前稍作布置。但是,僅僅是這樣還不夠重視,更加達不到文化傳承的效果。想要將“河燈節”作為當地文化傳承下去,就得有足夠的重視,加大宣傳力度,讓每家每戶都對“河燈節”有一個很明確的認識,認識到這是本村的文化特色,需要有一個重視的態度將此傳承下去。
二、建議
基于以上種種我所觀察到的不足,在此我也想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議。首先,關于龍虎“河燈節”的流程問題,因為考慮到時間和精力有限,活動的時間從一整天變為晚上,所以很多流程需要精簡或刪除,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需要改進的就是在有限的時間里,龍虎“河燈節”舉辦方應該要呈現出龍虎“河燈節”最精彩最有亮點的地方,能夠突出重點,讓村民以及觀眾能夠對當地的“河燈節”形成一整套完整的印象。這樣也更加有利于將龍虎“河燈”節形成一整套系統地傳承下去。其次,關于龍虎“河燈節”的時間安排和順序問題,整個文化節舉辦下來,應該達到讓村民和群眾都能全程參與和了解活動的效果,而不是因為時間安排上的沖突讓其只能二選一觀看節目。這樣,也不利于將其完整地傳承。因此,應當適當縮減一點放河燈的時間,刪減多余的節目,將木偶戲表演和文藝晚會表演銜接起來。最后,關于龍虎“河燈節”的宣傳問題,除了在當地集市進出口擺放展示牌的宣傳手段和力度都是不夠的,還應該利用媒體,在網頁網站上宣傳龍虎“河燈節”,給予該文化節應有的重視。讓本村村民意識到自己作為本村人有義務和責任將其傳承延續下去,也要讓外來人了解到本村的文化特色。在這樣“走出去”和“走進來”的過程中,龍虎“河燈節”的文化也就得到了傳承和延續。
三、結論
筆者以廣西省恭城縣龍虎鄉“河燈節”為例,希望通過探討該地極具特色的民間活動在旅游開發作為一種外界力量資本介入的場域中所產生的變化以及如何去傳承和保護進行簡單分析,以期對其他地區類似的情況產生借鑒的意義。具有“神圣”意義的活動,經過旅游開發,其傳統文化本身從內核到外形都不可避免的產生變遷和重構,專門以更為廣泛的受眾程度出現在大眾眼中的文化形態,很可能已經與原有本土民族習俗、信仰產生斷裂。傳統文化本身的適應性也決定了其在新時代背景下面臨生存挑戰的自我革新和重塑的能力。
“河燈節”作為一種節慶,在龍虎鄉傳統文化中占據重要地位,此時正在旅游場域中發生著或大或小的變遷、轉義,為了適應新的環境背景、適應旅游開發,此文化事項被注入了新的文化內涵,豐富了活動內容,產生著文化變遷。雖然商業化所帶來的影響,還有待進行長期觀察,但是通過筆者的了解和調研,現階段旅游開發過程中將“河燈節”帶入“他者”視野后所帶來的無論是經濟的收益還是發展的同階段當地村民們重新審視自己文化而產生的民族自豪感進而產生文化自覺,這也是成為“河燈節”民俗活動更好的傳承與保護的一種外在動力。
“小傳統”并不是一個絕對不變和凝固的文化系統,它是能體現一個社區的傳統心理、價值觀念、民族性格、內在氣質的具有延續性和建構性的系統。在日益開放的村寨場域格局中, 最終走向現代化是每一個民族村寨的必然選擇,然而當市場經濟和大眾傳媒源源不斷地把各種極具現代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態呈現在民族村寨成員面前時,這些文化主體如何在紛繁復雜的誘惑中繼續保持族群身份意識和族群文化認同,是決定上述能動性的村寨文化現代建構能否繼續進行,以及作為“小傳統”的地方性知識能否繼續傳承發展的關鍵性因素。費孝通早已指出, 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即在于文化主體的“文化自覺”。
然而旅游開發這把雙刃劍所帶來的問題也是我們需要關注的內容,通過對這個過程中所引起的問題分析,希望能引起各方的關注,以促進當地傳統文化與旅游業可持續地發展。旅游資源完全因他目的而生成或存在,只是由于人們價值觀的緣故而在一定歷史時期成為旅游資源。相對于旅游而言,它們是自在之物或獨立之象,當人類的審美意識或旅游價值觀不能接納這些物象時,它們仍為原來的功用而存在;當人們的旅游意識垂青于它們時,它們遂成為旅游資源。從這一點看,旅游資源存在著本體和其符號象征之間的復雜關系。一個先旅游而存在的客觀實體之所以成為旅游資源,在于其符號意義的旅游價值。
龍虎鄉目前開發旅游時是以“河燈節”民俗節慶活動作為主要的吸引點,當地旅游設施的建設和旅游活動的展開都是以“河燈節”的傳統的文化內涵以及一定意義的神圣性為基礎的,前文所述“神秘”的轉向也是以它在傳統社會中所積累的一套神圣體系為基礎的。因此,神圣性是祭祀文化的內核,但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的旅游活動卻讓它的生存空間縮小,其內含的一套禁忌和儀式被改寫,導致其象征意義發生轉義,這是否會導致旅游產品的內涵“空心化”現象而引起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問題,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1]
注 釋
[1] 谷尼娜:《從“神圣”到“神秘”——旅游開發下貴州月亮河村布依族銅鼓的人類學研究》,第61頁。
參考文獻
[1] 恭城縣縣志
[2] 桂林文明網:關于恭城縣河燈節盛況報道。
[3] 馬克斯·繆勒:《宗教的起源與發展》,金澤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4] 肖青:《民族村寨文化的現代建構邏輯》,《思想戰線》,2008 年第 3 期,第 9 頁
[5] 謝彥君:《基礎旅游學》(第三版),北京:中國旅游出版社,2011 年,第 113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