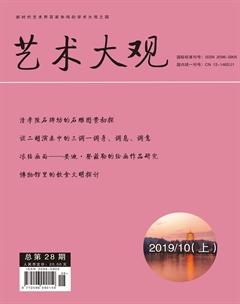淺談《朝侯小子殘碑》
摘要:漢代是中國書法史上一個重要的時代,是隸書書法發展的第一個高峰。而東漢后期是八分隸書入碑的鼎盛時期,書風多樣,一碑一面目,異彩紛呈。本文就是以東漢隸書碑刻作品《朝侯小子殘碑》為對象進行的研究,通過對其歷史背景、筆法、結體、章法等諸多方面的分析、對比與總結,來揭示漢隸書法藝術的獨特魅力,同時兼對東漢時期隸書書風的審美及表現做一探討,希望對當代的漢隸書法藝術創作和研究有些許意義和啟示。
關鍵詞:《朝侯小子殘碑》;漢隸書風;審美價值
一、東漢隸書刻石書風的形成與概述
目前存世的兩漢刻石或原石已毀迭而存有拓本者,共400余種,其中絕大部分屬于東漢刻石,而且在東漢中后期最為集中。這是因為東漢時期統治者十分重視書法教育,靈帝時期設立鴻都門學,使書法教育成為一門獨立的藝術教育。另外,漢代以孝治天下,有舉孝廉制度,社會上崇尚厚葬,樹碑立石以頌其生平的行為成為一種風氣。以上原因客觀上促進了東漢刻石藝術的發展。
隸書,由篆書演變而來,到西漢武帝時期發展成熟,亦稱“八分”“分書”。在諸多東漢碑刻中,以隸書石刻為主,雖然時代相近,但其風格多樣,異彩紛呈。從漢碑隸書的結構特征可以看出:它們有的端莊典雅,如《乙瑛碑》;有的靈動灑脫,如《曹全碑》;有的方拙樸茂,如《張遷碑》;還有的奇古渾樸,例如《西狹頌》。各種風格的漢隸,一起鑄造了書法史上隸書的輝煌。但是東漢時期還有一塊重要的隸書刻石卻很少被當代書家和書法愛好者所重視,此碑為東漢《朝侯小子殘碑》。
二、《朝侯小子殘碑》書法藝術特征
《朝侯小子殘碑》,又稱《小子殘碑》。無立碑年月,碑高84.3㎝,寬81.6㎝。隸書凡十四行,滿行十五字,存196字,碑陰存十字。清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在陜西長安出土,原為周季木收藏,并著錄于《居貞草堂漢晉石影》,現收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此碑上半部分殘缺,首行起為“朝侯小子”四字,故因此而得名。“朝”之上一字已損,即為某朝侯,朝侯是漢代官制。碑主人為某朝侯之子,碑文記載了其學識品格、生前宦跡、去世原因及家屬哀傷之情。
從藝術特征來看,《朝侯小子殘碑》用筆方圓兼備,以圓筆勝,多有篆意,線條粗細變化較少,平實遒勁,橫豎撇捺各有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其在“波磔”的用筆上與成熟時期的隸書碑刻存在較大的差別,這主要體現“燕不雙飛”的漢隸書寫原則上。《小子殘碑》中有多處雙飛甚至多飛的“燕尾”,與西漢后期及東漢早期簡牘墨跡隸書有相近之處,例如“度”“生”“薄”“真”“在”“彥”等字。《朝侯小子殘碑》的結體端莊典雅,方中近扁,筆勢開張,在嚴謹之中又富于變化,趣味橫生。其別具一格的是,碑中多處運用篆書結構,形成了篆隸兼容的獨特風格,如碑中“以、兇”二字完全采用了篆法書寫,還有“雄”字的“厶”部、“曜”字的“日”部等采用篆書書寫,與其他隸書部首組合而成,相得益彰。從章法上來看,《小子殘碑》左右行距略小于上下字距,縱橫之間的對比并不強烈,這與大多數成熟時期的漢隸明顯的“行距小,字距大”的章法形式有些許差別,但整體看來同樣氣勢充盈、端莊典雅。
通過對《小子殘碑》諸多方面的分析與對比,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此碑并非完全成熟的漢隸之作。加之出土時間較晚,受到業界重視,保護得當,被視為漢碑中的珍品,更是不可多得的臨習范本。啟功先生有詩贊曰:“筆鋒無恙字如新,體態端嚴近史晨。雖是斷碑猶可寶,朝侯小子爾何人?”
三、漢隸書風的表現及審美探討
本文名為探討漢隸書風,實則主要討論東漢成熟階段的隸書——“八分”。“八分”一詞大致出現于漢魏之際,它由古隸發展而來,其最典型的用筆特征就是波挑和掠筆,前文所提到的諸多東漢隸書碑刻也均為八分書。在由篆書到隸書的演變過程中,依靠快寫、省略、合并部首等方式,破壞了原有的篆書結構和用筆方法,使得篆書縱長的結字體勢逐漸演變為以橫向取勢的形態,進一步使得原來勻整的純中鋒線條增加了活潑的側鋒用筆,以達到書寫快捷和表現書寫者性情的目的。
清人劉熙載在《藝概》中曾指出:“秦碑力勁,漢碑氣厚,一代之書,無有不肖乎一代之人與文者。”這里強調的正是作為一種特定時代的藝術其獨特的審美特征,通過書法藝術實現社會之象到書法之象的創造性轉化。“氣厚”是漢碑的特質,同樣也是漢文化獨有的特質。
漢文化始終貫穿著以“大漢氣象”為標志的時代精神,在書法藝術上則更是追求端莊雅麗、雄健剛毅的正大氣象,無處不蘊藏著漢代的文化氣息。成熟時期的漢隸刻石,其線條含蓄蘊藉、肅穆敦厚,結體方正,字勢開張,整體看來寓典雅于渾厚、寓靈動于端莊,被自然而然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完美地展現出漢代獨樹一幟的書法風貌和社會氣象。通過以上的分析和研究,希望對當代的漢隸書法藝術創作有些許意義和啟示。
參考文獻:
[1]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編.歷代書法論文選[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作者簡介:王延川(1995-),男,新疆藝術學院書法系碩士研究生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