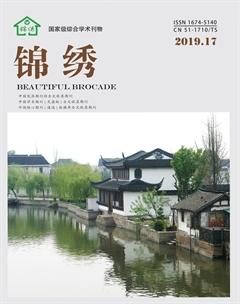嚴歌苓小說中女性形象的多重主體身份研究
摘 要: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女性文學在中國引起了發展過程中的第二次高潮,對于女性文學的研究一直是學界研究的熱門。嚴歌苓作為旅美作家的代表,她和她的作品一直備受關注和研究。小說中塑造的女性人物類型多樣、形象飽滿、各具特色。本文對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多重主體身份進行分析。
關鍵詞:嚴歌苓小說;女性形象;主體身份
在當代文壇中,嚴歌苓有著自己獨特的女性意識。比起男性,她更愛欣賞女性也更愿意寫女性。她對于女性人物的塑造可以看出其有著自己的自身經歷的影響,也有著對女性理想人格的美好幻想。“多重主體身份論”是西方女性文學批評里一個重要理論,用此理論對于嚴歌苓筆下的女性形象身份進行研究,是對女性人物形象的深層挖掘。
一.多重主體身份概念的提出和界定
“主體”作為西方現代性研究的核心概念有其思想淵源。“主體”即主動的、思考的自我,行動的發起者及經驗的組織者。“身份”是人的一種主體意識,”是與對方、與符號文本相關的一個人際或社會角色。”西方女性主義批評家克里斯蒂娃提出“多重異質性”的概念,將“主體”和“語言”這兩個概念聯系在一起,擴展了“主體”的內涵,發展了“無意識主體性理論”。她認為“主體”指使用語言者和在語言使用過程中被建構起來的“主體”。因而強調多重異質性主體的語言建構,來強調主體的變化和流動的特質,這也體現出在哲學角度上完成了對于人的主體性的回歸。在性別身份研究中,克里斯蒂娃認為性別身份存在不穩定性,主張用“女性特質”取代本質主義的“女人”概念,女性特質的符號域與男性特質的象征域共存于同一說話主體身上,它們之間的辯證關系造成主體身份的多元性與可變性。總之,“多重主體身份”是指主體在不同環境即意識形態中、語言結構中不斷發生變化,是在不斷建構指向人性的主體回歸。
二.嚴歌苓小說中女性形象的多重主體身份
嚴歌苓贊賞女性并擅長寫女性。筆下的女性形象多樣,但多承受著苦痛的人生,有著悲慘的人生經歷和境遇。從而深刻地承載著諸如種族、國別、性別等因素的內涵。既有對于西方異質價值觀念的吸收,也有著對于東方的男權文化霸權的妥協。這種在東西方文化的交融中重新建立起對于對東方女性的塑造,使她筆下的女性形象獨具特色。女性形象表現得格外的“弱”而又格外的“強”。因為“弱”到極限便觸底反彈。她筆下的女性形象多變,每個形象不只是一種身份的象征,會因為內部和外部因素的影響進而裂變和錯位而發生變化,所以導致她筆下的女性形象的可塑性強并且獨具魅力。
小漁和男朋友江偉來到異國尋求移民的途徑是為了獲得更好的生活,將未來的生活寄希望于外國這片新奇的世界。從意大利老頭對小漁起初的態度可以看出,老頭對于從中國來的小漁是充滿不屑諷刺和怠慢的,認為小漁就是弱等民族出來的沒有能力給自己創造美好生活的弱勢群體。而多鶴是在中日激烈對抗的戰爭年代,作為中華民族的民族敵人的后代這個身份出現的。這個身份就決定了年幼無知的必定被人凌辱和被仇視的悲慘命運。家國仇恨會首先會體現在人民對異族人民的態度上。起初,多鶴被買回來,張儉和朱小環作為日本人的受害者,對于多鶴則是充滿著憤怒、懷疑、仇視和敵視的。所以首先因為國別的因素,使多鶴成為日本民族罪惡的代言人,而多鶴對于他們來說就是縮小版的敵人。
《小姨多鶴》中的朱小環是個帶有傳統氣息的東方村婦。她有著女性的寬容博大富有犧牲精神和容易感動,她刀子嘴豆腐心。也有著女性的生來熱愛嫉妒的小心思同樣也善于結交朋友拉關系,這種通靈的性情使她為張家帶來了不少好處。她活的很明白,有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學。她的口頭禪透露著她的人生哲學,“湊合吧”。她愛張儉,也幸運地獲得了張儉大半輩子的寵愛。她識大體,通情達理地接納了一個日本女子接替她完成她一輩子都不能完成的給張家傳承香火的事情。她為張儉和多鶴騰地方讓他們盡快完成任務生出孩子。一方面自己心里也很酸楚,想著自己要和另外的女人共同分享自己的丈夫,她就氣不打一處來。但時間久了,她對多鶴產生了同情……。在幾十年的相處中,小環摸索出了和張儉和多鶴相處的方式,她懂得怎樣站在一個合適的位置去平衡三個苦命的人。
三.時間的變遷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女性的選擇
《天浴》中的大學生文秀,在文革的慘痛經歷中,“大學生”這個身份已不再閃光,知識分子的身份已不能給她帶來任何優待和庇護。甚至與普通人相比,她是更容易被當成侵犯對象的人。特殊境遇下,人性異化,為了能有個更好的出路,她必須先返城,而在那個慘絕人寰的時代下,知青返城是奢念。返城的代價是必須犧牲掉一些東西,而文秀沒有其他的什么,她只剩下自己了。為了生存她放下了自尊,放下了知識分子的高傲,出賣肉體,賤賣靈魂。她把希望都寄托在得到她的男人身上。而這些男人根本也沒想要真正地幫她返城,有的根本就沒有能力幫助她,他們想的只是一時快感,滿足自己無處釋放的性欲。所以不知不覺中,文秀變成了一個癡癡等待著被別人幫助和別人解放的期待返城的“妓女”,誰都可以嫖。至此,她完成了由“知青女大學”到“妓女”的身份的轉變。文秀最后以“死”來解脫自己,解放了自己的骯臟的身體和早已丟失了信仰的心靈,她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的犧牲品。
“時間”和“環境”的因素對于日本孤女多鶴身份的改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剛被買回來被叫做“小日本婆子”的時候的多鶴僅是個是年幼的日本女孩。她的身份是隨著她在張家跟張儉發生了關系,成為了張儉孩子的母親時變成了為張家傳宗接代的工具。而之后的幾十年,多鶴用她的小小的肉體架起了和張家的橋,打破了和張家的隔膜和陌生。隨著他們的幾次遷居,國家的意識形態、周圍的環境和人際關系都發生了變化。多鶴參與到張家的大事小情中,并進入到了兩人的感情中,占據了張儉心中的部分。她一生似妻非妻,似妾非妾,但她也成為了張儉的愛人,成為了張儉情感的寄托。進而在這個家中,她變成了張家的不可或缺和無法割舍的一部分,張家人的親人。在她回日本之后,她才發覺到她回日本已經晚了,日本也已經沒有她的位置了。她記憶中的快樂源泉依然是在張家做“朱多鶴”的日子。她這一生在中國的時候是“異居者”,在日本的時候依舊是“外國人”。
四.嚴歌苓小說中女性形象多重主體身份的研究意義
對人性處于劣勢地位的反思。“人被宣稱為應當是不斷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個在他生存的每時每刻都必須查問和審視他的生存狀況的存在物。人類生活的真正價值,恰恰就存在于這種審視中,存在于這種對人類生活的批判態度中。”她透過歷史的變遷中人性角逐的浮光掠影,觀察出時代、政治和社會給人性帶來的扭曲異化,同時也是用個體悲慘的遭遇來完成對于主流文明的反思。她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并不單一,而帶有立體感,都是在種族、國別、階級、性別本體和情感的因素的影響下在不同的身份中變化。在嚴歌苓旅美之后,處于東西方文化形成沖突的視角下,她是希望超越種族、國別、階級等因素,因為超越了這些因素后,觀呈現的隱藏在背后的人性。
對移民歷史進行審視和批判。以嚴歌苓為代表的新移民女作家,由于異居經歷而帶來的飄零感,她們的創作中都會表現出思鄉渴望重現母國文化中的優質部分的意思。在敘述中國時,她們在力圖上升到現代史觀的角度透過女性個體的生命歷程,建立一種區別于主流話語即父權話語的新的歷史觀。同時賦予“女性”以民族意義,給予她們的人物身份以豐富的闡釋,以此來表達對母國文化和精神家園的認同。只是在這種文化認同中并不構成對于異鄉文化的否定和抗拒,而是吸收不同文化和價值觀作為自己創作和思想的資源,從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一方面表明對中西文明的尊重,另一方面表明對于西方文化霸權主義的挑戰的態度。
多元文化沖擊下的身份認同。嚴歌苓筆下的移民女的多重主體身份代表著她們不同的選擇。她們在異國的文化語境中扮演著“邊緣人”的身份處于“他者”的地位。既在本國文化的邊緣也在異國文化的邊緣中生存,自然有迷失感,從而會產生身份認同的危機。“嚴歌苓是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小說家,在她的筆下自尊的敏感并非刻意要在人物身上雕鏤出什么可貴的美德,而是旨在表現人被置于某一境遇時的反應,是想寫出恐怕只有小說才能寫出的微妙感覺……。”通過對于多種女性形象的塑造,為我們展示了移民女性在異國的文化語境中的“邊緣人”的位置。她們帶著對于本土文化生活的記憶,自身帶有本土文化特質,作為本土文化意識的傳承者。
體現嚴歌苓塑造理想的女性人格。嚴歌苓說“我覺得女人比男人更有寫頭,因為她們更無定數,更直覺,更性情化。”她創造的女性形象都十分美好,既有傳統中國女性的一切美好的品質,也有著各自的獨特魅力。但是縱觀她筆下的各種系列的女性,可以說形象都過于美好,過于理想。也可以說這正是嚴歌苓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嚴歌苓自身有著很強的中國情結,但并不意味著她的創作中就有著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完全的回歸。她將異域生活稱為是“生命移植”,證明了異域的文化充實了她的生命,她的創作中有著在東西文化的交融和沖擊下對于傳統東方文化的再敘述,表現為對于中國傳統女性的優良品格的贊美。又有著對于西方的異質文化的優質部分的吸收,表現為她讓女性在身份的轉換中帶上了西方文化中的現代性的品格。
表達對于美好人性的禮贊。移居海外后的嚴歌苓的創作,將自己筆下的人物進一步走進歷史的深處,與歷史環境的變化一起成長和蛻變。但無論她的筆偏向東方視角還是西方視角,表達和贊美“人性”永遠是她關注的焦點。《天浴》里她描寫了一個純潔少女在歷史環境的扭曲中被玷污的過程,但少女仍然閃爍著美好的光;《扶桑》里刻畫出一個“神女”的弱到極處的自尊和強大,如同阿Q自欺欺人的反抗和激勵。她寫《少女小漁》一個不諳世事的少女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陷入生活的圍城,卻用自己的善良真誠感染著身邊的人。對于西方人來說,他們的身份是“看客”,中國女性是“被看者”。他們看待東方女性是帶著一種把玩的眼光像看待玩具一樣。在這樣卑微的處境中,嚴歌苓賦予他們帶有中國特質的美好的品質:勤勞、堅忍和善良,閃耀著“母性”和“雌性”的光輝。
五.結語
在父權社會中,女性始終處于邊緣的位置。但在嚴歌苓的小說中,女性人物是她關注的重點。她筆下的女性人物的主體身份復雜多變體現著她的女性意識。我們從嚴歌苓對于身份書寫的創新中,可以挖掘出影響女性主體身份發生變化的因素以及發生了哪些變化。對于嚴歌苓小說中女性多重主體身份的研究,對探尋女性移民在異國的生存境遇和身心的變化,對全球化浪潮下反思社會、歷史和政治和人性有很大幫助。嚴歌苓的寫作,促使女性文學的發展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向更加具體的方向和角度延伸,也開闊了跨文化寫作的視域。
參考文獻
[1]陸貴山等.中國當代文藝思潮[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2]劉迪.“地母”精神及“雌性”書寫下的女人[J].名作欣賞,2016.29.
[3]汪禮霞.繞指柔的多情:情愛與母愛的錯位寄托[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5.4.
作者簡介:
孫瀅韜(1997.06-),女,朝鮮族,吉林省吉林市人,吉林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