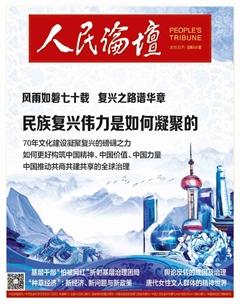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理論探索與范式突破
朱康有
【摘要】70年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理論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積淀在分科教材的建立和完善中,體現(xiàn)在研究方法的拓展和改進(jìn)中,顯示出了理論和制度、社會(huì)之間的良性互動(dòng)。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進(jìn)入新時(shí)代,“復(fù)興”喚醒了中華民族對(duì)自我文化傳統(tǒng)的肯定,面對(duì)寬廣的世界舞臺(tái),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理論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已經(jīng)勢不可擋。
【關(guān)鍵詞】傳統(tǒng)文化 理論創(chuàng)新 研究方法 【中圖分類號(hào)】D60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面臨的一個(gè)主要問題是,社會(huì)主義制度在具體國度的建立和鞏固并非單純依靠作為外來科學(xué)理論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內(nèi)含的普遍性所能解決。其既需要結(jié)合來自國情的實(shí)踐層面,又不能離開深厚歷史文化的影響。先進(jìn)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很早就意識(shí)到重構(gòu)新社會(huì)的這種特殊性(用今天的話講,就是“特色”,就是“中國化”),并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就是同中華傳統(tǒng)文化精華相融合、與中國具體實(shí)踐相結(jié)合的過程。當(dāng)前,歷經(jīng)70年的曲折發(fā)展,通過革新和轉(zhuǎn)化,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與發(fā)展逐漸融入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文化建設(shè),成為新時(shí)代引領(lǐng)民族復(fù)興的一股強(qiáng)大精神力量。
傳統(tǒng)思想文化研究邁入現(xiàn)代
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從一個(gè)自信的“天朝大國”淪為一個(gè)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huì)國家。面對(duì)“千年未有之變局”,有識(shí)之士本能地以“中學(xué)”之“體”,融吸大規(guī)模傳入的西學(xué)之“用”,卻未能在短期內(nèi)“破局”。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各種改造社會(huì)的思想文化紛紛涌入,西學(xué)占據(jù)上風(fēng),全盤西化漸成潮流。在此背景下,人們發(fā)現(xiàn),作為科學(xué)的“西學(xué)”,其最大特征便是分科化、學(xué)科化。代替科舉制而興起的近代高等教育,充分顯示了這一點(diǎn)。于是,建構(gòu)現(xiàn)代世界眼中的“傳統(tǒng)”成為當(dāng)務(wù)之急。但拿什么作為參照物呢?主要就是西學(xué)的觀念及其結(jié)構(gòu)。作為最先進(jìn)的理念,源于西歐和蘇聯(lián)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dǎo)學(xué)界從整體上建立起了具有“分科體制”特征的傳統(tǒng)之學(xué),這可以說是傳統(tǒng)思想文化邁入現(xiàn)代的重要標(biāo)志性體現(xiàn)。
需要指出的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不能說是沒有“分科”,只是其“經(jīng)史子集”的粗化類分、“小學(xué)”與“大學(xué)”的獨(dú)特區(qū)別,不太適合現(xiàn)代知識(shí)的歸類。即便是最為重視編年記載的傳統(tǒng)史學(xué),與現(xiàn)代歷史學(xué)科仍有一定距離。一個(gè)文、史、哲相對(duì)不分的傳統(tǒng)文教系統(tǒng)必須進(jìn)行拆散后的重新編排、整理。由此,中國傳統(tǒng)政治思想、中國傳統(tǒng)法治思想、中國傳統(tǒng)軍事思想、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濟(jì)思想、中國傳統(tǒng)倫理思想等按照現(xiàn)代寫法的分科教材相繼進(jìn)入教育體系。
盡管這些體系在今天看來仍免不了“西化”和“馬化”(馬克思主義化)的痕跡,但從客觀上講,其為我國的社會(huì)主義文化建設(shè)作出了獨(dú)特貢獻(xiàn)。由于受慣性的“革命”式思維制約,過去我們是論批判多、談繼承少。20世紀(jì)80年代后,這種狀況得到了改觀,對(duì)傳統(tǒng)文化正面功效的弘揚(yáng)日益增多。比如,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xué)史、中國美學(xué)史、中國古代文學(xué)史等,相繼走出了“蘇式”教科書模式,真正用中國人自己理解的馬克思主義進(jìn)行編寫。這反映了改革開放后理論研究的革新與沉淀,凸顯了基于客觀的歷史主義邏輯方法的進(jìn)步。
新時(shí)代,中華傳統(tǒng)文化正以其積極價(jià)值鍥入人們的生產(chǎn)生活之中,未來必將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正如《關(guān)于實(shí)施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的意見》指出的,我們“迫切需要深化對(duì)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重要性的認(rèn)識(shí),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價(jià)值內(nèi)涵,進(jìn)一步激發(fā)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生機(jī)與活力;迫切需要加強(qiáng)政策支持,著力構(gòu)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體系”。
理論探索方法和范式的諸多新突破
教材編輯背后的理論研究創(chuàng)新,源于探索方法的變革。傳統(tǒng)的學(xué)術(shù)研究方法離不開“訓(xùn)詁”和“義理”兩條路徑的循環(huán),但現(xiàn)代學(xué)人開創(chuàng)的研究方法則更為多元。
運(yùn)用自然科學(xué)的方法進(jìn)行研究。比如,放射性同位素在現(xiàn)代考古學(xué)中的應(yīng)用,能夠比較精確地推斷歷史事件的發(fā)生時(shí)間。橫斷性學(xué)科的系統(tǒng)科學(xué)方法出現(xiàn)以后,被應(yīng)用到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領(lǐng)域,有學(xué)者甚至將之貫穿到佛學(xué)文化的體系探索中,寫出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佛教哲學(xué)著作。
廣泛采用邏輯工具。中國古人的著作(包括經(jīng)典)絕大部分沿用“語錄體”“章句體”,散漫無常,生活在現(xiàn)代社會(huì)的人們很難理解,而新式教育則改變了現(xiàn)代人的閱讀和理解方式。學(xué)者利用邏輯進(jìn)行多方面的整理分析,使傳統(tǒng)文化更加立體地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
中西對(duì)比的多元融合。在不斷學(xué)習(xí)“西學(xué)”的過程中,中國人被賦予了更寬廣的世界視野。尤其是20世紀(jì)80年代后持續(xù)深入、不斷擴(kuò)大的改革開放,使人們具備了全球化的視野,互相對(duì)比成為可能。由此,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開始登上國際舞臺(tái),散發(fā)出耀眼的光芒。中國學(xué)者可以通過英語向國際社會(huì)介紹中華文化,而國外的漢學(xué)家可以對(duì)中華文明進(jìn)行旁觀者的解讀,通過相互吸收以及相互借鑒推動(dòng)不同視域的融合。
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廣泛滲透。馬克思主義一直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指導(dǎo)思想。從實(shí)際出發(fā)的觀念、辯證法的結(jié)構(gòu)邏輯、認(rèn)識(shí)論的理性辯護(hù)、唯物史觀的科學(xué)方法,都貫穿于歷史文化的各個(gè)領(lǐng)域,亦將長期延續(xù)下去。比如,二十世紀(jì)五六十年代侯外廬等著的《中國思想通史》(五卷)代表了當(dāng)時(shí)運(yùn)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的較高水平,讓人們?cè)诰幠牦w、紀(jì)傳體等寫作方法之外,從社會(huì)生產(chǎn)力、階級(jí)利益差距視角看到了不同的側(cè)重點(diǎn)。
理論和制度、社會(huì)之間的良性互動(dòng)
文化理論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不是孤懸的,而是和制度以及社會(huì)緊密相關(guān)的。來自于制度和物質(zhì)層面的文化,或能推動(dòng)、促進(jìn)抽象理論的發(fā)展,或能抑制、遲滯觀念王國的創(chuàng)新。當(dāng)然,它們之間的關(guān)系是復(fù)雜的,并非簡單之“極化”,亦非完全同步。70年來,我們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許多態(tài)度和做法,反映了文化視域下理論和制度、社會(huì)之間的良性互動(dòng)。
理論能否轉(zhuǎn)化為制度,關(guān)鍵在于政治領(lǐng)導(dǎo)人是否倡導(dǎo)。“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yīng)當(dāng)給以總結(jié),承繼這份珍貴的遺產(chǎn)。”這是毛澤東同志一個(gè)極為精彩的理念。由此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共產(chǎn)黨的杰出領(lǐng)袖,并不是“書齋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其閱讀的馬克思主義文獻(xiàn)、文本可能比相關(guān)專家要少,但無疑抓住了改造社會(huì)的關(guān)鍵,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由理論形態(tài)不斷向現(xiàn)實(shí)轉(zhuǎn)化、飛躍。毛澤東同志一直極其重視中國古代文化,他所閱讀的絕大部分書籍也都是中國古籍,而這種身體力行的做法無疑影響了黨內(nèi)外很多人。比如,第一代領(lǐng)導(dǎo)集體的很多成員都有著深厚的國學(xué)修養(yǎng),不自覺地把傳統(tǒng)文化作為治黨、治軍的潛在本領(lǐng),并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為現(xiàn)實(shí)的運(yùn)動(dòng)過程。周恩來同志曾說,“我們中國人辦外事,有這樣一些哲學(xué)思想。要等待,不要將己見強(qiáng)加于人。當(dāng)雙方爭執(zhí)不下時(shí),強(qiáng)加于人反而容易壞事,最好的辦法是等待對(duì)方自己覺悟……這些哲學(xué)思想來自我們的民族傳統(tǒng),不全是馬列主義的教育”。革命的“反叛”性格和經(jīng)歷,并沒有使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西化”和“復(fù)古”的兩極中搖擺,反而使他們?cè)诟脑飕F(xiàn)實(shí)社會(huì)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主見”。
總體來說,國家意識(shí)形態(tài)對(duì)理論的呼應(yīng)是積極的、有效的。從歷史上看,學(xué)術(shù)殿堂上的“話語”轉(zhuǎn)化為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需要假以時(shí)日。較早映入高層視野的是“中華傳統(tǒng)美德”提法,隨后,“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等術(shù)語逐漸進(jìn)入黨和國家的綱領(lǐng)性文件中。比較突破性的表述來自于黨的十八大、十九大報(bào)告,來自于習(xí)近平總書記的有關(guān)重要講話和重要思想。比如,黨的十九大報(bào)告把中國共產(chǎn)黨定位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忠實(shí)傳承者和弘揚(yáng)者,把傳承和發(fā)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作為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文化強(qiáng)國的重大戰(zhàn)略任務(wù)。可以預(yù)見的是,未來這種趨向?qū)⑾破鹄碚摻缪芯康母叱薄?/p>
需要說明的是,在70年的曲折發(fā)展中,或許有一些令人不快的經(jīng)歷(本質(zhì)上是近代以來將“傳統(tǒng)”視為沉重包袱、丟棄而后快的社會(huì)心理的承繼)。比如,“破四舊”運(yùn)動(dòng)導(dǎo)致了社會(huì)混亂,使得一些珍貴的文物或毀壞、或丟失。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展開以及不斷深化,思想文化的混亂局面逐步扭轉(zhuǎn)。 20世紀(jì)80年代,“國學(xué)熱”重回神圣學(xué)術(shù)殿堂,民間的、官方的研究不絕如縷,推廣傳統(tǒng)文化的社團(tuán)、機(jī)構(gòu)如雨后春筍般不斷出現(xiàn)。同時(shí),傳統(tǒng)文化理論層面的探索,也不再是封閉的“象牙塔”之學(xué),而是和百姓的信仰、企業(yè)的經(jīng)營管理、全民的德治理念等相結(jié)合,并漸漸進(jìn)入體制內(nèi)的教育。
當(dāng)前,從理論到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全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在“復(fù)興夢”的理想旗幟下,形成了對(duì)科學(xué)歷史思維重要性的共識(shí)。“復(fù)興”喚醒了中華民族對(duì)自我文化傳統(tǒng)的肯定。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的偉大中華民族,把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作為自信之本,昂然闊步,邁向未來。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進(jìn)入新時(shí)代,我們不再是被動(dòng)地進(jìn)入世界歷史,而是做好了主動(dòng)融入全球化的積極準(zhǔn)備。如果說一百多年以來我們更多的是在世界的影響之下,那么強(qiáng)起來的中國則是以平治天下、關(guān)懷人類命運(yùn)的心胸,秉承四海一家、天下為公的精神,努力為完善全球治理貢獻(xiàn)自己的智慧。在改革開放全面深入的新時(shí)代,各民族的精神產(chǎn)品已經(jīng)成為公共財(cái)產(chǎn),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可以說,面對(duì)寬廣的世界舞臺(tái),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理論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已經(jīng)勢不可擋。
(作者為國防大學(xué)國家安全學(xué)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