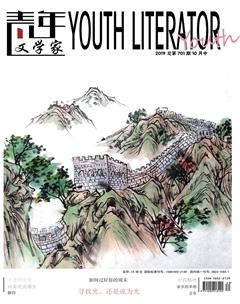論凌叔華小說中的女性形象
摘 ?要:凌叔華從自己的生活環境和時代背景出發,著重刻畫了五四這一新舊時代交替中的三類女性形象,即舊女性、新舊夾層中的女性、新女性,關注女性群體的生存狀態。常用冷靜客觀的筆觸與諷刺的語言描述女性悲劇的人生。
關鍵詞:凌叔華;五四時期;女性形象
作者簡介:王靖萱(1997-),女,漢,黑龍江蘭西人,在讀研究生,現當代文學方向。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9-0-02
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啟了一個歷史的新階段,在倡導平等與自由、科學與文明的時代氛圍中,“人”逐漸走出家庭的藩籬,突破封建血緣宗族的桎梏,開始了尋找自我的歷程。在這一歷史時期中,個人獨立的存在和價值成為人們追尋的目標,而有悖于此的封建綱常倫理則遭到了無情地撻伐,不再做“父親的孩子”成為“人”的呼聲。在“人的解放”這面大旗之下,我們看到了女性的身影。
這時期登上文壇的凌叔華和其他女作家一樣,著眼于女性的生存狀態,思考女性的人生道路以及面臨的種種現實問題,從女性的心理流變出發,刻畫出舊女性、新舊夾層的女性以及新女性這幾類人物形象。凌叔華看到在五四思想的沖擊下,社會歷史的急劇變遷中女性命運的變化,細膩的體察到她們內心的巨大波動,從她們與外面世界的沖突中,看到了女性根深蒂固的封建觀念,看到她們自身的弱點,同時也看到社會整體意識的落后對女性徹底解放的羈絆。魯迅評論凌叔華的小說:“恰和馮沅君的大膽,敢言不同,大抵是很謹慎的,適可而止的描寫舊家庭中婉順的女性,即使間有出軌之作,那是為了偶受文酒之風的吹拂,終于也回復她的故道了。這是好的——使我們看見和馮沅君,黎錦明,川島,汪靜之所描寫的絕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態的一角,高門巨族的精魂。”基于此,本文將具體闡述凌叔華筆下的女性角色畫廊。
一、舊女性
凌叔華出身于封建名門,她與其他女性作家不同的是,她并沒有從封建家庭中急劇的脫離出來,而是以其細膩的眼光體察父權制下女性的生活現狀,挖掘出人物內心的情感走向,冷靜客觀的講述著舊女性的辛酸,隱晦的表達出自己的同情,同時也流露出諷刺的意味。凌叔華筆下的舊女性大體分為兩類,舊式少女和舊太太。
凌叔華擅于描寫閨閣中的少女,她在《繡枕》中塑造了大小姐這個典型人物。這位大小姐聽從父親的話,精心的繡了活靈活現的鳥,縫在了枕套上,打算送給白總長,從而期待白總長家的二兒子能夠娶自己。而大小姐對于這種盲婚啞嫁的方式的態度是認可和期待的,她是父親的好女兒,乖順且毫不反抗。她甚至想象著自己嫁到白家后能夠著華美的衣裙惹來小姐妹們的嫉妒和艷羨。而丫頭手中不復原樣的鳥兒卻打破了大小姐的幻想,她意識到自己精心準備的繡品沒能受到重視,自己并沒有被選擇。凌叔華在《繡枕》中第一次著眼于女性內經驗的探求中,繡枕成為了一個把女子物化的明顯表征。 在這里, “繡枕”本身就是一個象征:“不僅暗示著男性社會對女性的粗暴蹂躪, 而且似乎也表現出整整一套上流社會的優雅與美, 連同這位舊式高門巨族的大小姐一道, 逝去了黃金時代并再沒有生路。”同時,這也表現出男性話語下對女性的要求,繡工成為衡量女子品行的工具,而且繡品與女子的價值都來自于男性的衡量,大小姐的生存空間在封建家長制下不斷被壓縮,整個文本具有著鮮明的悲劇色彩。
當舊式少女進入到家庭之后就變成了舊式太太,她們也是凌叔華描摹的對象。這群舊太太基本沒有活力,她們虛榮、迷信、整日討好丈夫,十分壓抑。《中秋晚》中的敬仁太太把婚姻不幸歸咎于丈夫沒有在第一年中秋節的時候吃團鴨。她確信,“吃過了團圓宴,一年不會分離”。而表姐的去世使得二人發生口角,團鴨也沒能吃上,事后丈夫打破了供神的花瓶,這些“噩兆”給敬仁太太的心中埋下了種子,她深信正是這些事件導致了自己婚姻的不幸福,而丈夫的放浪形骸以及二人四年后的流離失所在婆婆、母親以及敬仁太太本人看來都是命中注定的。這充分表現出女性主體性的蕩然無存,她們的思想觀念在封建倫理制度的戕害下麻木、愚昧,把希望寄托于迷信之中,是標準的封建家庭婦女的典型代表。
更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福氣的人》中的老太太,一個如《紅樓夢》中賈母一般成功的人也未免遭后輩惦記家財,里子遠不如外表一般光鮮亮麗。凌叔華通過對這些舊女性的塑造,表現出封建倫理制度對其精神上的戕害,同時也表現出舊女性自身對封建觀念的認同與依賴,讓后人理解五四精神傳播開來的現實意義及必要性。
二、新舊夾層的女性
成長于五四時期的青年男女一直以來接受封建倫理制度的教育,骨子里淫浸著封建的思想觀念。隨著五四思潮的不斷傳播,社會意識與禮儀文化有著極大的變化。因此,青年男女原本的思想觀念受到了沖擊,他們徘徊于新舊觀念之間,具體表現在女性對與異性交往中的不適和對禮儀行為的過分解讀。
《吃茶》中芳影的生存空間較之于《繡枕》中的大小姐的大了許多。“近年她見社會潮流變了,男女都可以做朋友,覺得這風氣也得學學。”但是,她并不真正的了解新式文明下的文化,所以她對于異性交往之間的禮儀行為有著極大的誤解,具體表現在芳影在與王先生的交往中很不自信,不知道怎樣自然的與王先生聊天。當王先生表現出紳士作風時,芳影誤以為他對自己有好感,甚至想與王先生走入婚姻,當得知王先生身有婚約之后才意識到外國規矩的不同。凌叔華對準女性的內經驗與外部環境的沖突,塑造出了一位社會轉型時期的女性,她代表著社會巨變中的一類人,她們在一場場鬧劇與誤會中逐漸成長,在融入新式文明的交往中持續掙扎。
《茶會以后》中的阿英和阿珠在新式文明的交往中成長起來了,她們已經能夠分清紳士行為與愛慕行為的不同,不太可能發生“芳影”式的笑話了,但是,更加尖銳的問題卻凸顯了出來,處于新舊時代夾層的女性對自己的未來處于相當迷茫的狀態。她們從舊式文明中逐漸走出,脫離了父權制包辦婚姻的嫁娶形式。可是,她們在現代以茶會為約會形式的相親模式中,直接的被適齡男性挑選,從而進入到另外一個披著文明外套的深淵。換句話來說,她們把婚嫁的主動權由父輩轉讓給了“看得上”她們的男子。但是,在現代文明的婚姻嫁娶習俗中,兩姐妹表現出無所適從的狀態,“其實我最怕同男子說話,我同男子說話,覺得很不舒服,樣樣都得小心。”她們還未做好完全融入到新式文明的準備,可是現代文明也對她們關上了大門,使得她們只能在新舊的夾層中徘徊。
在社會轉型時期,有一種工薪太太群體不容忽視。她們可以看做是芳影和兩姐妹生活的延伸。她們接受舊式的包辦婚姻同接受過教育的丈夫共同組成家庭,形成一種不匹配的組成方式。《送車》中白太太與周太太是第一批工薪太太的典型代表。她們是家中的寄生蟲,與丈夫無法達成有效的交流,她們是沒落封建意識形態的保護者,慣用精神勝利法來麻痹自己的神經,幾位太太在如何管教傭人方面找到成就感,在挖苦其他不被愛的女人身上找尋安慰。而《太太》中的舊式太太把人生的意義寄托于賭桌,虛榮的變賣家中僅剩的物件不顧女兒御寒的需要在賭桌上維持面子。她們承襲了舊社會中女子的不通文墨,卻沒有能力做到新女性的獨立自強,于是只能在新舊的夾層中麻木的生活。
凌叔華透過對于新舊夾層中女性的描摹,深度挖掘了女性與歷史及進步之間的微妙關系,從而引發我們隊社會轉型時期對于女性生存狀態的變遷以及女性心理意識的嬗變的思考。
三、新女性
凌叔華較之于同時期的冰心、廬隱、馮沅君等女性作家的高明之處在于她關注新女性在取得戀愛自由的權利后所面臨的問題,這與魯迅先生提出的“娜拉走了之后會怎樣”頗為相似。她敏感地認識到女性通過自由戀愛進入到婚姻之后并不是最后的歸宿與結局,她們仍舊有著難以言說的境遇。
《酒后》和《春天》之中都存在一個外來因素,作為“他者”進入到新式的夫妻生活。采苕向丈夫永璋傾訴自己對于好友子儀的傾慕,她在酒后表露出想親吻子儀的愿望。而宵音也在生活的倦怠期中回想起從前向她表露心跡的愛慕者。二人對異性的別樣情愫表現出女子對于婚后從屬于男子的不認同,以及對于表現主體性的迫切。可是,采苕的“沒什么,我不要kiss他了”又表露出新女性主體性的匱乏。她們在進入婚姻生活之后,必須控制自身情感的表達,壓抑自己的情感沖動,做好“妻子”這一社會角色。
而《花之寺》中的燕倩克服了自身的情感表達沖動,完美的進入到了“妻子”的家庭角色之中,她所面臨著問題是如何走出情感的倦怠期。她充分運用知識女性的聰明才智,以一個愛慕者的口吻給丈夫寫信,邀請丈夫出去游玩,增添婚姻生活的情趣。可是,這卻暴露出知識女性必需在家中經營婆媳關系,接人待客,處理雜事,困頓與家中事物難以脫身,而且她與丈夫之間的婚姻出現了細微的裂痕。同時,燕倩始終借助別人的語言來在表達自我,側面顯現出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失語以及主體性的缺失。燕倩在結尾對丈夫的嗔怪“難道我就不配做那個出來贊美大自然和贊美給我美麗靈魂的人嗎?”這也暗示了知識女性在走進婚姻后,對于自我主體價值的迷失以及成為“妻子”后的做出的犧牲表示委屈,也間接傳遞出燕倩依附于丈夫的心理。《他倆的一日》中的年輕夫婦也同樣處于婚姻倦怠期,經過二人一天的甜蜜相處,筱和認識到二人當日的甜蜜是因為分居時間長而促進的,于是她反省自己的婚姻并決定利用分居來刺激二人的婚姻。筱和和燕倩都是理智的、智慧的妻子,她們用自己的智慧解決婚姻中出現的問題,也表現出婚姻生活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客觀現實。
凌叔華還塑造了更加勇敢的女性形象。《再見》中的筱秋在見到駿仁先生之初還留有對他的傾慕,應邀做客并答應送駿仁先生自己的照片。但是,接觸下來,筱秋發現駿仁先生已經變成了油腔滑調、頤指氣使的人。于是,她斷然地拒絕了他。這充分彰顯出女性在自由戀愛中的選擇權與自主權,這是《繡枕》里的大小姐想也不敢想的行為,充分顯現出女性的獨立以及主體性的提高。而《綺霞》中的女子在進入婚姻之后,深陷于拉琴與處理家務難以兩全的矛盾之中,綺霞也嘗試過在婚姻中平衡兩者之間的關系,但是當她發現兩者無法平衡時,她就從婚姻生活中退出來,出國學習音樂。可是,在學成歸來后,丈夫已經另娶了太太。這充分體現了凌叔華對于職場女性對于如何平衡婚姻和事業問題的探討,也表露出女性在理想與婚姻之間難以兩全的實際情況,女性只能不斷地犧牲自己以實現婚姻的和諧。
凌叔華以她所熟悉的環境及女性群體出發,以冷靜客觀的語調、刻畫出一部女性的心靈史,在五四時期的浪潮的沖擊下,她關注與對人的發現、對女性的發現,真實地反映出不同女性在新舊文明沖撞時期的生存狀態和主要困境,以人文的視野來關懷女性的生存空間與自我表達,表現出她同其他五四女作家不同的特質。
參考文獻:
[1]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A].魯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2]劉思謙.女性角色人物畫廊——凌叔華小說人物談[J].河南大學學報,1992.
[3]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4]陳學勇.高門巨族的蘭花——凌叔華的一生[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5]張培.春夏秋冬:凌叔華筆下的女性世界[J].名作欣賞,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