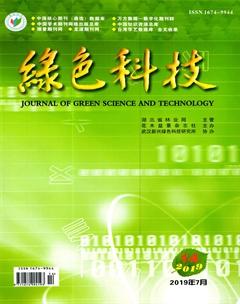農村居民點整治中利益相關者博弈分析
李佩恩 陳怡君 劉小波 匡垚瑤


摘要:在界定利益相關者的基礎上,闡述了農村居民點整治過程中各利益主體的行為偏好,運用博弈矩形,分析利益主體在整治中的博弈行為,探尋了影響各利益主體博弈的相關因素。研究結果表明:完善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經濟考核指標,加大對地方政府的懲罰力度,能夠有效抑制地方政府的違法整治行為;提高農民的整治補償收益,建立健全公眾參與機制,能增加農民對整治工作的支持力度。
關鍵詞:農村居民點整治;利益相關者;行為偏好;博弈矩形;博弈分析
中圖分類號:TP7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944(2019)12-0287-04
1引言
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大量人口涌人城市,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加劇了城市對土地的需求,城市得不到足夠的用地指標,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制約城市發展的瓶頸。與此同時,農村“一戶多宅”、“舊房未倒新房又立”、超法定面積占用宅基地等現象普遍,宅基地閑置、粗放利用等情況嚴重。城市發展對土地的迫切需求與農村居民點不合理利用造成的土地資源浪費形成了鮮明對比。農村居民點整治成為協調城鄉人地關系的重要工具。然而,由于農村居民點整治是一項龐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多方利益主體,各利益主體的目標傾向不一致,利益目標差距擴大,導致整治中利益沖突顯性化,矛盾頻發。因此,把握各主體間的利益平衡點,合理處理不同主體間的利益關系,是有效推進農村居民點整治工作進行的關鍵。
近年來,農村居民點整治的潛力、整治模式、整治評價等人地關系方面受到了廣大學者關注,但僅有少部分學者對農戶居民點整治中人與人的關系進行研究。如王兵運用博弈矩陣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整治區農戶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地方政府的行為傾向是決定農村居民但綜合整治效果的關鍵因素,中央政府應降低監督成本,建立科學合理的農村居民點綜合整治補償標準和整治收益分配機制。關江華、黃朝禧通過建立在自發流轉模式下和政府主導模式下的博弈矩陣,發現在自發流轉模式下,村集體與農戶的均衡策略為(不干預、流轉);在政府主導模式下,政府與農戶的納什均衡為(合理,接受)。農村居民點整治,歸根到底是利益博弈的問題,是各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再分配。因此,本文在界定利益相關者基礎上,運用博弈論構建博弈模型,分析農村居民點整治中各利益主體的博弈關系,探討相關影響因素,以期為整治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理論依據和科學建議。
2利益相關者界定及其行為偏好
2.1利益相關者界定
1984年,Freeman在《戰略管理:利益相關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一書中,將利益相關者定義為能夠影響一個組織目標的實現或者受到一個組織實現其目標過程影響的所有個體和群體。農村居民點整治中的利益相關者即指個人或群體對參與整治擁有特定的利益訴求,并且此利益訴求能在一定程度上對整治目標產生影響。因此,本文研究中的利益相關者具體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農民。
2.2利益相關者的行為偏好
農村居民點整治是以中央政府為主導,地方政府為主體,整治區農民參與的公共決策行為。由于整治中各利益主體追求的目標不同,加之環境、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影響,因而其存在不同的整治行為偏好。
中央政府是農村居民點整治中的政策制定者和監督者,作為國家的領導機構,它所追求的不僅是經濟效益,還包括社會效益、政治效益、生態效益等,其利益目標包含統籌城鄉發展,緩解耕地保護壓力,促進農村土地節約集約利用,建設美麗鄉村,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增加農民的土地財產性收入等多方面。
地方政府在農村居民點整治中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是貫徹相關的政策,在城市化建設中保護農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增加地方財政收入,滿足政績需要,爭取更多的建設用地,招商引資,發展當地經濟。由于目前國家嚴格保護耕地的政策,農用地轉為城市建設用地較為困難,成本高、風險大,而通過農村居民點整治換取建設用地費用低,風險小,且有巨大的獲利空間。因此,地方政府在農村居民點整治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不顧農民意愿,不切當地實際的整治現象。
農民是與農村居民點整治最直接相關的,他們的利益偏好就是從整治中獲取補償,改善生活條件,提高生活質量。然而,由于農民長期以來在公共事務決策中都處于弱勢、被動地位,受生活環境、接受教育年限和村委宣傳力度等因素影響,農民對農村居民點整治的認知較為模糊,加上故土情節、難以改變現有生產方式和擔心整治后生存成本升高等考慮,往往不愿意進行整治。
3博弈模型
博弈模型是運用博弈論來研究主體之間發生直接或間接作用時,所采用的各種決策,以及行為主體所采用這些決策的均衡性問題。參與人、戰略集、支付函數(可用效用表示)是構建博弈模型的核心要素(表1)。參與人是指選擇行動以最大化自己效用的決策主體,即參與1和參與人2。戰略集是選擇行動的規則,即參與1=(策略1、策略2),參與人2=(策略3,策略4)。支付函數是參與人從博弈中獲得的效用水平,即效用1一效用8。
開展農村居民點整治實際上就是通過利益相關者的博弈,在盡力滿足各參與主體的經濟利益條件下,實現最大或最優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納什均衡。
4不同利益主體行為博弈分析
4.1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對于農村居民點整治的關注側重點不同。中央政府認為要嚴格把控指標關,而作為具有“經濟人”思維的地方政府,受區域經濟發展目標的內在驅動以及地方財政增收的外在需要,會想方設法利用土地生財,以滿足財政支出以及各項建設的需要,而違法整治有可能獲得高額的收益。盡管中央處于強勢地位,但具體關于農村居民點的整治工作還要委托地方政府執行,為了防止地方政府在執行政策的過程出現投機行為,中央政府會對地方政府的行為進行監督。因此,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可構建如下博弈模型。
參與主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博弈策略:中央政府為(監督,不監督),地方政府為(遵守,不遵守)。
博弈函數:
(1)中央政府監督,地方遵守。假設中央政府的收益為GA,監督成本為GB,則總收益為GA-GB。地方政府的收益為RC,地方政府遵守成本為RD,其總收益RC-RD。
(2)中央政府監督,地方不遵守。地方政府不遵守相應的規則,被中央政府發現,將會受到懲罰,假設懲罰為RZ,該懲罰將成為中央政府收益的一部分。因此中央政府總收益為GA+RZ-GB,地方政府收益為RC-RZ。
(3)中央政府不監督,地方遵守。中央政府收益為GA,監督成本為O,總收益GA。地方政府收益為RC,遵守成本為RD。總收益RC-RD
(4)中央政府不監督,地方違反。在中央政府不監督,地方政府不遵守的條件下,地方政府會存在一定的隱形收益,假設為RX。而中央政府的不監督行為會使其信譽下降,其損失為GY,此時監督成本為0。中央政府總收益GA-GY。地方政府總收益為RC+RX(表2)。
假設地方遵循中央決策的概率為P1,不遵守概率為(1-P1):
中央政府如果采取監督措施,可獲得的期望收益為E=P1(GA-GB)+(1-P1)(GA+RZ-GB);
中央政府采取不監督,可獲得的期望收益為E=P1GA+(1-P1)(GA-GY);
假設中央政府進行監督的概率為P2,不監督的概率為(1-P2):
地方政府如果遵守,可獲得期望收益為E=P2(RC-RD)+(1-P2)(RC-RD);
地方政府如果不遵守,可獲得期望收益為E=P2(RC-RZ+RX)+(1-P2)(RC+RX)。
以上建立的博弈模型是一個純策略的納什均衡模型。當地方政府不遵守規則時,中央政府的最優策略為監督;當地方政府遵守規則是,中央政府自然會選擇不監督。而當中央政府選擇監督時,地方政府會選擇遵守;當中央政府不監督時,地方政府的最優策略則為不遵守。如此一來,兩個利益主體就會陷入無限的循環。然而,在現實生活中,這種狀態幾乎是不存在的,在中央政府進行監督時,地方政府也有可能選擇不遵守。這時就需要用到混合策略。
中央政府無論采取何種策略,期望收益相同的均衡條件為:
P1(GA-GB)+(1-P1)(GA+RZ-GB)=P1(GA)+(1-P1)(GA-GY);
得到1-P1=B/(Z+Y)。
地方政府無論采取何種策略,期望收益相同的均衡條件為:
P2(RC-RD)+(1-P2)(RC-RD)=P2(RC-RZ+RX)+(1-P2)(RC+RX);
得到P2=(X+D)/Z。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當中央政府加強監督成本時,地方不遵守的概率會增大,反之,地方不遵守的概率則會減小。當懲罰力度加大時,地方政府不遵守的概率會降低,中央政府也會降低監督的概率。當地方能夠獲得更大的隱形收益時,中央政府會加大監督力度。
4.2地方政府與農民
農村居民點整治是與農民息息相關的一項重要T程,直接關系到農民的切身利益。農民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會根據自己及家庭的情況作出支持或反對的策略選擇。地方政府出于完成中央下達指標和統一區域內的規劃,對農村居民點整治會作出鼓勵和限制的選擇策略。因此,兩者間的博弈為:
參與人:地方政府、整理區農民;
博弈策略:地方政府(鼓勵,限制),農民(支持,反對)。
博弈函數:
(1)地方政府鼓勵,農民支持。地方鼓勵帶來的收益為RA,支付的補償為RB1。其他成本為RB2,如鄉村文明損失等,則總收益為RA-RB1-RB2。農民支持整治獲得的收益補償為RBl,其余收益為FC,增加的生產、生活成本為FD,總收益為RB1+FC~FD。
(2)地方政府鼓勵,農民反對。地方鼓勵帶來的收益為RA,支付的補償為RB1,其他成本為RB2,失去農民支持的收益為RY,總收益為RA-RB1-RB2-RY。農民獲得的收益為o,且需支付一定成本FD,收益為O-FD。
(3)地方政府限制,農民支持。地方政府限制不僅收益為O,且會付出一定的成本RBz,將會失去民心Y,損失信譽為RY,總收益0-RY-RB2。農民會有收益FC,付出成本FD,總收益FC-FD。
(4)地方政府限制,農民反對。兩者的成本和收益均為O(表3)。
假設農民支持概率為P1,反對概率為1-Pl;
地方政府鼓勵達到的期望收益為E=P1(RA-RB1-RB2)+(1-P1)(RA-RB2-RY)。
地方政府限制達到的期望收益為E=P1(0-RB2-RY);
假設地方政府鼓勵概率為P2,反對概率為1-P2;
農民支持達到的期望收益為E=P2(RB1+FC-FD)+(1-P2)(FC-FD)。
農民反對達到的的期望收益為E=P2(O-FD)。
由表3可知,如果政府選擇限制農村居民點整治,農民不會主動選擇反對,并且在實際的農村居民點整治中,農民往往是處于被動決策的地位。因此,不論地方政府采取何種策略,其期望收益相同的均衡條件為P1(RA-RB1-RB2)+(1-P1)(RA-RB2-RY)-P1(O-RB2-RY),得到P1=(Y+B2+B2-A)/2Y+Bz,由于Y和B2都是難以量化的指標,因此農民選擇支持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方政府給予的補償Bl,補償費越高,農民支持的概率就越大。
而不管農民采取何種策略,其收益相同的均衡條件為P2(RB1+FC-FD)+(1-P2)(FC-FD)=P2(0-FD),得到P2=(D-C)/(B1+D)。從中可看出,政府鼓勵整治與否的態度,也與補償標準B1有關,B1越大,政府鼓勵的概率就越小。所以,補償標準的高低往往是地方政府和農民博弈的重點。
5結語
在中國建設新農村的轉型時期,純戰略納什均衡顯然是不存在的。
(1)地方政府違法進行農村居民點整治的概率與中央中央政府的監督成本呈正相關,與中央的懲罰力度呈負相關,因此,中央應適當減少監督成本,同時加大懲罰力度,使地方政府充分認識到投機的帶來的損失,有效減少地方政府違反的概率。
(2)中央政府進行監督的概率與地方政府的投機收益呈正相關,與懲罰力度呈負相關。中央政府應扭轉并完善對地方的經濟考核指標,從源頭上遏制地方政府違規的誘因。
(3)農民反對農村居民點整治的概率與補償標準負相關關系。在現實生活中,農村居民點整治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提高他們的生存成本,農民往往會因為對補償收益不滿足,對“失地”無后續保障而反對整治。
為了協調農村居民點整治過程中各行為主體的利益,保障整治工作的順利進行,提出以下建議。
(1)加大對地方政府違法整治的懲罰力度。建立責任連帶制,地方政府違法整治,一經查處,必須嚴肅處理,斬斷相關利益鏈,讓違法者付出高額成本和代價。同時,運用高科技手段,如"3S”技術,進行動態監察,力爭將違法行為扼殺在搖籃中。
(2)建立公眾參與機制。農村居民點整治作為一項公共政策,基于農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弱勢性,應當對弱勢群體提出的合理利益要求最大限度的滿足。在農村居民點整治過程中,要充分保障農民的知情權。由于農民消息來源的渠道少,村集體尤其要做好相關政策的宣傳工作,力爭讓每個參與者都能了解相關信息。同時,要確保農民有正常有效的利益訴求渠道,充分表達自己的想法。
(3)增加農民的整治收益。合理提高補償的標準,科學確定整治補償費的計算方法,讓參與整治的農民真正享受到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并且要加強對整治補償費的管理,防止少數干部截留、私用、挪用整治補償費,損害農民的合法利益。
(4)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農村低保、農村醫療保險和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使農民“生有所靠、病有所依、老有所養”,轉變農民靠“土地”養老的觀念,保證參與整治農民的基本生存權利,激發農民參與整治的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