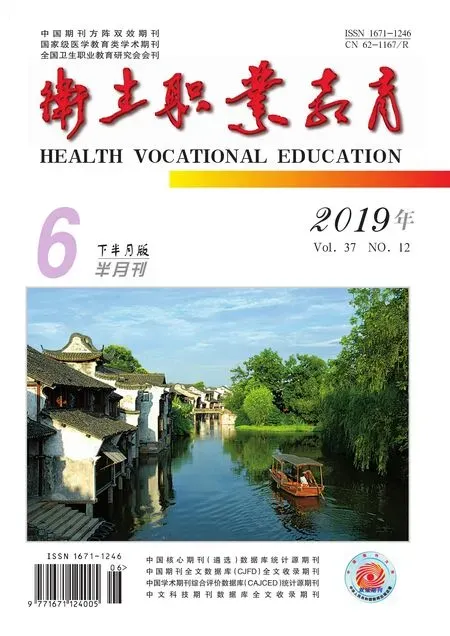法治視角下我國高校醫學倫理學教育現狀思考
張 萱
(中國醫科大學,遼寧 沈陽 110122)
法治,作為現代社會最理性而有效的調控方式,在日新月異的醫學領域發揮著重要的指引、評價、教育等規范作用。然而隨著干細胞治療、基因編輯等醫療新技術的發展,新的醫學倫理問題不斷挑戰著公序良俗,同時也向我們揭示了相關領域法治教育參與度的滯后性。因此,以“法治”為抓手提高我國高校醫學倫理學教育質量,是使醫學生在未來工作中自主應對倫理決策問題的重要途徑。
1 醫學倫理學與法治的關系
醫學倫理學是運用普世的倫理道德原則去解決醫療衛生實踐和醫學道德問題的學科[1]。而法治作為一種源遠流長的意識形態與治國方略,與倫理道德同受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制約,并同時直接受到一定階級的政治和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因此二者有著天然的密切關聯[2]。
1.1 產生過程相互滲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侵略者施行慘無人道的活體實驗給人類造成了嚴重傷痛,導致了1947年《紐倫堡宣言》的產生,當代醫學倫理學由此發軔。而《紐倫堡宣言》也是人類歷史上首個以明文規范了人體實驗規則的國際性文獻,并在此后經世界醫學大會數次完善,形成了國際規范并影響至今[3]。可見,一部法律規范性文件的產生始終貫穿著倫理精神,它的許多規范是根據倫理道德原則而制定的。而倫理學中的許多內容,又是依靠法律規范而被明文確定,并因此而具備法律強制性且得以普遍施行。
1.2 發展過程相互制約
“知情同意”是現代醫學的一項基本原則,隨著國際社會對醫學倫理精神認識的逐步深入,該原則在醫學倫理精神的指導下逐步走向法定化的“醫療告知義務”。例如,我國在1994年頒布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中確立了患者及家屬的知情同意權,經過幾年的司法實踐及醫學倫理學的深入發展,200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則首次以民事基本法律的形式對患者知情同意權進行了規定,法律層級不斷提高[4]。因此,法治通過立法和司法,促使某些倫理道德規范的完善和發展,制約不道德行為越出法律許可的范圍。倫理精神則通過對法的某些規定的公正性和公正程度的評價,促使法的立、改、廢,保持法的倫理方向。
1.3 運行過程相互支撐
2017年最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第八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不得違反法律,不得違背公序良俗。”第十條規定:“處理民事糾紛,應當依照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習慣,但是不得違背公序良俗。”“公序良俗”是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的簡稱,當法無明文規定或明文禁止時,公民則可以參照國家的公共秩序和社會的一般倫理規范自己的行為,從而發揮與法律規范的互補作用。可見,法是倫理的政治支柱,倫理是法的精神支柱。從實質上講,法和倫理道德的社會本質和服務方向根本一致,二者對人們行為的評價方向根本一致。
2 法治視角下我國醫學倫理學教育存在的問題
20世紀70年代,美國醫學教育家即指出,醫學模式已開始從“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轉變[5]。現代醫學模式的轉變,必然對醫學倫理學教育產生巨大影響。醫學人才的培養,應更加注重構建合理的知識結構,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最新成果引入醫學倫理學教育,使學科緊跟時代步伐并不斷煥發青春活力[6]。然而在法治社會下,要順應醫學模式轉型,從教與學兩方面提高我國高校醫學倫理學教學水平,仍存在許多問題。
2.1 對醫學倫理學教育重視程度不足
相比于歐美等發達國家,我國醫學院校將醫學倫理學設置為正規課程的時間較晚[7]。醫學倫理學課程多設置為考查科目,且課時有限,直接導致學生忽視自身人倫精神的培養,缺乏對其他相關人文社會科學的自主關注。其次,高校的醫學倫理學課程往往只設置在基礎教學階段,難以滿足臨床應用需求,遑論為醫學生在臨床實踐中將倫理原則與具體法律法規相結合,從而為指導其醫療行為提供知識支撐,削弱了醫學倫理學在臨床實踐環節當中的著力點。
2.2 醫學倫理學課程內容更新不足
課程設置的教學內容往往偏重于理論說教,缺少對醫學倫理社會熱點問題的分析,忽視了職業道德知識向行為的轉化,使學生對醫學倫理的理解過于簡單化,不利于將知識滲透到未來的應用當中去。其次,醫學倫理學與具體專業相結合的個性化課程空白,教學內容設置千篇一律,導致教學內容更新難、課程內容對實踐的指導意義不強等問題。
2.3 醫學生正確的醫學倫理觀亟待樹立
我國高校在醫學倫理學課程定位與教學內容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導致醫學生普遍存在重專業知識、輕人文倫理的問題。首先,重技術工具、輕人文情感。導致學生過于依賴高科技器械,忽視了自身看診能力的積累與體察病患情感能力的培養。其次,重科研成績、輕人文素養。不了解相關醫學倫理原則及法律法規的具體規定,易使學生在醫務乃至科研工作中作風浮躁、急于求成,出現學術道德失范、社會責任感缺失等問題。
3 法治視角下改進醫學倫理學教育的途徑
隨著我國法治社會的建成,醫療衛生相關法律法規也會不斷健全,從而為我國高校醫學倫理學教育質量的提升提供新的思路與保障。
3.1 完善醫學倫理學課程設置
首先,醫學倫理學的課程設置應當體現為縱向貫通[8]。使醫學倫理學課程貫穿于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以及繼續醫學教育全過程,同時將醫學倫理教育延伸到基礎醫學教育、臨床醫學教育以及臨床實習的各個階段,使醫學生在不同教育階段掌握相應的醫學倫理問題決策能力。其次,豐富醫學倫理學課程內容,在橫向上與其他醫學課程融會貫通,實現課程內容的豐富創新。例如,通過與各醫學專業相結合而衍生出兒科醫學倫理、精神科醫學倫理等課程,拓寬醫學倫理課程的覆蓋面,同時為倫理規范與具體專業的職業守則、法律法規的有機結合提供空間,細化倫理學知識對臨床實踐的指導性。
3.2 擴充高校相關人文素質教育教學資源
首先,醫學倫理學課程的師資力量不應僅局限于本專業內,還應吸納倫理學、哲學、法學教師以及臨床醫生等,構成教學團隊,有分工地開展醫學生在校期間及臨床實習階段的倫理教育[9]。多學科背景的教師團隊,會根據自身行業背景,從不同角度有的放矢地闡釋醫學倫理學,開闊醫學生視野。其次,加強高校醫學生醫學倫理相關政策法規的通識教育,對社會普遍關注的醫學倫理問題及最新政策法規進行及時宣傳解讀,使學生掌握醫學技術的同時了解技術的“紅線”在哪里,培養醫學生為人類健康事業奮斗的更為廣闊的視野。最后,利用校內人文院系的資源優勢,大力開展專題講座、研討會等活動,營造重倫理、重人文教育的校園環境[10]。
3.3 促進全社會醫學倫理學知識普及,完善醫學倫理相關政策法規環境
首先,以學生為主體、以校園組織為依托,定期開展醫學倫理學知識普及宣傳活動,并逐步走出校園向社會推廣。普及醫學倫理知識及醫療衛生法律法規,使患者從理性的角度理解醫生職業的特殊性,從而更好地促進醫務工作者提升自身醫學倫理素養與人文關懷精神,弘揚醫患之間理解共生的主流價值觀[11]。其次,有關機構應及時修訂、完善醫學倫理相關政策法規,為醫學倫理學發展提供法治保障,形成指導、約束醫療新技術運行的法律框架,使醫學倫理學教育、醫學科研以及醫事診療行為有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