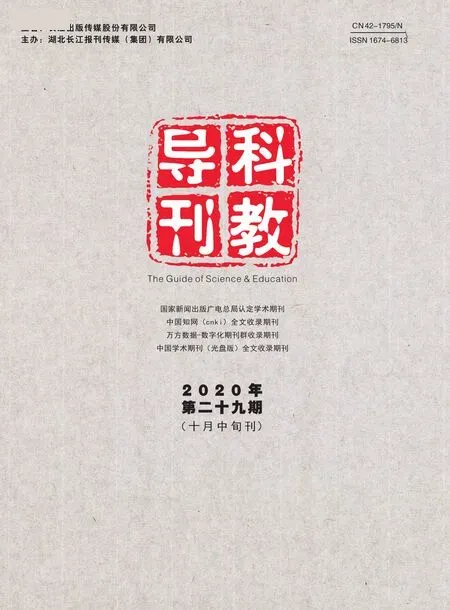網絡語境下高校國家安全教育的反思及對策
侯玉瑩
(江南大學物聯工程學院 無錫·江蘇 214122)
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統籌發展和安全,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大原則。國家安全關系到整個民族的生存,是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高校肩負著為國家培養社會主義事業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歷史重任,是敵對勢力滲透自身意識,爭奪利益的重點目標。[1]高等學校從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與創新等職能出發,無論是“為誰培養人”“培養什么人”還是“怎么培養人”,都必須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尤其是要在意識形態戰場維護國家的政治安全。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信息傳遞逐漸從傳統媒介向新型媒介轉移,以社交媒體為代表的新型信息傳播媒介逐漸稱為青年在校學生的主要信息獲取渠道。青年學生因其思想意識還未成熟,探討互動缺乏思考,容易缺乏判斷力輕信謠言。提高學生的政治敏感度和政治辨別力顯得尤為重要。這對廣大思政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在思政教育工作中筑牢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銅墻鐵壁。
1 網絡語境下大學生國家安全意識現狀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 2020 年3 月,我國網民規模為9.04 億,中國互聯網普及率達64.5%,其中20-29 歲學生的占比為最大。[2]但與之相對應的現實是,如此龐大的青年學生用戶群體,在面對海量信息時間,在信息甄別能力、政治敏感性和國家安全意識上均存在欠缺,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對國家安全概念界定不清晰。面對國內外形勢發生的復雜深刻變化,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概念,并首次系統提出“11 種安全”。但因宣教不到位,部分大學生對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概念知之甚少,對于國家安全的認識還停留在領土完整、國防科技、軍事力量等傳統領域,對文化滲透、信息網絡、價值傳播等軟實力的競爭敏感性不足。大學生日常生活環境和平穩定,忽視了不安定因素在社會中的存在,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放松警惕,總體國家安全觀尚未建立。
(2)對國家總體安全觀認識過于片面。在國家安全教育系統還未完全鋪開,學生對國家總體安全觀的認識還有待提高。部分學生因受電影、小說、影視劇及新聞等網絡信息的局限,形成了“信息繭房”,客觀上使其對國家安全的概念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認識產生局限,認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多是間諜情報活動、詆毀行為、暴力及沖突等外化型危機事件。對于意識形態滲透、文化入侵等非傳統的“內化型”行為認識不足。
(3)對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辨別力不足。由于國家安全宣教和學生認識的缺失,部分學生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辨識力和敏感性較差,對于網絡信息安全、有害言論散播、負面輿論引導等“軟性”危害行為或無知、或遲鈍、或麻木。網絡信息獲取的便捷且成本低廉,使敵對勢力的傳播見縫插針進行滲透。主觀上,學生對于自身意見表達存在情緒化和沖動性,容易受到外部引導和影響,其言論也缺乏責任感。[3]在沒有充分認識的情況下,被外部勢力利用,發表不負責任的有害言論,成為危害國家安全穩定的“幫兇”。
2 網絡語境下高校國家安全教育面臨的挑戰
迅猛發展的移動互聯網技術,創造了新的信息載體,也為新時代青年人營造出不同于以往的信息環境和話語體系。這種“新”,使傳統的國家安全教育在路徑和載體上與其受眾產生錯位,同時也使高校思政工作在國家安全教育上面臨巨大挑戰。
(1)復雜信息傳播環境的挑戰。新興媒體的崛起使得網絡信息的傳播多元化,復雜化,其傳播趨勢和結果難以提前預判。在“信息爆炸”的背景下,信息來源的開放性、復雜性、不可控性被放大,但其真實性和可信度卻在眾多“不可控”中受到削弱。高校學生社會閱歷尚淺、價值導向還不夠牢固,容易在被刻意營造的信息氛圍下對某些打著“普世”幌子的理論所迷惑,這也給了敵對勢力動搖學生價值觀的可乘之機,通過對事件的選擇性描述、局部扭曲和放大,使學生對社會問題產生偏激、片面的認識,最終導向對文化、體制等的懷疑和否定,進而可能被敵對勢力裹挾利用。
(2)信息圈層性和隱匿性的挑戰。青年學生因尋求認同的心理需求,在網絡中更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進而以興趣愛好為聚合點形成圈子,圈子在發展中形成屬于自己的語言體系。學生在圈子中學習獨有詞匯,加入獨立圈子,用隱晦、指代、縮略、內涵的方式發布和傳播語言、圖片、視頻信息,其言論立意在非本圈層人中辨識度很低,甚至能夠逃脫網絡安全監管范疇。思政工作者在實際工作中很難發現其言論表述是否得當,做好預案工作。而這樣的學生往往已經被預謀者帶入其圈層,不自覺地接受其價值觀念,為其開展宣傳工作。這也無形中加大了思政工作者對不當網絡信息傳播進程管控工作的難度。
(3)傳統國家安全教育失能的挑戰。技術的發展為信息高效、定向傳播提供了可能。碎片化信息的時代,學生在信息獲取的過程中主動權逐步增強,各大新媒體平臺不斷創新信息推送方式,主動掌握大學生關心的重點話題。在“算法”的加持下學生對信息的獲取更為高效,甚至在學校開展教育前,學生對事件的看法已有相對清晰的自我預判。而反觀高校傳統國家安全教育模式,很難又快又準的開展工作,時效性和實效性均受到不小打擊。對于學生而言,對比豐富自由的網絡語境時,甚至會對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活動產生抵觸和逆反心理,極大地削弱傳統思政教育的主導地位。[4]
(4)對高校思政工作的有序開展帶來沖擊。高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善于處理面向群體對象和系統問題,容易忽略學生的個人特點和個性化需求。在網絡時代大環境下,學生擁有更為廣闊的空間進行自我表達,容易沉迷于自己營造的世界而忽略與現實的溝通。這部分學生若性格孤僻、人際交流能力低、社會支持系統的崩潰,引發情感和心理障礙,反過來會使封閉自我的意愿更為強烈,并在網絡上發泄情緒,造成不良社會影響,更有甚者因自身思想與社會現實相違背做出過激舉動。[5]在學生價值觀塑造最重要的時間段里,對高校思政工作者培養大學生塑造健全人格帶來不小的壓力,也對思政工作的有序開展帶來巨大沖擊,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和國家安全教育,規避不良網絡信息也成了高校思政教育的基本內容。
3 網絡語境下加強國家安全教育的對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時而進、因勢而新。”在這種現實下,高校要立足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就要主動迎接互聯網浪潮的到來,適應網絡語境下青年成長軌跡,幫助學生建立好總體國家安全觀。
(1)防微杜漸,做到普及教育、重點掌握。將國家安全教育納入到日常學生管理的各個方面,做到針對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普及教育,要求學生對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社會安全有針對性的重點掌握。
不斷創新工作方法,用引導教育、體驗教育代替傳統的說教,開展有效的主題性班委培訓及年級會議,加強網絡平臺相關普法教育,自覺抵制網絡有害信息,依法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作斗爭。通過普及教育和重點掌握相結合,不斷提高政工干部和學生的政治敏感度及辨別力,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動搖,立場鮮明、主動亮劍。引導學生正確認識事件本質,避免產生大學生內部群體效應或輿情危機事件。
(2)主動學習,掌握青年群體話語體系。在當代大學生網絡語境中,學生個人社交平臺發布心情動態、轉發內容隱晦的有害信息時,思政工作者往往會出現“不知所云”的尷尬狀況。這就要求思政教育工作者更要主動掌握新興媒體技術,主動在網絡平臺關注大學生所思所想、用詞語系,不僅做到觀其所“言”,更要知其所“意”,能夠不斷提高自身網絡不當信息的認知水平,爭取到思政教育在網絡語境中的話語權。在遇到學生有不當言論時,及時發現與預判,做好引導教育。同時,建立良好的師生關系及信任網絡,用大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將國家安全教育置于其習慣的網絡語境中,與敵對勢力斗爭。守牢思政教育網絡新陣地,爭取網絡語境中思政教育的話語權。
(3)管理機制構建,班級-家庭-學校三位一體。在網絡語境下,大學生言論及行為方式復雜多樣,思政工作者要做好班級建設,構建良好的班級管理體制。學生對朋輩有更少的抵觸情緒,通過對班級班委的培訓,用好青年抓手,做到層層把控,對班委反映的學生異常動態進行預判,如青年大學習學習情況、團日活動參與情況、團費收繳情況、日常言論情況等,均可反映學生對國家安全相關事務工作的態度及其真正的想法,在青年群體中自發地建立好國家安全教育體系,做到互相監督、互相提醒。
做好家校聯系工作臺賬,在學生有言論及行為不當的情況下,及時與其家長聯系,共商學生行為的引導工作,及時告知其后果及社會影響。如學生行為在后期形成較為嚴重的社會影響,家校在商議過程種,也會盡到及時告知的義務,家長因其經歷較為豐富,政治意識強,對學生不當行為的知情后,會及時控制學生的言行,將社會影響降到最低。
(4)獎懲得當,警示教育與激勵教育同在。當前我國高校對破壞國家安全的行為處理機制薄弱,對行為的判定還存在不明確量化因素,監控水平還有待提高。高校思政工作也更應秉持德育為先的原則,發現有不當行為及時制止,如出現行為,造成一定的社會影響,應及時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對于以上行為,做到早發現、早預判,對于我們學生用好網絡平臺,提高自身辨別能力有較高要求,因而要進行警示教育。對于工作中積累的相關案例經驗進行總結分析,告知廣大學生群體“何為破壞國家安全”行為,將警示內容具象表述,起到威懾作用。此外,對于網絡信息辨別意識強的行為給予充分鼓勵和贊揚,構建好完整的獎懲機制,強化學生國家安全意識,引導其自覺維護國家安全。
4 結語
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高校必須承擔的責任和義務。《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中指出堅持以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為著力點為要求,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旗幟鮮明反對分裂國家圖謀、破壞民族團結的言行。高校思政工作者們應不斷跟著時代進步的腳步改進工作方法,主動構建廣大學生相適應的國家安全教育話語體系,重新配置話語權,不斷提升工作能力和工作技巧,主動出擊、勇于擔當、建好機制、守好陣地,不斷提升新時代國家安全教育及愛國主義教育建設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