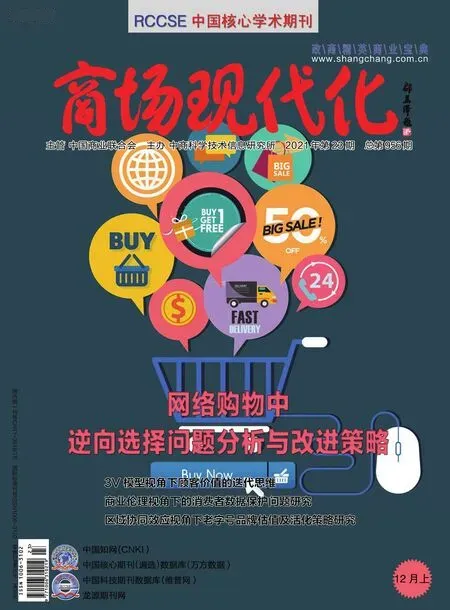企業戰略觀演進軌跡與方向

摘 要:本文基于“環境-戰略-組織結構”關系范式,以市場經濟形態變革為主線梳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企業戰略觀的演進軌跡。其中,整個演進過程可被依次劃分為賣方經濟時期、賣方經濟后期、賣方經濟向買方經濟過渡時期、買方經濟初期、買方經濟后期、未來型經濟時期六個階段,而與之對應的企業戰略觀依次是生產本位型戰略觀、匹配型戰略觀、環境本位型戰略觀、資源本位型戰略觀、體系本位型戰略觀、共生型戰略觀。
關鍵詞:企業戰略;共生型發展;“環境-戰略-組織結構”
引言:企業戰略觀反映了企業在戰略問題上的基本價值取向,決定和支配著企業戰略選擇。基于制度、經濟和社會等環境演進的漸進性,每個企業的戰略觀在動態調整的過程中又打造出了企業戰略觀的整體階段性(賀俊,2010),這意味著企業戰略觀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唯有“跟上時代”、“在時代里”,企業戰略方案才能指導其生存、競爭與發展。然而,截至目前,有關企業戰略演進性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對企業戰略管理理論的階段性梳理上,并且大都以西方的戰略理論體系為主,例如,王革等(2004)、高鎮光等(2010)對企業戰略管理理論進行了系統性回顧,前者在將企業戰略管理理論發展階段歸納為“企業—環境—綜合范式分析”三大階段的基礎上,提出了戰略管理學說體系的總框架,后者則將企業戰略管理劃分為古典戰略理論、新古典戰略理論、產業創新戰略理論三大發展階段。
區別上述研究,本文認為在“四個周期”加速變短(李海艦等,2018),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愈發“混沌”“無序”的時代背景下,從底層觀念出發,系統性地把握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企業戰略觀的演進軌跡及方向,有助于從根本上助力企業發展。并且,基于市場經濟形態作為企業生存與發展最基本以及最直接的“土壤”,能夠匯集所有外部環境因素對企業戰略觀影響的認知,本文最終以市場經濟形態變革為主線梳理出了六大企業戰略觀,即生產本位型戰略觀、匹配型戰略觀、市場環境本位型戰略觀、資源本位型戰略觀、體系本位型戰略觀、共生型戰略觀。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基于“環境-戰略-組織結構”關系范式,從市場競爭環境、企業組織形態兩個方面,正向推導和反向驗證了企業戰略觀的演進。
一、賣方經濟時期:生產本位型戰略觀
建國初期,“經濟短缺”是中國的一個基本國情,人們物質需求與落后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供需矛盾長期存在。一方面,市場處于嚴格的賣方經濟市場,消費者重在追求產品數量,生產者重在追求生產規模和生產效率。另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突出,企業本質上是一個政府的“代工”工廠,不僅一切活動都僅圍繞生產展開,而且其功能和“戰略”的合理性更多地體現為“政治合理性”而不是“經濟合理性”(賀俊,2010),企業戰略與國家戰略完美融合。這里,企業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戰略”,戰略的本質是一種國家計劃與規劃,其所有的經營決策與規劃都圍繞生產能力展開。具體來說,保證生產任務完成,擴大生產規模,強化生產管理水平,提高生產效率是該階段企業最主要的活動(王欽,2008),企業“就企業做企業”,采用的是以生產職能為主的生產本位型戰略觀。
與此同時,企業大量采用的直線職能制組織形態,旨在以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和韋伯的官僚主義理論為支撐,通過橫向和縱向分工,打造出一個上下、左右精準對接的封閉式系統。從而在形成高度集權的層級制權力鏈條,使權利、決策、信息等均自上而下有序流動的基礎上,產生一種“下層-上層-國家”嚴格線性的管理體制。此時,企業完全沒有自主經營權,主要任務是實現標準化、規模化、效率化的科學化生產,企業遵循的是生產本位型戰略觀。
二、賣方經濟后期:匹配型戰略觀
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確立與實施,計劃經濟體制開始松動,逐漸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這一“探索”時期,包含經濟制度、市場競爭以及金融條件等在內的企業外部環境正進行著“高速度”過渡(王欽,2008)。開放性市場和高速度經濟發展帶來的市場機會極大地刺激了隱藏于計劃經濟時期的企業家創業和創新活力,國有企業制度能量的釋放以及市場中大量民營企業的涌入真正開啟了中國企業戰略發展時代,整個市場逐漸邁入賣方經濟后期。
此時,從企業角度看,一方面,隨著越來越多非國有企業涌入市場,社會供給增加,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經濟短缺現象以及嚴峻的供求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緩和,市場供方約束減弱,市場需求(或潛在需求)、盈利空間的程度和穩定性被極大壓縮。另一方面,隨著“短缺經濟”向“相對短缺”過渡,人們對產品價值的定位發生轉變,即從單純追求產品數量逐漸過渡到追求產品功能、質量、安全、多樣、服務、環境等。由此可知,企業單一、穩定的生產格局正在被打破,企業不再僅僅需要關注內部生產效率、規模與速度,更需要開始關注外部市場的動向與變化。否則,“閉門造車”、“就生產而生產”的發展方式會導致產品與市場需求“南轅北轍”,無法實現“驚險的一跳”。這就導致企業在其戰略行為中既要重視內部資源、能力與效率,又要重視外部市場環境及其變化,保持一種內外兼顧的戰略觀(田奮飛,2005)。
與此同時,該時期對應的主流企業組織形態是事業部制。其通過適度分權,既沿用了金字塔式科層制的優勢,保證了企業對生產規模和生產效率的追求,又啟用了新型“本土化”發展模式,保證了人們對更高產品定位的需求,如企業通過建立產品事業部、地區事業部以及顧客事業部,分別實現了對產品、地區、顧客實施“本土化”、“定制化”的發展,進而滿足了“人們對不同產品”、“不同地區對相同產品”、“不同顧客類型對相關產品”的更高例外化要求,解決了計劃經濟時期企業成長與創新效率降低的矛盾。這里,企業組織形態從集權到分權,反映了企業戰略觀已從生產本位型戰略觀轉變為匹配型戰略觀。
三、賣方向買方經濟過渡時期:環境本位型戰略觀
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正式確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階段。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以及跨國企業涌入中國市場,社會整體的供給水平再次提升,供需矛盾被持續緩解,以買方需求為主的生產模式逐漸凸顯,賣方經濟向買方經濟過渡。
隨著持續不斷地發掘日益稀缺和隱含的市場機會對企業及其競爭優勢的價值和意義越來越大,外部市場機會的價值逐漸超越了企業內部效率與能力的價值,市場機會之爭日益成為企業間競爭的焦點,企業開始采用以市場機會導向為主的市場環境本位戰略觀。這使企業不斷地識別和進入利潤“無人區”,不僅形成了企業多元化經營的趨勢與風潮,而且加速企業競爭由行業內部轉向行業之間。當企業循環地“進入-競爭-飽和-在進入”時,利潤開始從企業的生產領域轉向營銷領域(李海艦和原磊,2005)。例如,企業普遍開始采用“廣告戰”。
與此同時,中國企業普遍采用的矩陣式企業組織形態能夠很好地驗證這一企業戰略觀的轉變。矩陣式企業組織形態通過在科層制垂直系統的基礎上增長一種橫向領導系統,形成一種“項目小組+職能成員”的組織模式。一方面,項目小組“即用即組,用完即散”的特征保證了企業對市場機會的及時響應;另一方面,“職能成員”的“企業既有資源”屬性大大降低了企業響應市場機會的成本,從而賦予了企業及時響應、不斷響應市場機會的能力,以此保障企業市場環境本位戰略觀的高效落地與實施。
四、買方經濟初期:資源本位型戰略觀
21世紀初期,市場化、全球化、信息化三者疊加對企業生存與發展的環境帶來了顛覆式變革。尤其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的日益成熟與應用,能夠從供需兩側發力,徹底改變經濟發展的基本邏輯與方式,加速市場邁入買方經濟初期。
這一新階段對企業戰略觀及戰略行為帶來的主要轉變有以下幾點:
(1)從“多元化”到“歸核化”。隨著市場機會日益稀缺化、動態化和隱形化,企業尋找和把握市場機會的難度和代價越來越大,專用性資本成為企業捕捉新市場機會的累贅,企業多元化擴張戰略相對于專一化戰略來說越來越不劃算。
(2)從“競爭”到“合作”。“歸核化”意味著企業將資源集中于特定的市場領域,即企業的生產與經營只涉及某一行業、某一產品或某一價值區段。這樣一來,為了適應市場需求的日益復雜化、個性化特征,企業需要轉變以往“零和博弈”競爭觀念,“跳出企業做企業”(李海艦和郭樹民,2008),與市場中其他企業共同合作。
(3)從“價值鏈”到“價值網”。合作壓倒競爭使企業的價值創造模式從價值鏈轉變為價值網,并且作為一個開放性系統,價值網絡能夠始終處于動態最優,以此保證企業競爭優勢的持續性。
綜上,企業集中資源培育核心競爭力,是該歷史時期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關鍵,而以自身核心競爭力在市場上“動態織網”是其在市場上獲得持久競爭優勢的主要方式。企業奉行以核心能力為主的資源本位型戰略觀。此時,區別以波特為代表的市場定位學派過分強調市場環境對于企業及其競爭優勢價值與意義的觀點相比,資源本位型戰略觀認為競爭優勢源于企業內部(Jay,1995),企業超額價值創造得益于企業的特殊性,而非產業間的相互關系(Rumelt,1987),強有力的資源和能力優勢遠比突出的市場位勢更加有利(Birger,1984),企業經營的業務范圍由企業所具有的資源與能力決定(Prahalad,2000)。
與此同時,該時期市場主流的企業組織形態是虛擬型組織。它踐行“腦體分離與在分離”的發展原則(李海艦和聶輝華,2004),通過聚焦企業最具優勢的價值鏈區段或環節,打開企業邊界,實現企業間的動態競爭與合作,以此實現企業競爭資源和能力的始終供給與優化,企業得以高效、持續發展。例如,外包、眾包、“皮包”等企業組織形態的出現,使企業從關注環境轉向關注核心能力,遵循的是以核心能力為主的資源本位型企業戰略觀。
五、買方經濟后期:體系本位型戰略觀
在我國經濟經歷了接近四十年高速度增長后,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提高,消費者需求持續升級,主要經濟矛盾發生根本性變化,買方經濟深化,市場處于賣方經濟后期。
隨著經濟發展從低速轉向高速、從確定性情景轉向不確定性情景、從線性變化轉向非線性變化、從實體空間轉向虛擬空間、從同道追趕轉向換道超車(李海艦等,2018),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愈發復雜、動態、不可預測。這意味著,該時期的經濟均衡分析需要加入時間變量,以此才能恰當地描述供需均衡“轉瞬即逝”的特點,即市場“結構化失靈”成為常態,速度經濟成為主流。此時,預測需求在生產的生產模式已失效,企業由價格戰、品牌戰、質量戰等轉變為速度戰(李海艦等,2016)。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意識到,打造出一種能夠自感知、自協同、自調整、自優化、自循環、自治理,實現柔性、彈性、輕型發展,并且能夠與外部環境不確定性、未來不確定性、環境高度復雜性動態匹配和整合創新的智慧型體系(李海艦等,2014),是當下企業最有效的競爭優勢來源,以智慧型體系為主的體系本位型企業戰略觀逐漸確立。
與此同時,市場中涌起了大量的平臺化企業,通過“聚合多元主體”、“用戶本位主義”、“價值增值機制”的組織特征實現了企業智慧型體系打造(李海艦和李燕,2019)。
(1)通過“聚合多元主體”和“用戶本位主義”形成完全以用戶需求為主的價值創造流程,真正做到用戶需要什么,就研制和生產什么,把“異質化”做到極致,把用戶體驗做到極致。
(2)通過“價值增值機制”激活整個體系的“自組織”功能,通過對市場需求的自感知、自協同、自調整、自優化,使企業的戰略發展方向不斷從內部涌現、完善、執行和迭代。由此,用實踐證實了企業對體系本位型戰略觀的重視。
至此,企業戰略觀的演進已經有了里程碑式轉變:
(1)從“內外割裂”到“內外融合”。以往,企業采取的是以“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清晰劃分為主的戰略分析范式,并且具有清晰的流程與工具。現在,技術發展將企業與市場間的邊界徹底打破,企業在“內外融合”基礎上采用一種新型的戰略分析范式,“戰略工具論”逐漸向“戰略思維論”的轉變。
(2)從“他組織”到“自組織”。以往,企業奉行的戰略觀是一種被動模式,強調企業戰略行為與實踐是對環境變化做出迎合反應的結果,企業以未來為指導,以過去為參照,以現實為基礎,人為地調整和優化現有狀態,使其朝著構建自身長期競爭優勢的方向發展。而現在,以打造智慧型體系為主的體系本位戰略觀,奉行的是一種“環境變、我也變”的“變色龍”式自組織模式,它強調企業從內部自發地、主動地察覺到市場環境的變化,進而達到現實與未來實時“共舞”的效果,當下就是之前的未來,未來只是當下的延續。
(3)從“戰略選擇觀”到“戰略復雜論”。以往,企業的戰略觀大體是圍繞著環境分析而形成的。因此,更多的是在奉行戰略選擇觀,即以環境的選擇性為主導,強調環境對企業戰略選擇的決定作用。而智慧型體系則更多的是在踐行復雜理論,強調環境與能力“協同演化”的重要性,它將環境和企業戰略看作是一個復雜系統,系統內存在自組織機制、非線性關系和協同演進的過程,企業一方面具備足夠的組織支撐維持其正常運營,另一方面企業具有相當靈活性與外部環境條件進行內部變革和相互關系調整,以適應復雜變化的環境和條件,實現企業戰略和環境之間的協同演進。
六、未來型經濟時期:共生型戰略觀
當前,中國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經濟轉型、“逆全球化”、經濟雙循環、新一輪科技革命等使企業的外部環境愈發“混沌”“無序”。然而,“無序”又蘊含著“有序”,用戶及用戶需求成為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唯一導向。由此推知,未來的市場經濟形態是對買方經濟的延續與深化,未來型經濟時期依舊是一種買方經濟,但是一種極致化發展的結果。這主要體現在,用戶需求從產品轉向場景、從功能轉向解決方案,例如,人們不是需要洗衣機,而是需要一個衣服全生命周期的護理方案。因此,競爭或簡單合作已經無法保障企業基礎的生存與優勢(陳春花和趙海然,2018),企業關系向共生極致化演進,由此倒逼企業形成一種以共生關系為主的共生型戰略觀。此時,價值創造最主要的特征是,產品、企業、行業邊界被不斷打破,所有系統參與者共同滿足消費者需求,價值創造沒有主體和客體區分。
本文認為以共生關系為主的共生型戰略觀是當今社會和未來社會核心的企業戰略觀,這一點從當下市場中涌現越來越多的生態化企業組織形態上可以得到印證。生態化企業是一種多方參與、共創共享、動態演化的商業生態系統,通過多價值主體間的共創共享實現從智慧型組織的定制化產品(服務)轉向更深層次的定制化場景,并且在技術和規則的保障下,實現了需求的自感知、自滿足、自調整、自迭代、自循環,真正做到了產品(服務)全生命周期的“自動化”供給。它在本質上是一個共生系統,即系統中的價值主體彼此“開放邊界、相互加持、共創價值、互補發展”(陳春花和趙海然,2018)。
七、結語
本文基于錢德勒提出的“環境—戰略—組織結構”關系范式,嘗試從“環境決定戰略”、“結構追隨戰略”兩條路徑,分別驗證新中國成立以來企業戰略觀已經經歷了生產本位型戰略觀、匹配型戰略觀、環境本位型戰略觀、資源本位型戰略觀、體系本位型戰略觀五個階段,并且正向共生型戰略觀極致化演進。需要強調的是,生產本位型戰略觀、匹配型戰略觀、環境本位型戰略觀、資源本位型戰略觀、體系本位型戰略觀、共生型戰略觀只是代表了某一時代領航企業的前進方向,即在理論上可將六種企業戰略觀分別闡述,但在實踐中,這些企業戰略觀大都同時存在且相互融合,并且后一階段的企業戰略觀不是對前一階段企業戰略觀的否定,但后者包容、涵蓋了前者并超越了前者。因此,雖然很難給出一個明顯的演進時間界限,但這一梳理依舊可大致反映出企業戰略觀的演進軌跡與方向,幫助企業打造“時代型企業戰略觀”。
參考文獻:
[1]賀俊.中國工業企業戰略演進的軌跡和方向[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0,47(2):104-112+159-160.
[2]王革,吳練達,張亞輝.企業戰略管理理論演進與展望[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4,(1):101-106.
[3]高鎮光,潘聰,焦豪.企業戰略管理理論演進的內在邏輯與實現路徑分析[J].上海管理科學,2010,32(1):18-21.
[4]李海艦,朱芳芳,李凌霄.對新經濟的新認識[J].企業經濟,2018,37(11):45-54.
[5]王欽.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企業戰略的發展:復雜環境下的“協同演進”[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23(S2):26-35+143.
[6]田奮飛.論企業戰略觀選擇的市場邏輯——基于西方企業戰略理論與實踐演進的脈絡分析[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6):127-130.
[7]李海艦,原磊.基于價值鏈層面的利潤轉移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5,(6):81-89.
[8]李海艦,郭樹民.從經營企業到經營社會——從經營社會的視角經營企業[J].中國工業經濟,2008,(5):87-98.
[9]Jay B.B.Looking inside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1995,9(4):49-61.
[10]Rumelt R.P.Strategy,economic theory and entrepreneurship:the competitive challenge [M].Cam-bridge,Mass.:Ballinger Books.1987.
[11]Birger W.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4,5(2):171-180.
[12]Prahalad C.K.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M]// Strategic Learning in a Knowledge Economy.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2000.
[13]李海艦,聶輝華.論企業與市場的相互融合[J].中國工業經濟,2004(8):26-35.
[14]李海艦,李文杰,李然.新時代中國企業管理創新研究——以海爾制管理模式為例[J].經濟管理,2018,40(7):5-19.
[15]李海艦,徐韌,李然.工匠精神與工業文明[J].China Economist,2016,11(4):68-83.
[16]李海艦,田躍新,李文杰.互聯網思維與傳統企業再造[J].中國工業經濟,2014,(10):135-146.
[17]李海艦,李燕.企業組織形態演進研究——從工業經濟時代到智能經濟時代[J].經濟管理,2019,41(10):22-36.
[18]陳春花,趙海然.共生:未來企業組織進化路徑[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