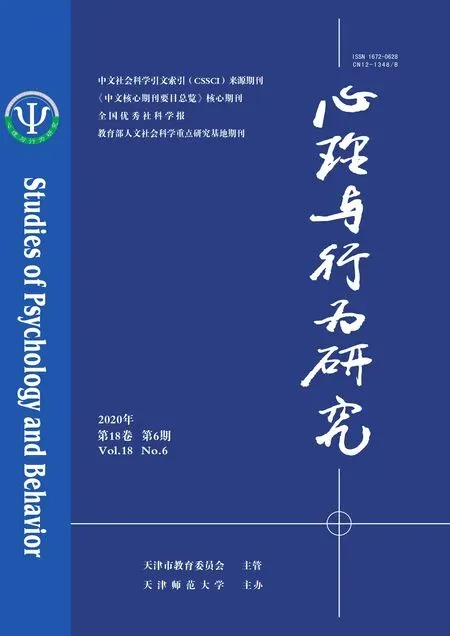自我污名與孤兒學生消極情緒的關系:解釋風格及領悟社會支持的多重中介作用 *
王江洋 于子洋 聶家昕
(1 沈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沈陽 110034) (2 沈陽師范大學社會學學院,沈陽 110034)
1 問題提出
在我國,一般由民政部門設置公立孤兒學校,對失去單親或雙親、或父母雖健在但卻無法承擔正常家庭監護責任的學齡期孤兒進行集中撫養與教育。這些學齡孤兒身份具有特殊性(王江洋, 李昂揚等, 2017),他們長期缺少父母的陪伴與管教,遠離主流社會,容易產生一系列心理問題。7 至18 歲學齡孤兒的心理健康水平整體低于普通學生(蘇英, 2011),通常具有恐懼、抑郁、焦慮、緊張等消極情緒癥狀(王江洋, 來媛, 2015;張楚, 王江洋, 高亞華, 溫文娟, 王菲, 2016)。嚴重消極情緒可導致個體出現攻擊性或各種問題行為(Loney, Lima, & Butler, 2006),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孤兒學生消極情緒產生的相關機制。
一般公眾對于身份受損個體產生的刻板印象、偏見和歧視性反應即為公眾污名;當身份受污個體內化公眾污名,并將偏見和歧視指向自己,并產生刻板性認同,進而表現出有意無意的自我貶低時,就形成了自我污名(Corrigan,Watson, & Barr, 2006)。孤兒學生的自我污名是指孤兒學生對其孤兒身份污名的感知,以及將感知到的污名內化后對自我產生消極認同與感受的心理現象,具體表現為自我身份敏感、自我懈怠、自我疏離、自我狹隘等傾向(王江洋, 王曉娜, 李昂揚, 高亞華, 溫文娟, 2017)。自我污名通常出現于具有污名身份的弱勢人群中。國外研究發現,自我污名可以造成心理疾病患者自尊和自我效能感降低,并引發焦慮、抑郁等消極情緒(Lysaker,Roe, & Yanos, 2007)。國內研究也發現,自我污名對孤兒初中生抑郁情緒有正向預測作用(王江洋,李昂揚, 聶家昕, 2020)。自我污名降低個體自尊和自我效能感的心理機制在于個體自我認知方式的改變(Corrigan et al., 2006; Xu et al., 2019),進而導致解釋風格的改變(Usitalo, 2002)。解釋風格是個體習慣性解釋生活事件發生原因的方式,又稱歸因風格。其作為一種認知變量不僅與自我污名具有密切聯系,也會對個體情緒變化產生影響(Reardon & Williams, 2007)。此外,個體也會因把自我感知到的污名看作是一種壓力事件而削弱自身的領悟社會支持水平(范興華, 方曉義, 劉楊,藺秀云, 袁曉嬌, 2012; 劉方芳, 祝卓宏, 2014; Prelow,Mosher, & Bowman, 2006)。領悟社會支持是指個體感受到被尊重和受到支持的情感體驗以及滿意程度。以往研究表明,領悟社會支持可以顯著負向預測個體的抑郁、社交焦慮等消極情緒(王江洋, 于子洋, 2019; Maheri et al., 2018)。由此推測孤兒學生的自我污名、解釋風格、領悟社會支持與其消極情緒的產生有關。
1.1 自我污名與消極情緒的關系
Miller 和Major(2000)研究認為,只要是超出個體自身適應范圍的事件就可被當作壓力事件,污名可被看成是一種程度更深、影響更廣、時間更長的特殊壓力源。從這個角度說,用于解釋壓力與情緒二者關系的理論同樣也適用于解釋污名與情緒的關系。壓力源-情緒模型認為,個體對其身心健康產生威脅的各類壓力事件評估后就會產生壓力感,進而導致消極情緒的產生(Spector &Fox, 2002)。當具有污名身份特征的個體感知到來自外群體的偏見與歧視,這種自我感知的污名意識就構成一種特殊壓力源,使個體產生各種消極情緒。國外研究表明,自我污名可以增加心理疾病、肥胖癥,以及艾滋病患者的抑郁、羞恥等消極情緒(Li, Mo, Wu, & Lau, 2017; Lysaker et al., 2007;Magallares et al., 2017)。國內研究也表明,自我污名對孤兒初中生的抑郁情緒有顯著正向預測作用(王江洋等, 2020)。據此,可以推測自我污名與消極情緒之間有正向關聯,提出假設1:自我污名對孤兒學生消極情緒具有直接正向預測作用。
1.2 解釋風格的中介作用
具有污名身份的個體很可能是依據其感知到的他人對自己的污名評價而形成自我污名,表現出低自尊(Corrigan et al., 2006; Xu et al., 2019)。由于自尊對個體的解釋風格具有預測作用(陳舜蓬, 陳美芬, 2010),自我污名也可能會對個體解釋風格造成影響。Usitalo(2002)的研究驗證了感知污名對個體積極解釋風格的預測作用。由情緒ABC 理論可推知,如果個體長期保持不合理的解釋風格,就會導致其消極情緒的增加(Ellis,1962)。以往研究也證實解釋風格和消極情緒顯著相關(Gladstone, Kaslow, Seeley, & Lewinsohn, 1997;Reardon & Williams, 2007)。Clyman 和Pachankis(2014)開展的干預實驗也表明,促進樂觀解釋的干預可以對男同性戀者避免產生與污名有關的消極情緒有保護作用。據此,可以推測解釋風格在自我污名與消極情緒之間起中介作用,提出假設2:自我污名可以經負向預測解釋風格,解釋風格負向預測消極情緒的中介作用來實現對孤兒學生消極情緒的間接正向預測作用。
1.3 領悟社會支持的中介作用
依據領悟社會支持的壓力易損假說和社會支持威脅模型假說,領悟社會支持是一種壓力易損因子,與感知污名相類似的創傷或恥辱等壓力性事件會通過降低個體對社會支持的領悟能力對個體心理適應產生影響(王建平, 李董平, 張衛, 2010)。針對心理疾病患者及流動兒童的研究均證明了個體感知的污名與其領悟社會支持水平呈顯著負相關關系(范興華等, 2012; 劉方芳, 祝卓宏, 2014)。另一方面,社會支持主效應模型認為,社會支持是對個體具有普遍增益作用的保護因素,有助于減少抑郁等消極情緒(鄧琳雙等, 2012)。已有研究也證實領悟社會支持與孤兒中學生的消極情緒呈顯著負相關關系(王江洋, 于子洋, 2019)。也有研究進一步指明領悟社會支持就是聯結歧視知覺與個體心理健康或適應之間的中介變量(范興華等, 2012; Hatzenbuehler, 2009)。據此,可以推測領悟社會支持在自我污名與消極情緒之間起中介作用,提出假設3:自我污名可以經負向預測領悟社會支持,領悟社會支持負向預測消極情緒的中介作用來實現對孤兒學生消極情緒的間接正向預測作用。
1.4 解釋風格與領悟社會支持的關系
領悟社會支持是基于個體對社會支持的主觀解釋而形成,所以它受到解釋風格的影響(Norris &Kaniasty, 1996)。Weiner(1985)的歸因理論也指出,個體如果能積極地對社會支持做出歸因解釋,則可能拓展其歸因范圍,進而可更多地意識到幫助者的功勞,就會對社會支持產生更多領悟。針對大學生的研究表明,解釋風格可以顯著預測個體領悟社會支持能力(朱蕾, 卓美紅, 2015)。據此,可以推測解釋風格對個體的領悟社會支持具有預測作用,提出假設4:自我污名可以經由解釋風格-領悟社會支持的鏈式中介對孤兒學生消極情緒實現產生間接預測作用。
綜上所述,本研究關注到孤兒學生群體身份的特殊性,將由其身份帶來的自我污名與其消極情緒相結合,建構出關于自我污名、解釋風格、領悟社會支持與消極情緒四者關系的潛變量多重中介作用模型(見圖1),以對四者的關系機制進行深入考察。研究結果可為孤兒學校開展降低孤兒學生消極情緒的心理健康教育干預提供理論依據。

圖1 假設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向某省立孤兒學校四至九年級孤兒學生發放問卷863 份,剔除項目漏填較多及未作答的問卷48份,回收有效問卷815 份,有效回收率為94.44%。有效被試中,男生525 名,女生290 名;四年級68名,五年級86 名,六年級135 名,七年級171 名,八年級174 名,九年級181 名。
2.2 研究工具
2.2.1 自我污名
采用王江洋、王曉娜等人(2017)編制的孤兒學生自我污名自陳問卷測量孤兒學生的自我污名。該問卷共包含25 個項目,由自我身份敏感、自我懈怠、自我疏離、自我狹隘四個因子構成。問卷采用1~5 級評分標準,其中1 代表“從不這樣”,5 代表“總是這樣”。總分越高代表孤兒學生自我污名的程度越高。該問卷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擬合良好(χ2/df=2.78, CFI=0.95, TLI=0.94,RMSEA=0.04)(王江洋, 王曉娜等, 2017),結構效度較好。在本研究中,該問卷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95,自我身份敏感、自我懈怠、自我疏離、自我狹隘四因子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94、0.86、0.90、0.82。
2.2.2 解釋風格
采用馬丁·塞利格曼(1998)編制、洪蘭翻譯的兒童解釋風格問卷測量孤兒學生的解釋風格。該問卷由24 個積極情境項目組成積極解釋風格維度,24 個消極情境項目組成消極解釋風格維度。積極解釋風格分數越高代表個體越樂觀,消極解釋風格分數越高代表個體越悲觀。該問卷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擬合良好(χ2/df=2.34, CFI=0.95,TLI=0.93, RMSEA=0.05)(石國興, 林乃磊, 2011),結構效度較好。在本研究中,該問卷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1,積極與消極解釋風格維度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63 和0.53。
2.2.3 領悟社會支持
采用由Zimet,Powell,Farley,Werkman 和Berkoff(1990)編制,嚴標賓和鄭雪(2006)修訂的領悟社會支持量表測量孤兒學生的領悟社會支持。該量表共包含12 個項目,由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以及其他支持三個因子構成。采用1~7 級評分標準,1 代表“極不同意”,7 代表“極同意”。領悟社會支持總分越高代表個體對社會支持的領悟能力越高。該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擬合良好(χ2/df=4.84, CFI=0.92, GFI=0.94,RMSEA=0.08)(葉寶娟等, 2018),結構效度較好。在本研究中,該量表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9,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三個因子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78、0.80、0.80。
2.2.4 消極情緒
對陳文鋒和張建新(2004)修訂后的積極/消極情感量表中與消極情感相關的題目進行修改,形成修訂后的消極情感量表,以此測量孤兒學生的消極情緒。為使原消極情感量表同樣適用于小學學齡段,請1 名心理學教授及6 名應用心理學研究生對量表項目進行相應的修改與調整,確保所有孤兒學生能夠理解,并將原量表中的“感到非常孤獨或者與別人距離很大(在情感或興趣方面)”拆分成兩道題目“在情感方面,我覺得孤獨或與別人有很大距離”,“在興趣方面,我無法融入到其他人中”。修訂后的量表共包含7 個項目,描述了個體不同的消極情緒,如憤怒、抑郁、孤獨感等。采用1~4 級評分標準,其中1 代表“沒有”,4 代表“經常有”。消極情緒總分越高代表個體的消極情緒越高。對修訂后的量表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擬合良好(χ2/df=5.34,CFI=0.97, TLI=0.95, RMSEA=0.07, SRMR=0.03),結構效度較好。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3。
2.3 程序
為了確保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孤兒學生填寫問卷時的抵觸情緒及各種無關變量的干擾,本研究將題目數量相對簡短的問卷放在前面,相對較長的問卷放在最后,并按照積極-消極-消極-積極的排列順序以平衡可能因問卷內容性質相互影響而導致的順序效應。按照領悟社會支持量表、消極情感量表、孤兒學生自我污名自陳問卷以及解釋風格問卷的排列順序,將四種測量工具印刷并裝訂成冊。在得到孤兒學校調查許可的前提下,由該學校心理教師以班級為單位向各年級孤兒學生發放問卷,集體施測,現場回收。并使用SPSS22.0和Mplus7.4 對收集的數據進行整理及分析。正式分析數據前,采用Harman 單因素法對研究結果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進行檢驗。結果有25 個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其中第一個因子解釋率為17.49%,低于40%的臨界標準,故研究結果可以排除共同方法偏差的影響,可以開展后續的統計分析。
3 結果
3.1 孤兒學生自我污名、解釋風格、領悟社會支持和消極情緒的相關
采用皮爾遜積差相關檢驗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結果見表1。由表1 可知,自我污名各因子與消極情緒呈顯著正相關,與積極解釋風格呈顯著負相關,與領悟社會支持各因子呈顯著負相關;消極情緒與積極解釋風格呈顯著負相關,與領悟社會支持各因子之間呈顯著負相關;領悟社會支持各因子與積極解釋風格呈顯著正相關;消極解釋風格與其他變量各因子均相關不顯著(故后續不再分析)。以性別及年級為自變量,消極情緒為因變量進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孤兒學生消極情緒的性別主效應[F(1, 803)=0.04,p>0.05]、性別和年級交互作用[F(5, 803)=0.82,p>0.05]均不顯著,只有年級主效應顯著[F(5, 803)=4.95,,p<0.01]。故在后續結構方程模型分析中把年級作為統計控制變量。

表1 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與相關系數
3.2 自我污名對消極情緒的直接預測效應
以自我污名為自變量,消極情緒為因變量,年級為控制變量,檢驗自我污名對消極情緒的直接預測效應。模型各擬合指標達到可接受標準:χ2/df=5.13,p<0.01,CFI=0.98,TLI=0.97,RMSEA=0.07,SRMR=0.03。用Bootstrap 檢驗法(抽樣5000 次)檢驗,95%的置信區間為[0.46, 0.62],不包含0,說明直接預測效應顯著。由圖2可知,自我污名可顯著正向預測孤兒學生消極情緒(β=0.54,p<0.01),其后可加入中介變量進行分析。

圖2 自我污名對消極情緒的直接預測路徑圖
3.3 自我污名對消極情緒的間接預測效應:積極解釋風格及領悟社會支持的多重中介作用
建立以自我污名為自變量,消極情緒為因變量,積極解釋風格、領悟社會支持及解釋風格-領悟社會支持鏈為中介變量,年級為控制變量的結構方程模型。模型各擬合指標達到可接受標準:χ2/df=4.50,CFI=0.97,TLI=0.95,RMSEA=0.07,SRMR=0.04。用Bootstrap 檢驗法(抽樣5000 次)檢驗各個中介路徑的顯著性,結果見表2 及圖3。由表2 可知,模型各中介路徑95% 置信區間中均不包含0,說明圖3 中無論是自我污名→積極解釋風格→消極情緒、自我污名→領悟社會支持→消極情緒這兩條單獨中介路徑,還是自我污名→積極解釋風格→領悟社會支持鏈→消極情緒鏈式中介路徑均顯著(ps<0.01)。計算總間接效應值為0.05+0.17+0.02=0.24,總效應值為0.24+0.32=0.56,總間接效應在總效應中占比為0.24/0.56×100%≈43%。其中,積極解釋風格單獨中介效應占比為0.05/0.56×100%≈9%,領悟社會支持單獨中介效應占比為0.17/0.56×100%≈30%,積極解釋風格-領悟社會支持鏈式中介效應占比為0.02/0.56×100%≈4%;直接效應占比為57%。這表明,在自我污名對孤兒學生消極情緒的預測關系中,除直接效應外,主要通過積極解釋風格和領悟社會支持的各自中介作用以及二者的鏈式中介作用來實現。

表2 全模型中介效應的Bootstrap 分析

圖3 自我污名、解釋風格、領悟社會支持與消極情緒關系的多重中介作用路徑圖
4 討論
4.1 自我污名對孤兒學生消極情緒的直接預測
本研究發現自我污名可以直接正向預測孤兒學生消極情緒,驗證了假設1,并與以往研究一致(王江洋等, 2020)。污名是一種特殊壓力源,由于它常常與個體的社會身份相關聯,所以與其他壓力相比,其作用時間更長、影響及范圍也更廣(Miller & Major, 2000),包括易內化形成自我污名(Corrigan et al., 2006)。依據壓力源-情緒模型(Spector & Fox, 2002),如果孤兒學生感知到“孤兒”身份污名壓力,那么其在心理上就會自覺內化形成自我污名的壓力感,進而產生消極情緒。
4.2 自我污名經積極解釋風格中介對孤兒學生消極情緒的間接預測
本研究發現自我污名可通過負向預測積極解釋風格,積極解釋風格負向預測消極情緒,進而間接正向預測孤兒學生消極情緒,驗證了假設2。當孤兒學生感知到公眾對孤兒身份的刻板印象,便會產生自我污名的認知偏差,即使是遇到積極事件時,孤兒學生也很少將其歸因于自身的內在因素,進而導致其積極解釋風格水平較低。按照情緒ABC 理論,存在自我污名偏差的孤兒學生如果將積極事件的結果解釋為不可控的外在因素,則會產生消極情緒(Scheier & Carver, 1988)。此外,有研究表明個體的解釋風格可能同時擁有樂觀和悲觀兩個水平,因而對積極與消極事件的解釋風格是相互獨立的(曹素玲, 2014)。自我污名對孤兒學生消極情緒的間接預測作用可能恰好在于孤兒學生個體是否能夠合理發揮自己的積極解釋風格。
4.3 自我污名經領悟社會支持中介對孤兒學生消極情緒的間接預測
本研究發現自我污名可通過負向預測領悟社會支持,領悟社會支持負向預測消極情緒,進而間接正向預測孤兒學生消極情緒,驗證了假設3,并與以往研究一致(范興華等, 2012; 劉方芳, 祝卓宏, 2014; 王江洋, 于子洋, 2019)。根據領悟社會支持壓力易損假說及社會支持威脅模型的觀點(王建平等, 2010),如果自我污名這一特殊壓力較高,就會導致孤兒學生領悟社會支持水平下降。同時,本研究也與社會支持主效應模型觀點一致(鄧琳雙等, 2012),即領悟社會支持作為保護性因素,有利于孤兒學生緩解消極情緒。
4.4 自我污名經積極解釋風格-領悟社會支持鏈式中介對孤兒學生消極情緒的間接預測
本研究還發現自我污名可通過負向預測積極解釋風格,積極解釋風格正向預測領悟社會支持,領悟社會支持再負向預測消極情緒,這種鏈式中介作用進而間接正向預測孤兒學生消極情緒,驗證了假設4,與以往研究部分一致(朱蕾,卓美紅, 2015)。個體對社會支持的領悟有一部分是基于對社會支持的解釋而形成(Norris & Kaniasty,1996)。高自我污名孤兒學生往往把來自他人的模糊性社交信息理解為拒絕,并將其原因歸為自己的孤兒身份這種持續穩定的內部因素(王江洋, 王曉娜等, 2017),這容易導致對生活不滿,從而領悟不到他人發出的各種支持性信息,增加抑郁等消極情緒(王江洋等, 2020; 王江洋, 于子洋, 2019)。
5 結論
(1)自我污名可以直接正向預測孤兒學生消極情緒;(2)積極解釋風格、領悟社會支持、積極解釋風格-領悟社會支持鏈均可部分中介自我污名對孤兒學生消極情緒的間接預測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