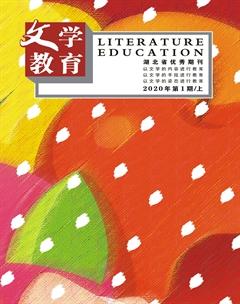從敘述模式和性別視角讀《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陳嘉敏
內容摘要:《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是香港作家西西的代表作,小說采用第一人稱、內聚焦的敘述模式向讀者講述了一個在殯儀館做化妝師的女子的生命體驗和感情經歷。本文按照現代小說的敘述模式和女性的性別視角來分析其文本的藝術價值。
關鍵詞:敘述模式 性別視角 藝術價值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寫于1982年,已成為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經典之作。小說是主人公“我”的內心獨白,講的是一個在殯儀館做化妝師的女子(“我”)在咖啡室等她的戀人夏一起去參觀她工作的地方:殯儀館化妝室。在等待的過程中,“我”開始回憶“我”和夏相識的經過,“我”選擇職業的過程。期間穿插怡芬姑母和她的戀人的故事,“我”年輕兄弟的故事,“我”的母親的故事等。
一.第一人稱的內聚焦敘述所構成的寬闊時空對話
在結構主義敘事學中,敘述視角是個重要概念。敘述視角是指視點、視角,強調的是觀照者的立足點、看的角度和看的觀點。《像我這樣的的女子》是以第一人稱的敘述視角,由“我”在敘說以及穿插“我”與他人的對話構成。以第一人稱講述故事的方法是一種精巧的、比其它方式有影響的方法。當然,不能把作為第一人稱的敘述者和作者本人混為一談。第一人稱敘述法的目的和效果是富于變化的。有時,這一方法的結果是使得敘述者比其它人物更少鮮明性和“真實性”,如小說《大衛·科波菲爾》中。相反,摩爾·弗蘭德斯和哈克·貝利芬卻是他們所在的故事中的中心人物。在愛倫·坡的第一人稱敘述小說中有時表面看起來是戲劇性的獨白《如小說《阿摩提拉多》),有時是一個痛苦的靈魂向人公開傾訴衷情的書面自白(如小說《揭發隱私的心》)①。顯然,《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采用第一人稱的目的和效果同后者是相似的。
在《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中,不僅是采用第一人稱敘述者,而且也就是故事中的中心人物。敘述始終聚焦于“我”的內心世界,即便有“我”和夏、“我”與怡芬姑母的對話以及年輕兄弟、朋友的只言片語,也是從“我”的視角出發的,換言之,不是完整對話的還原,而是經過“我”回憶的篩選。這一切都染上了“我”的感情色彩。即“我”所敘述出來的是一個有著“我”之色彩的世界。指出這一點很重要,因為由此我們進而可以說,敘述聚焦于敘述者內心世界,在客觀上也就刻畫了自我的性格,這是內聚焦的敘述模式。在第一人稱敘事和第三人稱敘事中都可以出現內聚焦敘事。熱奈持認為:“敘事作品中出現第一人稱動詞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情況,語法對二者不加區別,敘述分析則應分辨清楚:—是敘述者把自己稱作敘述者,一是敘述者和故事中的一個人物同為一人。”②這里第一人稱敘述顯然就是屬于第一種情況。在內聚焦中,敘述焦點與一個人物重合,于是他變成一切感覺,敘事可以把這個人物的感覺和想法全部告訴我們。
具體到《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的內聚焦,是指敘述始終聚焦于“我”內心情緒流動的軌跡。“我”似乎是個取景框,一切外在的事件都是由“我”這個取景框過濾后進入敘述視野的。對于這個文本內聚焦可以做如下細致分析。比如,小說中每一處對話部分都是簡明扼要的,說明作者有意刻畫一個安靜內向不愛與人交談習慣沉默的溫柔女子形象,這也就同她的成長環境(“我年紀很小的時候,我的父母都已經亡故了”)和特殊的工作環境(在殯儀館從事為死者化妝)是相吻合的,孤寂封閉的環境熏陶出她的內傾性格;而小說中每一處的敘說部分顯得完整而冗長,也刻畫出了一個沉浸在自我世界中有著細膩情感并喜歡對生活對人生終極問題思考探索的女子形象。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作為一種敘事性文體,從敘事模式的三個方面來看,可以概括為:從敘事時間來看,有別于傳統小說按線性時間的敘述,而是采用倒裝敘述、交錯敘述等多種敘述時間;從敘述角度來看,自白體小說決定了從“我”之視點去敘述,已經完全擺脫了純客觀敘事角度,為心理空間的開掘創造了方便;從敘述結構來看,則以“我”的內心世界感情的軌跡為聚焦點,以心理軌跡的運行帶動外在故事和人物之間的關系,外在故事行程和內心感情軌跡相互依托。
二.站在女性性別視角審視自我與世界
香港作家西西的大部分作品的視角都是立足于當代,她筆下的女性無論處于何種生活環境,都對自己有清醒的認識,都試圖把握命運,并對世界的某些問題追根溯源,從中也可感受到女性作家沖出束縛表現自我的強烈沖動和不同于男性作家的獨特視角。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從標題就可得知這個文本的主人公是一位女性,小說開篇就是“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其實是不適宜與任何人戀愛的”,為什么?于是從戀愛話題展開,我們聽著這位女子平淡卻又真切地訴說她的情感體驗、生命體驗。通過文本細讀,不難發現“命運”這個關鍵詞反反復復出現了11處之多,它左右著這位女子的心理、情感活動,左右著她對夏及其他人與事的認識。
文本中,女主人公具有明顯的相互矛盾的兩個方面。她過于自尊與自卑,承擔著過重的心理負擔。“對于生命中不可知的神秘面我們天生就有原始的膽怯”,這里的“我們”其實并沒有包括“我”,因為“我”是“并不害怕”“并不膽怯”“毫不畏懼”的。“在這個世界上,總的有人做這樣的工作,難道我的工作做得不夠好不稱職?”這里的反問也并不是對自我的質疑,其實是對自我的認同以及自我的肯定的。同時,她的自卑也是鮮明的,“我是一個不懂得保護自已的人,我的舉止和言語,都會使我永遠成為別人的笑柄”,“像我這樣一個讀書不多,知識程度低的女子,有什么能力到這個狼吞虎咽、弱肉強食的世界上去和別的人競爭呢”,所以她習慣沉默、不換職業。而文本最大的矛盾也是一直貫穿的沖突是她對于命運的看法,一方面是開篇就表明自己受命運殘酷的擺布并且沒有辦法反擊,接著也是不斷的自我暗示服從命運指引,然而對于年輕兄弟,她突然換了一種論調——“長長的一生為什么就對命運低頭了呢?”對于殉情男孩,更是發出了“一個沒有勇氣向命運反擊的人應該是我不屑的”聲音,此處已不是低回的敘述了,而是充滿了力量的聲音。雖然女子將這層態度僅限于“聲音”的抗爭之中,但至少我們看到了她的變化,她不是徹徹底底的宿命論者,對其是產生過反抗意識的,對命運也是追問與思索過的,生命的張力也就在人處于兩股相異的思想力量斗爭中綻放。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是一篇內心獨白小說,是一女子從自己的性別視角審視著自我、他人與世界。在這種“女性化”的敘述中或多或少的流露出對男性話語的遮蔽與叛離,對于工作對象,一殉情男子她拒絕對其尸體做修飾,“難道說他的自殺竟是一件快樂的事情?但我不相信這種表面的姿態,我覺得他的行為是一種極端懦弱的行為,一個沒有勇氣向命運反擊的人應該是我不屑的”。這是一種質疑、解構的聲音,帶有偏見的聲音,或許在男子自己心中這樣的方式是他認為勇敢的方式與樂意的選擇,每個人都有自己選擇生活方式與生活狀態的自由。對于她的愛戀對象——夏,在這個文本中行為的被動與心理刻畫的缺乏也使得他的形象不免蒼白、空洞,我們只知道他的名字——“夏”,明亮如太陽的名字,留給讀者的線索得到的就是一個模糊的“大男孩”形象,而“我”通過大篇幅的訴說個人體驗世界的感受以及對永恒主題的思考,在讀者面前就是一位成熟的女性形象,她對生活的深情與執著方面大大超越了男性,她清醒地審視著自我的精神世界。另者,對于這份情感,她不去問夏是否害怕,而是選擇帶著他直接去工作場地,并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獨自擔當夏的因害怕而離去的結果,這是一種高邁的、包容的、自覺的女性意識,“因為她不曾仰視并期待著男性的崇高與拯救,所以她不必表達對男性的失望與苛求;她所關注的是女性的自省,是對女性自我的質詢。”③
愛情主題是個恒久的話題,婚戀關系以及女人的尊嚴更是人類敏感的感情內容,我們對于文本的分析是對“這一個”文本的分析。《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站在女性視角,扣住了讀者情感能產生共鳴的母題,另一方面這篇小說選擇的是社會底層小人物邊緣群體的聲音,所以它帶給了我們別樣的審美經驗。
注 釋
①[美]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251頁。
②[法]熱拉爾·熱奈特:《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第174頁。
③戴錦華:《真淳者的質詢》,《當代作家評論》,1994年第5期。
(作者單位:深圳市高級中學(集團)東校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