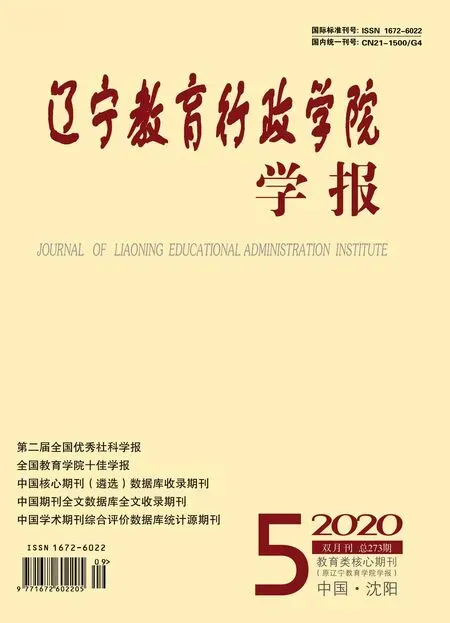法人治理結構視域下的民辦高校黨建工作研究
裴宇星
遼寧傳媒學院,遼寧 沈陽 110136
一、民辦高校黨建工作存在的問題
經過30多年的探索與實踐,民辦高校黨的建設已基本完成了基礎性工作,組織機構相繼建立、組織生活步入正軌、各項制度日益完善。黨的十八大尤其是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以來,民辦高校黨建工作不斷豐富內容與形式、創新載體與平臺,黨組織政治核心作用更加凸顯,黨建工作對民辦教育事業的引領和保障作用日益顯著。民辦高校黨建工作正以嶄新的面貌步入了新時代。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也應當清醒地認識到民辦高校黨建工作中還存在一些問題。
(一)黨建工作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目前國內的民辦高校辦學經費主要來源于個人或社會力量的投資興辦和學生的學費收入,不像公辦院校是政府投入,因此舉辦人決策時首要考慮的因素就是辦學收益和投資回報率。學校管理層也會把工作重心更多放在招生宣傳、教學科研、實習實訓、學生就業等一些“實”的方面,相比之下,黨建工作就顯得比較“虛”,見效也比較慢。于是乎,黨建工作不被重視,“重業務、輕黨建”成了幾乎所有民辦高校的通病。許多民辦高校沒有黨建工作的專項經費支持、黨組織開展活動缺乏時間保障,組織生活流于形式,思想建設流于表面,致使黨建工作的實效性大打折扣。
(二)黨建工作隊伍力量薄弱
民辦高校的舉辦人出于成本核算的考慮,在教職員工的配備、部門機構的設置方面往往要求高度精簡。不設專門的黨務工作部門,或將黨務工作部門與行政部門合署辦公。專職黨務干部隊伍少之又少,大都采取專兼結合兼職為主的方式。民辦高校大多黨務工作者身兼雙職甚至一身數職,科班出身很少,理論水平不高、黨務工作經驗缺乏,繁重的行政工作和管理工作重壓之下,黨建工作只能是疲于應付上級黨組織安排的需要硬性完成的任務,無從奢談工作的創新。另一方面,由于體制的原因使得民辦高校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始終圍繞辦學效益和業務工作,導致黨建工作和黨建工作隊伍處于邊緣化的處境,黨務工作者的職業發展受限,職業前景不明、上升通道狹窄,普遍缺乏職業榮譽感和工作的積極性,嚴重制約著民辦高校黨建工作的水平。
(三)黨組織參與決策的功能缺乏制度保障
在管理體制上民辦高校實行的是董事會(理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黨組織發揮政治核心而非領導核心作用,黨組織主要在辦學性質、辦學方向及學校的穩定和諧等宏觀層面發揮作用,而高校的人事、財務、機構設置、編制體制、管理模式等事項的決策權,則掌握在舉辦人控制的董事會手里。雖然《國務院關于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促進民辦教育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6〕81號)提出了推進民辦高校黨委班子和董(理)事會成員“雙向進入、交叉任職”,即民辦學校黨組織領導班子成員通過法定程序進入學校決策機構,黨員校長、副校長等行政機構成員,可按照黨的有關規定進入黨組織領導班子;建立黨政聯席會議制度等一系列創新舉措,但并沒有改變董事會決策領導、黨組織監督保障的法律定位和權力架構,在“資本權力”和“資本話語”的背景下,如何切實發揮黨組織的監督制約和政治指引作用,缺乏明確的制度保障。
二、制約民辦高校黨建工作發展的體制性原因剖析
(一)資本逐利性與教育公益性的矛盾
教育是一項以人才培養為目標的崇高的公益性事業。不論是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社會還是文化的傳播和傳承,教育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從根本上來說不是為了謀求經濟利益、獲取利潤,而是為社會培養所需要的合格人才,提高國民的整體素質,推動科技創新文化進步,促進國民經濟增長,服務社會公共事業,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教育關乎社會公共利益,事關社會的進步、民族的未來乃至整個人類的福祉。因此,公益性是教育的根本屬性。無論政府投資辦學,還是個人或社會力量投資辦學,都要堅持教育的公益屬性。《民辦教育促進法(2018修訂)》第三條規定:“民辦教育事業屬公益性事業,是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
與歐美發達國家私立大學大多為捐資辦學不同,我國的民辦高校一般由個人或社會力量投資興辦。資本的逐利性不會因為其進入領域的不同而改變。社會資本一旦進入教育領域,不可避免引發投資者對于高校財產權、投資回報和辦學收益的預期和訴求。資本的天性是貪婪的、趨利的,逐利性是資本的本質屬性。出于資本運作的規律,民辦高校舉辦者勢必追求低成本高收益,往往忽視教育規律,盲目擴大辦學規模、開設市場熱門專業。因此說資本逐利性和教育公益性的矛盾,是制約民辦教育健康發展的體制性矛盾。
(二)出資人控制與法人治理的矛盾
理論上來說,非營利性民辦高校的出資人以捐贈的方式出資到學校,成立具有獨立人格的民辦學校法人,對內采取社會共同治理的管理模式,內部管理機構由董事會(理事會)、校長和大學評議會或教授會構成。我國的民辦高校在形式上也能依照《民辦教育促進法》及其實施條例的規定,設立理事會、董事會或者其他形式的決策機構,體制上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然而實踐中,由于我國的民辦高校通常都是個人、企業等社會力量投資辦學,這種因個人投資辦學而出任董事長的民辦高校董事會,常常因學校創辦人天然的影響力和創辦人的特殊地位,而使董事會完全服從于個人意志,董事會集體決策形同虛設。因為缺少社會力量的捐資、投入,董事會構成缺乏多樣性和代表性,導致大多數民辦高校都是家族式管理,董事會中多數成員或骨干成員均為家族成員,董事長與校長合而為一,形成了一種由投資者控制的單邊治理模式。在董事會中,資本勢力一家獨大,缺少內部的監督制衡機制,雖然建立起了形式上的法人治理的結構,但實質上仍然實行的是自然人治理。
(三)出資人所有權與民辦高校法人財產權的矛盾
隨著近代公司制度的誕生,通過法人這個制度設計,使所有權與控制權實現了分離。投資人投入公司的資本成為法人資產,公司對其擁有法人財產權。公司財產唯一主體屬于法人,公司作為獨立存在的法人,享有對其財產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而出資人所有權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出資人可以任意轉讓其擁有的股票,但卻不能直接處置公司的財產。
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能有效配置投資者、決策者和管理者的權利,實現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是民辦高校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必然要求。按照法律規定,民辦高校的舉辦人在投資設立民辦高校后,學校作為獨立的法人實體便享有了獨立的財產權,投資人不再擁有學校的財產權,在高校存續期間必須保證高校法人財產的完整性,無權處置學校的財產。而在實踐中,民辦高校舉辦人使用、支配學校的收入,或通過運用各種會計方法和資本運作技術,最大限度地提取回報的現象普遍存在,實質是由于投資人所有權與法人的財產權界限模糊,而導致的對法人財產權的侵權行為。
(四)黨建工作政治性與投資人片面追求辦學效益的矛盾
中組部、教育部黨組早在2000年6月印發的《關于加強社會力量舉辦學校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中就提出:“社會力量舉辦學校的黨組織在教職工和學生中發揮政治核心作用。”隨后在《關于加強民辦高校黨的建設工作的若干意見》中,進一步強調要“充分發揮民辦高校黨組織凝聚人心、推動發展、促進和諧的作用,為促進民辦高校的健康發展提供堅強有力的政治保證。”
雖然民辦高校的黨建工作與投資人的辦學效益,在學校發展的根本利益和長遠目標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學校發展建設的具體過程中,政治方向與經濟利益往往是不一致的,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和教育公益性原則,與辦學效益兩種價值取向常常會發生碰撞和沖突,這就造成民辦高校舉辦人的一種矛盾心態:一方面希望黨組織發揮保障作用;另一方面對黨組織的監督作用又是抱有戒備甚至排斥的心理。
三、落實法人治理是解決民辦高校黨建工作問題的根本途徑
(一)明晰法人屬性,落實分類管理
在民辦高校分類管理制度框架下,應當明確營利性民辦高校是營利性組織,可采取營利法人(在我國是企業法人)的法律形態;而非營利性民辦高校則是非營利組織,可登記為民辦事業法人或民辦非企業。《民辦教育促進法》第十九條規定:“民辦學校的舉辦者可以自主選擇設立非營利性或者營利性民辦學校。”一旦選擇設立非營利性民辦學校,則舉辦者不得取得辦學收益,學校的辦學結余全部用于辦學。《國務院關于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促進民辦教育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6〕81號)第五條指出:“對民辦學校(含其他民辦教育機構)實行非營利性和營利性分類管理。非營利性民辦學校舉辦者不取得辦學收益,辦學結余全部用于辦學。”
我國民辦高校的舉辦人一般選擇非營利屬性法人,而非營利法人通常要同時具備以下三個條件:一是不能以營利為宗旨;二是不取得經濟回報;三是不享有該組織的所有權。但是在實踐中,多數民辦高校雖然選擇了非營利法人的類型,卻可以通過采取各種會計策略和資本運作手段,變相從民辦高校辦學收益中取得回報甚至轉移資金,因此需要政府有關部門出臺具體法律制度,對非營利法人的財務制度、激勵機制和合理回報做具體的規范,將分類管理制度落到實處。
(二)明確舉辦人與民辦高校法人財產權的關系
《民辦教育促進法》第36條規定:“民辦學校對舉辦者投入民辦學校的資產、國有資產、受贈的財產以及辦學積累,享有法人財產權。” 第37條進一步指出:“民辦學校存續期間,所有資產由民辦學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占。”也就是說民辦高校自成立的那一天起,便具有了自己獨立的法律上的“人格”,是一個不依賴于投資人的獨立的經濟實體,可獨立地支配學校資產的營運,享有對高校資產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而舉辦人則不再能直接支配學校財產的營運,不能從學校的經營中獲取財產凈收益的,也不能在學校解散清算后獲得剩余資產。這也就意味著民辦高校的舉辦人自投資辦學開始,基本失去了對他投入民辦高校財產的實質所有權。舉辦人只能通過董事會等決策機構間接參與高校管理運營。
當前從政府層面需要進一步完善制定與《民辦教育促進法》及其實施條例相配套的法律法規,從法律層面保護民辦高校的法人財產權不受侵占。通過出臺操作性強實踐性強的法律法規,規范舉辦人的行為,避免舉辦人回收、抵押、租賃和轉讓學校財產或是借助財務方法和資本運作技術,變相攫取回報的行為,破壞民辦高校法人財產的完整性。
(三)確保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避免“出資人控制”
民辦高校法人治理結構脫胎于公司治理結構,是指民辦高校作為一個獨立的法人實體,在舉辦者(投資人)、決策者(董事會)、管理者(校長)和教職工等其他利益相關方之間,建立的有關學校運營與權利配置的機制或組織結構,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一整套權責分明又相互制衡的運行機制。本質上是一種基于財產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分離情況下的所有人與代理人之間關系的制度安排。[1]
民辦高校的法人治理結構,必須建立在舉辦者所有權、高校法人財產權和辦學者辦學權相互分離的基礎上,構建所有權、決策權、辦學權三者相互制衡與監督約束,以權力制約權力的有效機制。法人治理結構,從制度上很好地解決了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情況下的代理問題,打破了“家族化”治理模式,真正實現了從自然人治理向法人治理、由投資人單邊治理向社會共同治理模式的轉變。“分權制衡”是法人治理的重要原則和基本特征,而“校董合一”則是完全不符合法人治理結構精神的。因此,為避免“出資人控制”確保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民辦高校的董事長(理事長)不應當同時兼任學校的校長。
(四)健全監督機制,充分發揮黨組織的監督保障職能
由于民辦高校發展歷史較短,相關的法律制度、運行機制尚在摸索完善之中,由此造成國內絕大多數學校都沒有建立常設的監督機構,導致投資人“一家獨大”,董事會決策權力被架空,法人治理結構徒有形式,內部權力制衡機制失調。對于公司法人來講,一般由監事會行使監督職能。建立健全利益相關人參與的監督機制,充分發揮黨組織的監督職能,是實現民辦高校法人治理分權與制衡的有力保證。
為了更好地反映和代表各方面利益,增進監督實效,監事會的人員除了學校黨組織負責人、工會或教職工代表以及學生代表外,還應吸收教育行政部門的代表和家長代表參加。監事會的負責人可以由學校黨組織負責人兼任。[2]
為更好發揮其監督職能,監事會不應對董事會負責而應向省級教育行政部門負責。從代表性來看,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是專業的教育管理機構,最適合作為民辦高校內部“資方”以外的眾多利益相關方的代表。從權威性來看,教育行政主管部門還具有較高的行政權威,有權對民辦高校實施相應的獎懲,這些特點使得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最適合成為民辦高校監事會的負責對象。民辦高校黨組織的負責人(政府派駐學校的督導專員)擔任監事會的負責人,為黨組織“引導和監督學校遵守法律法規,依法治教、規范管理”的監督職能發揮,提供了組織的和制度化的保障。[3]進而構建一套以董事會為權力機構、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的執行機構和以黨委(監事會)三角結構的權力制衡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