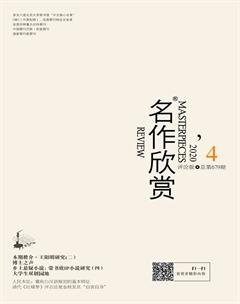精神成長之花
摘 要:《秋天的懷念》三次提及菊花。初提菊花,史鐵生的精神世界是自我封閉的;再提菊花時,史鐵生的精神世界有了更進一步的成長,對于命運和人生進行初步探索;終賞菊花,實際上也是史鐵生精神世界的感悟新生。
關鍵詞:《秋天的懷念》 菊花 自我封閉 初步探索 感悟新生
《秋天的懷念》是一篇看似篇幅短小卻意蘊豐富的散文。全文通過三次“看花”展開脈絡:為了讓殘疾的史鐵生重新拾起對生活的希冀,母親提議去看菊花但被拒絕;母親再次提議去看菊花,“我”同意,但卻沒能實現;母親走后,妹妹推“我”去看菊花。菊花的三次出現無疑展現出一種母愛的情感體驗。但從更深層面看,菊花也成為史鐵生精神成長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個見證者。
一、初提菊花:精神世界的自我封閉
菊花第一次被提及,是在“我”剛剛雙腿癱瘓后。母親知道,對于失去雙腿的兒子來說,任何寬慰都顯得無關痛癢,也正因如此,母親向“我”提出去看菊花,因為菊花是一種喜愛陽光,耐寒而又適應性強的植物,母親想讓“我”像菊花一樣,以堅強樂觀的態度去面對生活,去“好好兒活”。但此時的“我”還尚未走出癱瘓所帶來的痛苦,目光所至,不論美丑,“我”都暴怒無常。例如“望著望著天上北歸的雁陣,我會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聽著聽著李谷一甜美的歌聲,我會猛地把手邊的東西摔向四周的墻壁”。因為當“我”沉浸于景物和歌聲之中時,癱瘓的雙腿帶來的痛楚和傷感會比往日更狂烈地向“我”襲來,這是一種陡然而至的失意和無助。正是這樣的感覺,讓“我”更加感覺自身的可悲,不愿與外界再去接觸。而雁陣的自由和歌聲的甜美與“我”的生活之間又形成了一種鮮明的對比,使“我”更加清醒地認識到自己行動的不自由和生活的不甜美。實際上,“我”的這種暴怒的情緒化并不完全是針對外界的,更多的是因為不完美、有缺憾的自己,因為在這個時間段,“我”的精神世界是排斥與外界的任何關聯的,是選擇自我封閉的。
在聽到母親看菊花的提議后,“我”除了暴怒無常,不乏還充斥著對生活的自怨自艾。在正值盛放的年齡遭遇癱瘓,承受了他人所不能的磨難,所有的驕傲與狂妄,都被囚系于一方輪椅之上。面對這樣的境遇,“我”選擇捶打自己的雙腿,傷害自己,沉浸在自己痛苦而又封閉的精神桎梏中,看不見因我而有著巨大生活變動的母親,本來愛花的母親因為“我”的癱瘓,沒有了去照顧花的時間和心情,她侍弄的花兒都死了;“‘我看不見母親在‘我暴怒時的忍耐與壓抑,看不見母親怎樣收拾起被‘我砸碎的玻璃和被‘我摔壞的東西,看不見母親怎樣‘悄悄地躲出去,一個人一邊擦掉淚水一邊‘在我看不見的地方偷偷地聽著我的動靜,甚至悄悄地走進來”a。因為此時“我”的心中只是充斥著自己的不幸與悲憤,無暇顧及外界。此時的“我”選擇將精神世界封閉起來,為自己建立了無形的桎梏。
二、再提菊花:精神世界的初步探索
菊花在文中的第二次出現,是在秋天。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內心的痛苦也隨之被沖淡些許,精神狀態也比之前好了許多,獨自坐在屋中看著窗外落葉飄零。母親再次提議去看菊花,這次,“我”果斷同意。這一次菊花的出現,是“我”精神世界成長的關鍵線索,同時也在“我”的心中烙下了難以抹去的印記。
在這一時間,“我”與母親能夠開始有意識的大量交流,這些與母親的對話也正暗示了“我”不再像以前一樣暴怒無常,過度情緒化,而是開始主動建構理性的思維。值得注意的是,在描寫母親進屋時,用的是“擋”在窗前,這一小小的細節雖然不夠惹人注意,卻充滿了母性光輝,因為母親為“我”擋住的,不僅是屋外紛飛飄零的落葉和寂寥的秋色,更是怕“我”隨之沉湎的內心。實際上,正是因為此時“我”的心境初步進入一個相對平穩的階段,不再封閉自我的精神世界,“我”才會留心母親這一舉動,關注到母親憔悴的臉,建構對母親的理解,從而開始平靜而有意識地思考。
“好吧,就明天”去北海看菊花,短短幾個字,語句極為干脆,語調又極為淡然,看似敷衍隨意,實際上是對母愛的順水推舟,是“我”主動踏出探索外界的第一步,暗含了“我”對命運的初步思考,開始用新的眼光去審視這個世界。此時的“我”放下了對命運的抱怨,不再為人生的不公而自怨自艾,而是轉而開始去領悟生命的真諦,學會去淡然地看待生命中的挫折,在母親為“我”點亮的生命之光下逐漸走出心靈的困境。
之所以在前文提及這一次的菊花是“我”精神世界成長的關鍵線索,是因為這次看菊花的約定并沒有實現,母親病故了。母親的離世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對“我”來說,意味著“少了生活的拐棍,少了精神的慰藉,少了人生的指引”b。但這一次“我”沒有選擇自暴自棄,沒有喜怒無常的情緒化,而是對母親深深的懊悔和無盡的自責。“我卻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經到了那步田地”,“我沒想到她已經病成那樣”,“也絕沒有想到那竟是永遠的訣別”這三句是全文里最深刻的懊悔。“我”恨自己,只關注自己的痛苦,忽略了母親的艱辛。由此開始,因為母親的離去,“我”和母親看菊花的約定未曾完成,“我”才會因此懊悔,才會去試圖理解并遵從母親所說的“好好兒活”,“‘好好兒活——樸素的不能再樸素,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一句話,涵蓋了那么多復雜的感情——母親就是以自己殘缺而悲苦的余生,教給兒子如何面對有缺憾的生命”c。人不能只為自己好好兒活,還要為他人好好兒活。“我”開始去嘗試理解母親的“好好兒活”。至此,“我”的精神世界有了更進一步的成長,“我”對于命運和人生也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
三、終賞菊花:精神世界的感悟新生
如果說第二次菊花的出現在“我”的心中烙下了難以抹去的印記,那么最后一次菊花的出現則讓“我”真正讀懂生命的奧義。菊花的最后一次出現是在母親走后的一個秋天,妹妹推著“我”去北海看菊花。
在最后觀賞菊花時,文章對菊花有了更多的細節描寫:“黃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潔,紫紅色的花熱烈而深沉,潑潑灑灑。”秋天是一個蕭瑟的時節,風雨如晦令人心畏,枯枝敗柳讓人憂愁。然而,卻是在這樣的時節里,積蓄了三個季節的能量與生機的菊花蓬勃綻放了,顯示了它高傲的風貌。此處雖是寫菊花紅白紫交相輝映,但更多的卻像是在寫人生精神:“淡雅”展示了一種生活態度,“高潔”顯露了一種品格風骨,“熱烈而深沉”表現了一種思想感情,“潑潑灑灑”更是包含了一種氣概與神色。這一段菊花的描寫不僅構成了一幅美麗的風景畫卷,更是繪出了生命的真諦。
“我”看著五彩繽紛的菊花,想起了母親和她未說完的話。母親和“我”看菊花的約定就像是打開“我”精神世界的一把鑰匙,當“‘我完成看花這一約定,也并非有意為之,可當‘我意識到‘看花這一行為是曾經的約定時,就截然劃分出一個時間點,明白了‘我的成長”d。正是為了履行與母親“看菊花”的這個約定,“我”才完成了精神世界最終的自我成長。菊花雖然一開始是“我”和母親口頭約定的信物,但最后卻是見證“我”成長的一個象征物。
“我”最終選擇走出家門,去觀賞菊花,實則也是去迎接未來嶄新的人生——走出了之前自己設下的精神桎梏。“我”由一開始暴怒無常的情緒化,到開始主動探索人生、思考命運,再到最終獲得感悟與新生,也正是從自我封閉的精神世界到敢于直面命運并重獲新生的精神世界的成長歷程。而這其中的關鍵和著眼點,便是貫穿全文的菊花。
四、結語
著名作家葉傾城曾說:“易朽的是生命,似那轉瞬即謝的花朵。然而永存的,是對未來的渴望,是那生生世世傳遞下來的、不朽的、生的激情。每一朵勇敢開放的花,都是一個死亡唇邊的微笑。”e花朵生來就被賦予奉獻與犧牲的宿命,《秋天的懷念》借由菊花的三次出現,讓史鐵生的精神世界逐步獲得成長,切實地完成自我救贖,真正重新思考生命的價值與意義。文末菊花的綻放,既是對生的報答與饋送,更是對死亡的反抗與搦戰,也是對母親所說“好好兒活”的最佳詮釋。
a 宓毓旸:《看見與看不見——〈秋天的懷念〉研讀》,《語文教學通訊》2014年第9期,第58頁。
b 羅愛平:《一支激情澎湃的生命頌歌——〈秋天的懷念〉之探微》,《中學語文教學參考》2018年第23期,第66頁。
c 竇桂梅:《比“母愛”更深邃的——我這樣教〈秋天的懷念〉》,《語文教學通訊》2005年第8期,第53頁。
d 韓一嘉、許孟陶:《母愛缺席的成長與心靈釋放的救贖——〈秋天的懷念〉的敘事動力》,《中學語文教學》2017年第9期,第56頁。
e 葉傾城:《死亡唇邊的微笑》,《大眾科技》1999年第12期,第17頁。
參考文獻:
[1] 陳海蓉.從“感知母愛”到“自我救贖”——我讀史鐵生散文《秋天的懷念》[J]. 語文知識,2016(16).
[2] 孫琪.《秋天的懷念》文本解讀與教學價值的確定 [J].中學語文教學,2018(4).
[3] 李前尚.秋天的懷念,感人的瞬間——穿珠引線話懷念 [J].語文教學通訊,2015(8).
[4] 唐潔.由文到人:散文深度學習的探索——以《秋天的懷念》為例 [J].語文知識,2017(3).
[5] 宗華.批判精神是將設計變成現實的橋梁——《秋天的懷念》教學設計批判 [J].語文知識,2017(15).
作 者: 姚金宜,哈爾濱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院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學科教學語文。
編 輯:趙紅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