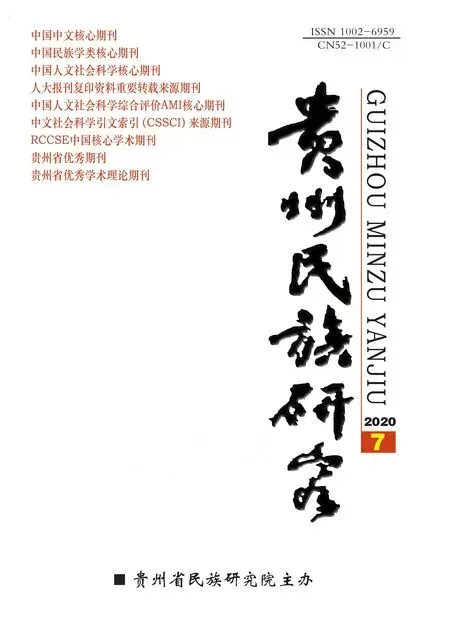從多民族地區(qū)的無字方言談?wù)Z言翻譯的悖論
——以貴州方言為例
張湖婷
(貴州師范學(xué)院 外國語學(xué)院,貴州·貴陽 550000)
一、語言翻譯定義與語言翻譯標(biāo)準(zhǔn)的討論
翻譯理論的核心內(nèi)涵是翻譯定義和翻譯標(biāo)準(zhǔn)。
最初人們雖然沒有對(duì)翻譯下一個(gè)明確的定義,但自打有翻譯的歷史以來,歷代譯家都自然而然地認(rèn)為翻譯是語言翻譯問題。以至于現(xiàn)代,中外都不言而喻地圍繞語言為中心對(duì)翻譯一詞進(jìn)行定義。《現(xiàn)代漢語詞典》1999年7月修訂第三版345頁將翻譯定義為:“把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dá)出來(也指方言與民族共同語、方言與方言、古代語與現(xiàn)代語之間一種用另一種表達(dá))”。《學(xué)生新華大字典》2016年第1版第172頁將翻譯定義為:“把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dá)”。《新華漢語詞典》2017年8月第二版第266頁也將翻譯定義為:“把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dá)”。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尤金·A·奈達(dá)(Eugene A.Nida) 對(duì)翻譯的定義是:“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用漢語翻譯過來,尤金·A·奈達(dá)(Eugene A.Nida) 對(duì)翻譯的定義是:“所謂翻譯,是指從語義到語體(風(fēng)格) 在譯語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對(duì)等語再現(xiàn)原語的信息”[1]。可見,中外翻譯的定義,都是以語言為基準(zhǔn),圍繞語言路線進(jìn)行的討論。
數(shù)千年翻譯研究說明,語言翻譯定義既是數(shù)千年語言翻譯的理論概括,又是數(shù)千年語言翻譯標(biāo)準(zhǔn)研究的方向標(biāo)。不管譯者是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認(rèn)識(shí)語言翻譯定義,語言翻譯定義作為一種無形的方向標(biāo),始終導(dǎo)引著歷代譯家按照如何將原語轉(zhuǎn)向?yàn)樽g語的方向去研究語言翻譯標(biāo)準(zhǔn)問題。
翻譯是與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相適應(yīng)的范疇,中外翻譯標(biāo)準(zhǔn)的研究伴隨著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三個(gè)發(fā)展階段:
第一階段:“文字翻譯”標(biāo)準(zhǔn)階段。“文字翻譯”標(biāo)準(zhǔn)階段主要從文字層面研究翻譯活動(dòng)。最初的翻譯活動(dòng),由于生產(chǎn)力比較落后,文化環(huán)境因素簡單,人類交流溝通的需求簡單,翻譯未上升到理論高度加以認(rèn)識(shí)。翻譯活動(dòng)僅僅只局限于佛經(jīng)翻譯,而且是字對(duì)字、詞對(duì)詞的硬譯。在中國,最早的翻譯是從佛經(jīng)翻譯開始,“早在東漢年代(公元2世紀(jì)) 就開始了系統(tǒng)的佛經(jīng)翻譯活動(dòng)”[2]。在國外,公元前4世紀(jì)中期羅馬帝國的西塞羅之前,處于字對(duì)字、詞對(duì)詞的硬譯階段。
第二階段:“語言翻譯”標(biāo)準(zhǔn)階段。生產(chǎn)力的快速發(fā)展,使翻譯標(biāo)準(zhǔn)的研究從文字層面上升到語言層面。這一階段,翻譯活動(dòng)逐漸上升到理論高度加以認(rèn)識(shí),譯者以句子、話語以及整個(gè)作品為翻譯單位,以語言規(guī)范和語言學(xué)理論為基礎(chǔ)研究翻譯,產(chǎn)生了大量的語言翻譯標(biāo)準(zhǔn)。“在我國的翻譯史上,后漢三囯時(shí)代的譯經(jīng)大師們一般都采用直譯方法;而后秦時(shí)代的譯壇盟主鳩摩羅什一改以前譯家古直風(fēng)格,主張意譯;初唐時(shí)三藏法師玄奘則自創(chuàng)‘新譯’”[3]。近現(xiàn)代,清末馬建忠提出了“善譯”的翻譯標(biāo)準(zhǔn),八國聯(lián)軍以后嚴(yán)復(fù)提出“信、達(dá)、雅”的翻譯標(biāo)準(zhǔn),民國時(shí)期梁實(shí)秋、趙景深派提出“寧順而毋信”的翻譯標(biāo)準(zhǔn),魯迅派提出“寧信而毋順”的翻譯標(biāo)準(zhǔn),王佐良提出“照原作”的翻譯標(biāo)準(zhǔn)等等。改革開放以來,系統(tǒng)理論逐漸引入翻譯標(biāo)準(zhǔn)的研究,司顯柱、陶陽[4]搜集梳理了國內(nèi)2004年以來10余年數(shù)十篇相關(guān)論文,這些論文,都是“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xué)立足于對(duì)語言使用的研究”。這些翻譯標(biāo)準(zhǔn),都是緊緊圍繞語言翻譯進(jìn)行的討論。在“語言翻譯標(biāo)準(zhǔn)”中, 尤以嚴(yán)復(fù)的“信、達(dá)、雅”三字真經(jīng)影響深遠(yuǎn),至今仍發(fā)揮巨大作用。在嚴(yán)復(fù)的三字真經(jīng)影響下,翻譯的定義有人就理解為:“翻譯是在準(zhǔn)確(信)、通順(達(dá))、優(yōu)美(雅)的基礎(chǔ)上,把一種語言信息轉(zhuǎn)變成另一種語言信息的行為”。在國外,公元前4世紀(jì)中期羅馬帝國的西塞羅“明確地使用了‘以詞譯詞’ (word for word translation,即‘逐詞翻譯’) 和‘以意譯義’ (sense for sense translation,即‘意譯’) 等術(shù)語概念。他提倡‘意義對(duì)意義’而非‘詞對(duì)詞’”[5]。之后,賀拉斯(Horace) 提出“靈活翻譯”、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 提出“歸化和異化”的翻譯標(biāo)準(zhǔn),等等。20世紀(jì)開始,“一些學(xué)者開始引用語言學(xué)理論研究翻譯,這批學(xué)者被稱為西方翻譯研究中的語言學(xué)派”[6],其翻譯研究以現(xiàn)代語言學(xué)理論為基礎(chǔ)。國外主要的語言翻譯標(biāo)準(zhǔn)還有:尤金·奈達(dá)(Eugene A.Nida) 的“動(dòng)態(tài)對(duì)等”、紐馬克(Peter Newmark) 的“兩種方法、克特福德(J.C.Catford) 的“語言學(xué)觀”、克里斯蒂娜·諾德(Christiane Nord) 的“功能翻譯理論(functionalism)”等。
第三階段:“文化翻譯”標(biāo)準(zhǔn)階段。這是一個(gè)剛開始的歷史時(shí)期。由于生產(chǎn)力高速發(fā)展,文化環(huán)境因素高度復(fù)雜化,人類交流溝通的需求也高度復(fù)雜化,從語言翻譯規(guī)范和語言學(xué)理論角度研究翻譯標(biāo)準(zhǔn)已不適應(yīng)翻譯需要,有學(xué)者嘗試尋找新的翻譯理論“元”泉,從文化層面研究翻譯標(biāo)準(zhǔn)。與前兩個(gè)階段不同,文字、語言翻譯階段直接針對(duì)文字、語言研究翻譯標(biāo)準(zhǔn),而“文化翻譯”階段則是針對(duì)影響、制約文字、語言翻譯的文化環(huán)境研究翻譯標(biāo)準(zhǔn)。在中國,1933年,林語堂在《論翻譯》 一文中提出“翻譯是一門藝術(shù)”的“翻譯美學(xué)觀”,“將美學(xué)引入翻譯研究,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shí)踐上,美學(xué)對(duì)翻譯都有著特殊的意義”[7]。“傅雷在1951年《高老頭·重譯本序》中便提出了‘獨(dú)樹一幟、卓然成家’的‘神似’說:‘以效果而論,翻譯應(yīng)當(dāng)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8],對(duì)翻譯研究有極大的啟示作用。但其“神似”說的理論基礎(chǔ)仍是“語言翻譯”。比較有影響的,還有錢鐘書在“化境說”中借用佛經(jīng)的“投胎轉(zhuǎn)世”,許淵沖提出“三美論”美學(xué)準(zhǔn)則, 都是從文化層面研究翻譯,實(shí)質(zhì)仍未跳出語言翻譯定義的框框。在國外,鑒于語言翻譯標(biāo)準(zhǔn)的局限性,國外譯家極盡努力想從文化層面探討新的翻譯標(biāo)準(zhǔn)路徑。從1972年霍爾姆斯發(fā)表《翻譯研究的名與實(shí)》一文開始,越來越多的學(xué)者采用描述性或結(jié)構(gòu)性范式從文化層面研究翻譯標(biāo)準(zhǔn)。以色列學(xué)者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 在20世紀(jì)70年代從形式主義出發(fā)提出了多元系統(tǒng)理論,將系統(tǒng)理論引入翻譯理論研究,從文學(xué)本身的運(yùn)作來討論翻譯標(biāo)準(zhǔn)。1990年,英國學(xué)者巴斯奈特(S.Bassnett) 與美籍比利時(shí)學(xué)者勒菲弗爾(A.Lefevere) 在《翻譯、歷史與文化》一書中提出“文化翻譯”理論和“文化轉(zhuǎn)向”說。認(rèn)為翻譯是文化內(nèi)部與文化之間的交流,翻譯不應(yīng)以語言為單位而應(yīng)以文化為單位,以語言為單位的翻譯應(yīng)向以文化為單位的翻譯轉(zhuǎn)向。國外“文化翻譯”標(biāo)準(zhǔn),還有圖里(Gideon Toury) 的“文化制約規(guī)范”、斯內(nèi)爾-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 的“綜合法”、勒菲弗爾(Andre Lefevere) 的“改寫理論”和“三因素論”,等等,都比較有影響。這些討論,都似乎要尋找新的翻譯理論“元”泉,但都未跳出語言翻譯框框的束縛。
以上翻譯標(biāo)準(zhǔn)的三個(gè)發(fā)展階段,形成了“文字翻譯→語言翻譯→文化翻譯”三個(gè)翻譯標(biāo)準(zhǔn)層次,但都未脫離語言翻譯理論定義下的語言翻譯標(biāo)準(zhǔn)的討論。
我們把語言翻譯理論稱為“一元翻譯理論”,“一元翻譯理論”的元定義稱為“一元翻譯定義”,“一元翻譯理論”的元標(biāo)準(zhǔn)稱為“一元翻譯標(biāo)準(zhǔn)”,“把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dá)出來”,認(rèn)為是“語言翻譯”理論的“元定義”和“元標(biāo)準(zhǔn)”。
二、從貴州無字方言的翻譯談?wù)Z言翻譯的悖論
國家推廣普通話,多民族聚居地區(qū)的漢語言文字使用的都是統(tǒng)一的普通話漢字。但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56個(gè)民族語言融合發(fā)展、交流互鑒,形成了無數(shù)具有地域特點(diǎn)的漢語言無字方言。“方言發(fā)展軌跡受少數(shù)民族語言、外來語言和自身演變的滲透及影響,形成了漢語方言與民族語融合發(fā)展的特殊反映形態(tài)”[9],這種特殊反映形態(tài)往往只有語音表達(dá)而無文字記載。
以多民族地區(qū)的貴州為例,據(jù)多彩貴州官網(wǎng)[10]介紹:貴州2017年末常住人口3580萬人,其中少數(shù)民族人口占36.3%,有苗族、布依族、侗族等17個(gè)世居少數(shù)民族。另據(jù)貴州大學(xué)楊軍昌教授等[11]研究,貴州“少數(shù)民族的人口總量在全國位居第四,比重位居第五,在我國56個(gè)民族中,除塔吉克族和烏孜別克族外在貴州省均有居住”。多民族聚居必然形成多民族語言的交流互鑒,漢語言中必然融匯出許多地域性的無字方言。多民族地區(qū)無字方言的翻譯,對(duì)面向世界全方位人文交流開放的翻譯帶來挑戰(zhàn)。貴州作為多民族地區(qū),如何翻譯多民族地區(qū)的無字方言,顯現(xiàn)出翻譯的難點(diǎn),也折射出語言翻譯理論的缺失。
貴州漢語言在長期的多民族語言交流互鑒的過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在漢語言中沒有對(duì)稱性文字表達(dá)而僅有語音形式的無字方言。貴州方言,不太注意卷舌音,不太注意兒化音,聲調(diào)大多為第二聲,而且不少發(fā)音在漢語拼音中沒有規(guī)范的拼讀方法。貴州無字方言大致有三種情況:
一是漢語字詞典中完全查找不到對(duì)應(yīng)字詞但有相似音調(diào)的漢字替代發(fā)音的無字方言。這種替代方言發(fā)音的替音漢字僅發(fā)音相似,且替音與方言發(fā)音并不完全相同,而意思與替音漢字也完全不同。如:“一哈哈”,貴州方言的發(fā)音是“yí hā hā ”,普通話的意思是“一會(huì)兒”;“我喝”, 貴州方言的發(fā)音是“wó hō”,普通話的意思是“完蛋了”,是貴州方言的感嘆詞;“作不住”,貴州方言的發(fā)音是“zuó bú zú”,普通話的意思是“受不了”;“假巴耳飾”,貴州方言的發(fā)音是“jià bā ér sí”,普通話的意思是“假仁假義”;“慣實(shí)”,貴州方言的發(fā)音是“guán sí”,普通話的意思是“溺愛”等等。這些方言的發(fā)音,即使我們采取了不規(guī)范拼讀法,實(shí)也難以達(dá)到原音的“原生態(tài)”。無論我們是將貴州方言翻譯成任何文字,或者是我們將任何文字翻譯成貴州方言,我們?cè)诜g時(shí)都無法做到“把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dá)出來”。因?yàn)椋@些方言的替音漢字僅是一個(gè)抽象的替音形式,無表達(dá)文字。
二是漢語字詞典中完全查找不到對(duì)應(yīng)字詞又無相似音調(diào)的漢字替代發(fā)音的無替音漢字的無字方言。這種方言,只能以不規(guī)范的漢語拼音拼讀方法去發(fā)音。這類方言的翻譯情況又如何呢?如貴州人邀約朋友:“我們明天要kí打雞洞玩,你kí不kí”。這個(gè)讀音“kí”的方言,在漢字中不僅無對(duì)應(yīng)文字, 也找不到“kí”字讀音的字來替代發(fā)音, 只能以不規(guī)范的漢語拼音拼讀方法去發(fā)音。這個(gè)讀音“kí”的方言發(fā)音,是“去”的意思。“kí”是“去”,貴州當(dāng)?shù)厝硕贾肋@個(gè)意思。這個(gè)意思,雖無文字表示,但卻是貴州各民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chǎn)生活中形成的對(duì)人的行為方式共同認(rèn)可的一種思維習(xí)慣。如果我們要把這句話翻譯成外語,“kí”是無替音漢字的無字方言,外語也就沒有對(duì)稱性的語言文字可供擇用,翻譯時(shí)就只能進(jìn)行思維習(xí)慣的轉(zhuǎn)換,然后在譯入語中尋求最貼切(妥帖、確切) 的語言文字來表達(dá),語音、文字只是思維習(xí)慣的表達(dá)形式。
三是用方言發(fā)音說漢語字詞的無字方言。如“角落”,普通話的發(fā)音是“jiǎo luò”,而貴州方言的發(fā)音則是“guó luō”。這類方言與第二類有相似之處,不容易區(qū)分,區(qū)別在于該類方言是直接用貴州方言發(fā)音“讀”漢字。因“讀”音不同,方言和漢民族共同語的思維習(xí)慣也就不同。
由于地域性方言是僅有語音的無字方言,在翻譯時(shí),無論我們是將方言翻譯成任何文字,或者是我們將任何文字翻譯成方言,我們?cè)诜g時(shí)都無法做到“把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dá)出來”。因?yàn)椋窖员旧硎菬o字語音,與其他語言沒有意義對(duì)稱的語言文字,無法做到“把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dá)出來”。
可以舉一個(gè)貴州方言語音語句,將其翻譯成規(guī)范普通話文字,從翻譯過程來討論其折射出的理論問題。
例如,方言:我喜歡吃“maó lá gó”。
譯文1:我喜歡吃“西紅柿”。
譯文2:我喜歡吃“番茄”。
這句話中的貴州方言的發(fā)音是“maó lá gó”,它的替音漢字是“毛辣果”。如果將這句含方言發(fā)音的方言語句翻譯成普通話文字,我們?cè)鯓臃g呢?譯者如果通曉普通話,那么例1中屬普通話的發(fā)音“我喜歡”的意思不言自明。但如果譯者不是貴州方言區(qū)人,而“maó lá gó”由于屬于貴州地域方言,譯者漢語共同語的知識(shí)儲(chǔ)備中肯定搜索不出“maó lá gó”這一地域性方言發(fā)音的詞語。這時(shí)候,這句話中的方言語音“maó lá gó”一詞,在譯者思維狀態(tài)中反映的只是“maó lá gó”這一抽象的語音形式。“maó lá gó”這一抽象的語音形式,只是地域方言區(qū)人群在長期的相互交流中,對(duì)交流對(duì)象這一種蔬菜在相互大腦中形成的共同認(rèn)可的思維習(xí)慣的一種思考方式。要將“maó lá gó”翻譯成普通話文字,譯者需要知道這句方言的“maó lá gó”語音在原語人群中的思維習(xí)慣即思考方式指的交流對(duì)象是什么,才能將方言語句的思維習(xí)慣的語音表達(dá)的“我喜歡吃‘maó lá gó’”的意思,翻譯轉(zhuǎn)向?yàn)樗季S習(xí)慣高度相似的普通話的語言文字“我喜歡吃‘西紅柿’”或者“我喜歡吃‘番茄’”的意思。在翻譯過程中,“maó lá gó”只是地域方言區(qū)人群對(duì)交流對(duì)象共同的思維習(xí)慣的語音表達(dá)形式,譯者要將“maó lá gó”的語音翻譯成普通話,譯者需要確切知道原語“maó lá gó” 的語音表達(dá)形式是一種蔬菜交流對(duì)象的思維習(xí)慣,才能從漢民族共同語的思維習(xí)慣中去尋找同一交流對(duì)象思維習(xí)慣最佳相似度最貼切(妥帖、確切) 的語言文字“西紅柿,番茄”來表達(dá)。
“西紅柿,番茄”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實(shí)際上翻譯的是交流對(duì)象的思維習(xí)慣,而不是方言語音,翻譯并未實(shí)現(xiàn)“把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dá)出來”,實(shí)現(xiàn)的只是將原語交流對(duì)象語音的思維習(xí)慣轉(zhuǎn)向?yàn)樽g入語同一交流對(duì)象語音文字的思維習(xí)慣,“maó lá gó”、“西紅柿,番茄”只是不同思維習(xí)慣的表達(dá)形式。這一過程,并非是“把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dá)出來”的過程,而是把一種思維習(xí)慣轉(zhuǎn)向?yàn)榱硪环N思維習(xí)慣的過程。這一過程中,方言音節(jié)和普通話字詞的意思,是不同思維習(xí)慣的表達(dá)形式,方言語音和普通話文字的意義,起到的只是同一交流對(duì)象的思維習(xí)慣的表達(dá)作用。顯然,這里討論的思維習(xí)慣的翻譯與語言文字的翻譯就有了本質(zhì)區(qū)別,思維習(xí)慣翻譯的翻譯對(duì)象是同一交流對(duì)象的思考方式和方法,語言翻譯的翻譯對(duì)象是語言文字的意義,一個(gè)翻譯的主體是內(nèi)容,一個(gè)翻譯的主體是形式。
同理,將任一語言文字翻譯成另一語言文字,也都是一個(gè)尋求思維習(xí)慣的最佳相似性理解的翻譯轉(zhuǎn)向過程。由此追溯數(shù)千年的翻譯歷史,翻譯開始也并非是直接就能“把一種語言文字的意義用另一種語言文字表達(dá)出來”,而同樣是先通過認(rèn)識(shí)同一交流對(duì)象原語人群的思維習(xí)慣,再將原語人群的思維習(xí)慣作為參照物,再在譯入語中尋求、判斷、選擇兩種思維習(xí)慣的“最佳功能契合點(diǎn)”[12],最后在譯入語中尋找最貼切的文字、語言表達(dá)形式,才能形成思維習(xí)慣的翻譯轉(zhuǎn)向。后人將表達(dá)這些思維習(xí)慣的相似點(diǎn)的對(duì)稱性的語言文字逐步整理出來,才根據(jù)思維習(xí)慣的相似度逐漸形成兩種語言文字意思相對(duì)應(yīng)的字詞典和語言規(guī)范。不同字詞典中的多種釋義和多種語言規(guī)范,只是不同人群文字語言表達(dá)形式的多種思維習(xí)慣。翻譯過程應(yīng)先尋求、判斷、選擇同一交流對(duì)象兩種思維習(xí)慣的“最佳功能契合點(diǎn)”,才能在文字語言多種釋義的多種思維習(xí)慣的表達(dá)形式中,去尋找譯入語最佳相似性理解最貼切的文字、語言表達(dá)形式。
至此,對(duì)無字方言的翻譯討論,可以得出這樣的認(rèn)識(shí):翻譯是思維習(xí)慣的翻譯。由此,我們提出了一個(gè)“思維習(xí)慣翻譯”理論,將思維習(xí)慣翻譯理論稱為“二元翻譯理論”,其元定義和元標(biāo)準(zhǔn)稱為“二元翻譯定義”和“二元翻譯標(biāo)準(zhǔn)”。
根據(jù)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對(duì)思維習(xí)慣翻譯理論的“二元翻譯定義”和“二元翻譯標(biāo)準(zhǔn)”作出界定:
思維習(xí)慣翻譯理論的“二元翻譯定義”是:翻譯是將交流對(duì)象原語的思維習(xí)慣轉(zhuǎn)向?yàn)樽g入語的思維習(xí)慣。
思維習(xí)慣翻譯理論的“二元翻譯標(biāo)準(zhǔn)”是:將交流對(duì)象原語的思維習(xí)慣作為參照物,在譯入語中尋求、判斷、選擇兩種思維習(xí)慣的“最佳功能契合點(diǎn)”。
這樣,翻譯就存在語言翻譯、思維習(xí)慣翻譯的兩個(gè)“元翻譯理論”“元翻譯定義”“元翻譯標(biāo)準(zhǔn)”的悖論!
三、語言翻譯悖論的解悖
“悖論是表面上同一命題或推理中隱含著兩個(gè)對(duì)立的結(jié)論,而這兩個(gè)結(jié)論都能自圓其說。……所謂解悖,就是運(yùn)用對(duì)稱邏輯思維方式發(fā)現(xiàn)、糾正悖論中的邏輯錯(cuò)誤。”[13]
我們認(rèn)為:思維習(xí)慣翻譯“悖論”和語言翻譯“原論”,是翻譯內(nèi)容與翻譯形式、翻譯主體與翻譯客體、思維內(nèi)容與思維形式的不對(duì)稱。我們可以用對(duì)稱邏輯思維方式得出這樣的認(rèn)識(shí):語言翻譯理論的“一元翻譯定義”與“一元翻譯標(biāo)準(zhǔn)”是翻譯形式,思維習(xí)慣翻譯理論的“二元翻譯定義”與“二元翻譯標(biāo)準(zhǔn)”是翻譯內(nèi)容。形式和內(nèi)容形成對(duì)立統(tǒng)一的對(duì)稱性邏輯關(guān)系,也就實(shí)現(xiàn)了語言翻譯、思維習(xí)慣翻譯悖論的解悖。
當(dāng)我們將語言翻譯的“一元翻譯定義”“一元翻譯標(biāo)準(zhǔn)”界定為翻譯的形式,將思維習(xí)慣翻譯的“二元翻譯定義”“二元翻譯標(biāo)準(zhǔn)”界定為翻譯的內(nèi)容,就可以用內(nèi)容和形式對(duì)立統(tǒng)一的哲學(xué)觀點(diǎn)來認(rèn)識(shí)原論和悖論的關(guān)系。按照對(duì)立統(tǒng)一的哲學(xué)觀點(diǎn):內(nèi)容決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內(nèi)容,矛盾雙方可以互相轉(zhuǎn)化。因此,思維習(xí)慣翻譯理論決定語言翻譯理論,語言翻譯理論反作用于思維習(xí)慣翻譯理論,其定義和標(biāo)準(zhǔn)亦如此。
實(shí)現(xiàn)解悖以后,我們可以根據(jù)以上的討論提出一個(gè)“兩元翻譯理論”及“兩元翻譯定義”“兩元翻譯標(biāo)準(zhǔn)”的概念,對(duì)語言翻譯理論和思維習(xí)慣翻譯理論的概念進(jìn)行形式和內(nèi)容的統(tǒng)一,作出“兩元翻譯理論”“兩元翻譯定義”“兩元翻譯標(biāo)準(zhǔn)”的界定。
“兩元翻譯理論”是兩合一基礎(chǔ)翻譯理論:翻譯是語言翻譯形式的元定義、元標(biāo)準(zhǔn)和思維習(xí)慣翻譯內(nèi)容的元定義、元標(biāo)準(zhǔn)的統(tǒng)一。
“兩元翻譯定義”是兩合一基礎(chǔ)翻譯定義:翻譯是將交流對(duì)象原語的思維習(xí)慣轉(zhuǎn)向?yàn)樽g入語的思維習(xí)慣,用最貼切的語言文字表達(dá)。
“兩元翻譯標(biāo)準(zhǔn)”是兩合一基礎(chǔ)翻譯標(biāo)準(zhǔn):翻譯是將交流對(duì)象原語的思維習(xí)慣作為參照物,在譯入語中尋求、判斷、選擇兩種思維習(xí)慣的最佳功能契合點(diǎn)最貼切的語言文字表達(dá)。
四、結(jié)語
論文通過對(duì)多民族地區(qū)無字方言翻譯問題的討論,提出了“語言翻譯理論”的“一元翻譯理論”“一元翻譯定義”“一元翻譯標(biāo)準(zhǔn)”和“思維習(xí)慣翻譯理論”的“二元翻譯理論”“二元翻譯定義”“二元翻譯標(biāo)準(zhǔn)”兩個(gè)悖論。論文用形式和內(nèi)容對(duì)立統(tǒng)一的哲學(xué)觀點(diǎn)進(jìn)行了解悖,提出了“兩元翻譯理論”“兩元翻譯定義”“兩元翻譯標(biāo)準(zhǔn)”的概念,進(jìn)行了形式和內(nèi)容的統(tǒng)一,作出了“兩元翻譯理論”“兩元翻譯定義”“兩元翻譯標(biāo)準(zhǔn)”的界定。論文認(rèn)為翻譯理論、翻譯定義、翻譯標(biāo)準(zhǔn)應(yīng)存在形式和內(nèi)容兩個(gè)不同的研究方向,對(duì)翻譯研究和翻譯評(píng)價(jià),具有一定的理論和實(shí)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