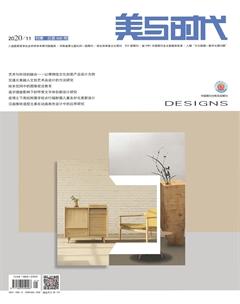女性主義視角下“女性題材屏風畫”初探
摘 ?要:通過對古代來女性題材屏風畫的部分分析可以理解在不同朝代,女性題材的屏風畫風格之轉變的社會必然性。在男權至上的社會里,女性被男性以自私的目光牽制著,使女性越來越符合仕女屏風畫中無獨立人生追求的美女花瓶設定,并把這種花瓶烙印以文字、繪畫等形式經久傳承。
關鍵詞:女性主義;屏風畫;女性形象
女性主義發端于西方19世紀末的婦女解放運動,在1990年代以后伴隨著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涌入,開始在中國知識女性中傳播。國內學術界進而掀起了與女性主義理論相關的獨特視覺文化語言探索的熱潮。女性題材的屏風畫,是從漢代開始逐漸流行開來的一種受歡迎的人物畫類型,在這一類型人物畫中,當時社會環境中的性別與權力兩者之間暗含的杠桿關系躍然紙上。這種藝術創作和政治生活之間盤根錯節的關聯性,使女性自身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的弱勢地位一目了然,也最能直接地讓我們感受到古代女性地位與我們所了解的現實世界之間的真實距離。
一、女性形象顯露的時代權利與政治
“在中國歷史上有很長一段時期,關于屏風的種種話語乃是圍繞著屏風前假想的一位男性坐者或臥者發展出來的,盡管實際生活中女性也擁有和使用屏風。”[1]99在漢代之前以及漢代時期的典籍記載中都只發現談及男性使用屏風的話語。他們認為屏風畫中的女性角色是為坐在屏風前的男性所準備的,主要是一些要求女子恪守“賢妻良母、守節整齊、咸曉事理”的教化故事。歷史學家班固記錄了西漢成帝有圖繪商代昏君紂王與妲己飲酒尋歡的一扇屏風,以此告誡自己不可被女色所迷惑,否則就可能遭受紂王一樣的亡國命運。從古至今人們對于商朝的滅亡都歸咎于一個稱為“狐貍精”的絕色女子身上,而后無論哪個朝代,這類絕色女子一旦在統治者的后宮出現,就會被視為迷惑君王、國家衰退的符號象征。然而,這卻是古代一些男子畏縮卑鄙的切實證據,反映了在男權社會下男性為了打壓和束縛女性而對女子的一種敵視態度。如果紂王有治國安民的雄才大略的話,妲己真的能成為毀壞千里之堤的蟻穴嗎?這顯然是那個時期男尊女卑的社會意識的反映,這種意識為社會里的最高權力者做掩護,讓這個社會看起來似乎自然而永恒。“福柯曾說,權力只有在‘戴上面具,將自己遮蓋大半時才能讓人忍受。父權社會加諸女性的權力論述戴著自然的面紗—邏輯的面紗。”[2]這也就證實了為什么史官即使記載紂王昏庸無道,但罪魁禍首還是歸結為女性,仿佛沒有此類女子的蠱惑,他就可以保住江山。與其說這類屏風畫是為了起到警醒君王、權貴的作用,不如說是為了成全當時父權社會體系下男子迫使婦人俯首帖耳、百依百順的炫耀,其目的并不是為了規勸男子,而是為了達到使男性統治女性成為天然無需證明的真理,從而保證男性在各個領域凌駕于女子之上,讓她們在男性權威下全心全意地為男性服務,不可存逾越之心,不可去質疑男人的合法統治地位,否則就是有違倫常。
二、女性形象中暗含的男性凝視目光
到了北魏時期,屏風繪畫中的女性形象發生了重大變化,女性逐漸從被政治權力打擊和規范轉變為純粹的男性審美欣賞和承載欲望的視覺對象,女子形象的存在意義更多的是因其帶來的美妙視覺感受,而男子對女子的真實期盼也反映得越發直接。《列女傳》記載喪偶之婦梁高行被梁王看中,以至梁高行自我剪鼻毀容,拒絕再嫁。這個故事在東漢和北魏出土的石制屏風中都出現過。東漢時期的梁高行石屏畫面構圖簡單,人物用線單純,在形體上沒有太多復雜的描繪,屏面僅呈現故事的主要瞬間,梁高行正拿起剪刀準備毀容;而北魏時期出土的石屏畫場景和線條都更加復雜,能夠使觀賞者在人物角色中感受到由文字轉化而來的深入人心的柔弱女子風情與高傲男子氣質之間的疏離感,這幅石屏畫因而變得比乍看之下要復雜得多,寡婦與國君兩人之間的畫面關系構成了一種性別化的兩極對立,一個是 “受男性凝視”的符號象征——美女,一個是“發出凝視動作”的人群代表——梁王。這種不同身份所激起的對立與當時社會的性別意識密切相關。正如勞拉·馬爾維關于男性凝視所說的“女人作為形象,男人作為觀看的承擔者”[1]9。這句話用來概述女性題材屏風畫的視覺化轉變,簡直恰當至極。這種將女性置于畫面焦點,在眾目睽睽下觀看的構想,不論從行為或身份上來看,觀看者—男性的權利都凌駕于被觀看者—女性之上,也可以說這種行為安排完全是為了滿足男子窺視異性的心理欲望及快感,這些自我創造的畫面使男性可以墜入白日夢的幻境當中。這一時期的父權文化,致使畫家和墓主人對女性題材屏風畫的趣味,從勸誡內涵轉變為吸引男性目光的女性形象。
三、女性形象中男性赤裸的視覺化欲念轉變
女性形象在繪畫中發生明顯風格轉變的一幅畫是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可以說以這一作品為開端,女子在當時男子眼中的作用愈加審美化和欲念化,女性形象毫無遮掩地暴露出權力掌握者的自然本性,展現出其內心深處渴望的性幻想對象。
到了唐代,女性題材的屏風畫在經受了不同朝代的淬煉后風格發生了較大的轉變,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仕女屏風,男性形象從此類屏風中消失,畫面僅剩下作為唯一視覺觀賞對象的“衣袂飄飄、纖塵不染”的富有誘惑力的女性形象。這種仕女屏風由隱喻內涵轉化為情色意象圖畫,女性形象完全被欲念化和視覺化以后,男性統治者當然不再允許男人們和這種情欲象征的觀賞物同席而坐。但是,即使男性不再出現,也不用懷疑他們會受到忽視和遺忘,因為父權社會絕對不會忽視男性中心的統治地位和代表性力量。
唐代以來現存的最具代表性的仕女屏風就是現稱為《簪花仕女圖》的作品。盡管現在這幅作品的形式并非屏風畫,但有學者在對其進行研究修復的過程中發現,它是由三塊絹面拼接而成的畫面,而這三塊絹面應該是從同一屏風的三個不同扇面上拆下來的。英國藝術史家蘇利文有一篇關于中國屏風畫的文章,也提到有關屏風畫會被重新裝裱為卷軸畫的實例。
根據傳世的古代繪畫作品以及考古發現的墓葬壁畫中的屏風畫,使我們對古代屏風的陳設和用途有了更多的了解,安放在男性床榻周圍的屏風畫與放置在女性床榻周圍的屏風畫在大小、式樣以及圖像內容上都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從《簪花仕女圖》的尺幅和內容來看,有學者認為它與《韓熙載夜宴圖》中的一種環繞床榻的低矮屏風相似。畫中女性與觀賞者的距離如此親近,那么《簪花仕女圖》中的女性形象為何創造得如此精致誘人也就可以理解了。仕女屏風的此種擺設位置,清晰地顯露出權貴內心打造的美女幻境世界,隱晦地傳達著文人墨客們的內心祈求和愿望,這是一種典型反映中國式皮格馬利翁神話的表現形式。誠然,這些文人墨客不僅是所有描述魅惑女性的主體,也是所有色情欲望產品的消費者與創新者,而在這種意識形態下的社會中,消費者永遠是對的。通過對藝術與性的隱晦關聯控制,男性及其幻想也制約著情色世界的想象力。
就《簪花仕女圖》上的圖像來看,美人的身體透過薄若蟬翼的紗衣若隱若現,紗衣上面點綴著彩色圖案,誘惑著欣賞者去窺探衣服之下的美麗身體。另一方面,畫中美人的目光被吸引到蝴蝶、花叢等形象上,這些形象映射著她們對男子以及自由的期盼和渴望。在這樣一幅美人圖中,觀賞者—男性對待她們的態度是既想貪婪地欣賞和占有,但又對她們近乎情色的著裝存貶低和輕視之心。就像在西方深受畫家們喜愛的圣經題材蘇珊娜沐浴中出現的鏡子一樣,男性畫家一方面將蘇珊娜描繪成一個嫵媚漂亮的裸體女人正在鏡前欣賞她美麗的身體,“另一方面他們還將鏡子作為女性好虛榮的象征。然而這種說教才最虛偽。你畫裸女,因為你愛看她。你在她手中放一面鏡子,稱之為虛榮,于是,你一方面從描繪她的裸體上得到滿足,另一方面卻在道德上譴責她。”[3]可以看出中西方男性為鞏固處于中心地位的男權文化的某些相似心理,反正誰掌握著“話語權力”,誰就在社會中占據主導位置。
隨著朝代更迭變換,男性統治者的審美趣味發生變化,因而后來的仕女屏風畫中的女性形象不再似唐代那樣豐滿嫵媚。后世仕女形象開始追求傷感、憂郁和病態的纖細,女性形象在男性世界觀中日漸消瘦下去,而男性的膨脹自大心理卻日漸高漲起來。女性形象充當著最常規的賞玩性角色,和他的男性供養者待在一起時給人一種在男性羽翼保護下歲月靜好的感覺。在這種邏輯下看待女性,如果一女子表現出內心苦悶的情緒,那問題的原因一定是出自女子自身,或是女性不遵從禮教而愿意拋頭露面,或是女性勇于追求自主人生而不滿于安逸的生活,反正全是女人的問題,男子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們對女性的束縛和限制。在這種男子文化霸權的統治下,女子的獨立思考能力和識破男性狹隘私心的可能性被降到最低,讓她們自覺自愿地做男性社會的仆人。
四、結語
通過對古代來女性題材屏風畫的部分分析,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人類在進化過程中還沒有改變的本能,尤其是男性對于女性的歧視和性渴望,動物性加上社會性的雙重復雜因素,致使女性形象常常有意無意地被作為社會變化時期的某種代碼”[4]。也就可以理解在不同朝代,女性題材的屏風畫風格之轉變的社會必然性。在這種男權至上的社會里,女性被男性以自私的目光牽制著,并且男性自己也和女性一樣都被這一套謬論洗腦,使女性越來越符合仕女屏風畫中無獨立人生追求的美女花瓶設定,并把這種花瓶烙印以文字、繪畫等形式經久傳承。
參考文獻:
[1]巫鴻.重屏 中國繪畫中的媒材與再現[M].文丹,譯.黃小峰,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2]諾克林.女性,藝術與權力[M].游惠貞,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9.
[3]伯格.觀看之道[M].戴行鉞,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50-51.
[4]徐虹.女性:美術之思[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123.
作者簡介:于海燕,山東師范大學美術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