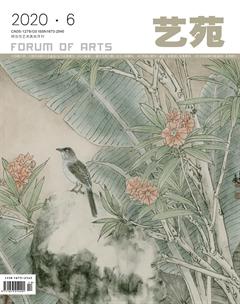“后疫情時代”數字吸引力電影的潛能與未來
朱晨
【摘要】 毋庸置疑,這一次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使電影行業遭遇了史無前例的“寒冬期”,影視作品的制作、發行、放映等都紛紛受到重創。值得欣慰的是,疫情在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隨著《八佰》的“破冰”,緊跟其后的國慶檔影片也屢創佳績,截至10月8日下午,國慶檔的票房接近40億,取得了今年電影業的大豐收。在“后疫情時代”背景下,數字吸引力電影作為一種具備推銷功能的電影形態,將成為全球電影市場的“寵兒”,5G時代的到來為數字吸引力電影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在數字技術不斷更新的大背景之下,中國電影在保證技術的同時,也急需探索屬于國產影片自身的標識。
【關鍵詞】 “后疫情”;數字吸引力;數字技術;電影市場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
“數字吸引力電影”最早由新西蘭學者列昂·葛瑞維奇提出,是在湯姆·甘寧“吸引力電影”(1)的基礎之上發展而來,“即由新興的各種數字技術所創造出的奇觀影像。數字吸引力標志著敘事和吸引力之間的再平衡,使兩者并非在爭斗中此消彼長和/或一方支配另一方”[1]165。正如《農夫與放映機》里所體現的早期電影對觀眾帶來的沖擊,百年后的今天,當人們第一次戴上3D眼鏡,沉浸在詹姆斯·卡梅隆所創造出的夢幻世界時,我們與20世紀90年代被銀幕上飛馳而來的火車嚇得四散而逃的觀眾并無二致。新興技術媒介下的數字電影同樣驗證了電影誕生初期的“火車效應”。在甘寧看來,這并不是觀眾對這種“再現現實”的輕信,而是電影的機械裝置所創造出來的幻象使觀眾呈現出震驚的狀態,這種“驚詫美學”并不是源于早期記錄電影對于現實的完整復制,而是新興的媒介與機械裝置對于影像的轉化過程。正如甘寧所說:“吸引力電影的拍攝方法是一次展覽主義者的呈現,同此后敘事電影發展起來以后所引入的隱藏窺視者的電影完全相反。這種絕無僅有的視線展示非常明顯是屬于在剪輯成為電影主導之前的某個時期。”[ 2 ] 1 1 1無論是以盧米埃爾兄弟為代表創作的紀錄片,抑或是以梅里埃為代表創作的故事片都是通過制造幻覺引發觀眾的好奇心,成為“興趣的中心”。
人們對于電影機械裝置的探索從未停止過,1968年,庫布里克執導的《2001:太空漫游》打開了數字化影像的大門,斯皮爾伯格、喬治·盧卡斯以及詹姆斯·卡梅隆等導演都致力于將數字技術運用于電影制作的各個環節中。2009年《阿凡達》第一次將3D虛擬影像攝影系統、IMAX、表演捕捉技術以及面部捕捉頭戴設備相結合,開啟了數字吸引力電影的新時代。此后,無論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還是《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都在一次次突破觀眾的觀影習慣。3D、VR、CG成像技術、無人機航拍等技術都體現了消費時代數字吸引力的中心地位。
一、類型化:景觀敘事與倫理建構
此次新冠疫情波及全球,經過全國上下的共同努力,疫情暫時得到了緩解,但其帶來的極大的經濟代價以及對大眾帶來的心理創傷將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當前,我們正處于疫情集中爆發之后的一段時間,也稱“后疫情時代”,但這并不意味著疫情的終結,而是它的延續。從更深層面來講,這是一次重大的集體事件,關乎民族集體記憶與歷史創傷,而“后疫情時代”包含了人們對于這場災難的反思,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概念的理解也必定會更加深刻。
電影行業在經歷了寒冬之后必定會迎來新的突破。1929正值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普羅大眾都沉浸在失業的悲痛之中,也正是這時美國的電影業迎來了最為輝煌的黃金好萊塢時期。查理·卓別林、奧黛麗·赫本、瑪麗蓮·夢露、克萊克·蓋博、葛麗泰·嘉寶等明星都成為影院的寵兒,觀眾也在他們的號召之下紛紛走入電影院,沉浸在夢工廠制造的幻影中。而這個時間節點也正值有聲電影誕生初期,從一定意義上看,也體現了新興技術對觀眾的吸引力。這與《阿凡達》放映后觀眾的表現極其相似,據媒體報道,很多觀眾在放映結束后都遲遲不愿走出影院、摘下眼鏡,有的甚至要去尋求心理醫生的幫助。雖然身處兩個時代,但新興技術對觀眾產生的吸引力卻從未改變。
5G技術為影視創作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疫情又為影視創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創作者完全可以利用其構建中國的災難電影。“疫情”電影已有很長的歷史。1976年著名的《卡桑德拉大橋》上映后便大受歡迎,自此,一系列疫情電影都以視覺奇觀為主要表現對象。美國的《傳染病》《鐵線蟲入侵》、韓國的《流感》等都從不同視角對人類生態、道德困境、倫理建構等議題進行了深入探討。2003年我們經歷了非典時期,但國內的影視創作者似乎都不愿觸碰整個民族共同的創傷,有關疫情的影視作品只停留在“記錄”的層面。17年后的今天,當我們再一次受到自然的懲罰時,有必要對其進行反思。不同于《流感》《傳染病》等虛構的疫情電影,中國的抗疫片已經具備了非常完整、成熟的現實條件,對于疫情的發生、爆發、控制等階段,我們每一個人都深有感觸,因此,未來的中國疫情電影也必將擁有更多的可能性。雖然圍繞“疫情”來進行創作,但電影的類型可以是多元化的:災難片、科幻片、現實主義倫理片,等等。對于災難的呈現必定會用到最前沿的科技,“通過高解析度的影像將觀眾‘吸入到銀幕世界中,從而使觀眾能夠達到一種‘在場的臨場體驗模式”[ 3 ] 3。對災難的“沉浸式體驗”必定會喚起觀眾的感覺機制,從而加深其對災難的“觸感”。正如巴克所說,電影所帶來的是一種近密的體驗,觀者與電影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我們并非將電影看作純粹是視聽藝術的媒介載體,觀眾也絕不僅僅是電影“遠距離的觀察者”,兩者之間的親密感正是其彼此互相纏連的觸摸效應。5G時代的技術必然會使觀者與影像本身之間的“體觸”更加真實,除了景觀的呈現,在敘事上我們可以將小家庭的建構作為核心,將疫情前后家庭的分崩離析、疫情期間無法相見的現實阻礙、抗疫醫生的心理刻畫、困境得到解決后的家庭團聚等情節作為敘事的重要元素,重視對于疫情發生過程中的真實再現,而不是停留在傳統災難片對未來的構想層面上。此次疫情是一次全球性的災難,所以創作者不應將目光局限于本國,對于留學生群體的困境應作為國外部分的重點,同時穿插各國民眾在疫情面前的應對措施及心理重建,從而凸顯“后疫情時代”全人類共同的“反思”主題。中國的疫情電影要實現景觀美學、類型敘事、倫理建構三者的“縫合”,“在命運共同體中建構價值共同體和審美共同體,以價值共同體和審美共同體推動命運共同體的成長和壯大”[ 4 ] 8。
5G時代的到來突破了4G在影像呈現方面的壁壘,4G技術還主要停留在電影的宣傳、發行、放映等環節,5G不僅可以彌補其在傳播速率、傳輸穩定性等通信技術方面的缺憾,同時又可以直接作為一種影視制作技術,參與到影片的拍攝、制作等環節,完成對電影行業的全覆蓋。中國電影目前對于技術的應用還并不成熟,《流浪地球》《哪吒》等電影的成功又讓影人看到了市場對于技術的渴望,《姜子牙》雖褒貶不一,但其在畫面的呈現上卻完成了自己的“封神”之路,以中國傳統花紋圖案和山水元素為基礎,在IMAX和3D的加持下,形成了獨屬于中國的具有東方美學意蘊的視覺景觀。中國電影對于技術帶來的景觀敘事的追求無疑是5G時代的必然趨勢,但很多影片都表現出了對視覺感受的過度追求,其根本原因是缺乏對于現實的深度思考。盡管從概念來看,數字吸引力電影的確強調視覺景觀的建構,但影片中的敘事結構、價值觀念同樣可以成為將觀眾“粘在座位上”的重要因素。
二、具身性:從體驗到交互
技術的變革改變了觀眾的感知方式,“吸引力使觀者在心理和意識層面參與其中,并影響其行為。吸引力可以指‘個體觀者的參與,也可以指‘社會意識”[ 5 ] 7 0。電影的媒介特性決定了觀眾的參與具有一定的社會性,因為坐在影院的觀眾能感受到周圍的人與他正在體驗同一部電影,而對影片的解讀及評論也是其參與性的一部分。西蒙弗雷澤大學藝術與文化講座教授勞拉·馬科斯在《電影皮膚:跨文化電影、具身性和感覺機制》中,提出了“觸摸影像”“觸摸視覺”以及“觸摸感電影”的概念。她認為,我們獲取的很多知識不是經由視覺模式,而是經由身體接觸而來的。某些經驗更可能以非視聽性的觸摸感、嗅覺感和味覺感“記錄”下來。“具體到以視聽為重要元素的電影,即便視覺認知在電影經驗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影像所訴諸的也不僅僅是普通意義上的視覺,而是一種‘具身化視覺或‘觸摸視覺抑或是完整的感覺機制(初生嬰兒與外界的接觸首先是通過觸感而非視覺感),又與視覺感緊密結合,構成具身化視覺。”[ 1 ] 8 0“電影皮膚”凸顯的也是觀者與影像之間的一種“手手相觸”之感,技術的進步必定會使這種“觸感”變得更加真實。
5G時代的到來必將會給電影行業帶來一場技術革命,觀眾從此前的沉浸式參與到將來作為創作者的互動式體驗都可以利用5G帶來的新技術完成。同時“藝術家可以輕易地去操控、處理、改動數字化的影片;這種改動可以針對某一幀畫面或是整部影片。這種可操控性也為電影展示更廣闊的空間”。很多學者認為,技術的變革在拓寬電影表現空間及觀眾感知經驗的同時,也將逐漸失去再現現實的能力。列夫·曼諾維奇認為,人們對于現實的強烈追求推動了技術的變革。筆者認為,5G時代的數字技術不但可以深化影像的現實主義風格,同時將觀眾縫合進了技術與傳統相融合的影像中,強化了觀看的主體性。數字技術時代的美學觀念具有內在的自反性,不懼怕觀眾意識到影像內部空間的建構特征,其突出表現包括創作中的互文指涉、經典挪用,以及與流行文化和其他媒介之間不斷呈現的對話關系等等。
《頭號玩家》通過VR技術將游戲中的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相融合,全沉浸式體驗可以看作本片在電影技術方面的一大突破,該片方與HTC Vive又合作推出了八款線下VR體驗服務,觀眾可以體驗角色在影片中經歷的各種場景。“觀眾因撲面而來的生動性被主動邀請參與到影像中,未被忽視的觀眾使得VR電影成為了一種裸露癖”[6]47。影片中隱藏了100多個彩蛋供觀眾尋找,真正意義上實現了與場外觀眾的實時互動。觀眾由“被動體驗”轉化為“主動選擇”,通過尋找彩蛋獲得與影片主角相同的快感,完成了對影像世界的現實延伸,“電影由‘物質現實的復原轉化為‘心理現實的復原”[7]61。斯皮爾伯格通過將影片中的現實世界、游戲世界與觀眾所處的世界相融合,并采用游戲人物的第一視角,使觀眾獲得了劇中角色的真實體驗,影像中的人物通過游戲世界破解謎題,觀眾則在尋找彩蛋的任務中獲得一種替代性快感,由于視角與影像空間的不斷變化,觀眾可以隨意出入游戲世界,完成現實與虛擬的交互式體驗。正如麥克盧漢所說:“一切媒介均是人的感覺的延伸,我們的感覺器官和神經系統憑借各種媒介得以延伸。輪子是腳的延伸,文字是眼睛的延伸,電視是眼睛與耳朵共同的延伸,這是與器官相關聯的。”(2)
數字技術的不斷更新給觀眾帶來了更加真實的體驗感,在“可觸”的場景中作為參與者親歷影片中的場景,觀眾與影片的關系也不再停留在“體驗與展示”的層面上,兩者之間的中介越發趨于透明化,數字技術下的“混合現實”以其可“進入”性恰恰凸顯了身體與觸摸在形象立體層面的重要意義,觀眾的參與互動也不僅僅是發送實時彈幕,甚至可以根據自身喜好通過隨意選取某個場景或角色完成與影像本體的真正互動,同時可以作為創作者掌握故事的走向。勞拉·穆爾維認為觀眾同時作為觀者與參與者,可能找出影片各個場景之間的因果、文本、情感之間的斷裂及聯系,而這些可能是創作者容易忽視的。[8]166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使觀眾更加直接地參與到影片的創作中,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了編劇的權威,但他們也只是在創作者構建的完整敘事空間中完成自己的創作構想。
在倡導電影工業美學的大環境下,電影的真實性從攝影對現實的復刻轉向了技術所構建的效果的真實、情感的真實以及觸感真實的層面,觀眾的感知機制是數字吸引力電影真實感的主要來源。雖然數字時代的影像以建構的虛擬世界挑戰著以巴贊為代表的攝影影像本體論,但對于“真實”的追求仍然是數字影像時代對于觀眾最大的吸引力。
三、畫意影像;工業技術與傳統寫意的縫合
電影是藝術與技術結合的產物,近年來,《戰狼》系列、《紅海行動》《流浪地球》等影片的相繼成功,使“電影工業美學”“重工業美學”“電影技術研究”等相關話題成為電影研究領域的焦點。在5G技術日益成熟的今天,電影行業必將會面臨一次產業升級,關于技術的探索也會越發深入,數字吸引力電影也會面臨著隨之而來的挑戰。就國產影片而言,畫意影像是一種基于民族化和東方視覺經驗的電影風格,也是技術革新背景下國產影片的先鋒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