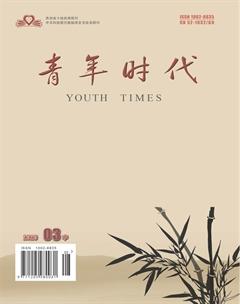我國食品安全問題的懲罰性賠償問題研究
許曉燕
摘 要:從1993年實施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首次制定懲罰性賠償制度算起,到2015年修改的《食品安全法法》增加了“價款的十倍和損失的三倍”的這樣具有懲罰色彩的法條,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我國已有20多年歷史。但是,相關法律條款的命運卻都是經歷了從制定之初的“歡聲鼓掌”到具體實施時的“沉寂落寞”。我國食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相關的立法還有很多不周全的地方。本文通過分析懲罰性賠償的適用主體以及功能,找出懲罰性賠償在適用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一些解決辦法,以期懲罰性賠償能最大程度上發揮其特有的作用。
關鍵詞:食品安全法;懲罰性賠償;作用
一、懲罰性賠償中“消費者”的認定
(一)對于“消費者”的概念的理解
關于“消費者”的概念,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食品安全法》都未作明確規定。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條規定:“消費者為生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本法未作規定的,受其他有關法律、法規的保護。”可見,目前我國只承認自然人作為消費者主體,不包括法人和其他組織。消費者,就是為消費生產購入和利用他人所供應的物資和勞務的人,是一種與供應者相對立的概念。《布萊克法律詞典》認為消費者就是指那些購買、使用、持有處理產品或服務的個人。1978年國際標準化組織消費者政策委員會在日內瓦召開的第一屆年會上,將“消費者”定義為使用、取得、定作、或者具有取得或定作商品的意圖以供個人生活的公民。
“消費者”的特征可以簡單概括為如下5點。一是消費的性質主要是指生活消費,精神消費除外。二是消費的客體主要指商品和服務,包括動產和不動產。但是,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問題是購買商品房是否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司法實踐中這類案件都是以合同糾紛的案由起訴到法院的,未出現過適用懲罰性賠償制度的情況。在這個問題上,何山教授和梁慧星教授各執一詞。何山教授素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之父”之稱,他認為應根據購買的物品屬性界定“消費者”。他認為只要購買的物品屬于生活消費品,不管購買的動機是什么,也不管購買后是否轉售,都屬于“消費者”。梁慧星教授認為應根據購買的目的界定“消費者”。他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目的必須是為了“生活消費”,而“知假買假”者卻是為了“索賠”,因此其不屬于“消費者”。三是消費方式方面: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必須是自己使用,而且是有償的。也就是說食品的購買者與食品的使用者須是同一個人。四是消費主體僅指個人,將法人、其他單位排除在外。五是對農業以及農業生產采取特別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62條規定,農民購買、使用直接用于農業生產的生產資料,參照本法執行,而且“農業生產的生產資料”主要應該是指種子、化肥、農藥。
(二)“知假買假”者能否作為消費者的爭議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通過的《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食品藥品規定》)第3條規定“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可知,“知假買假”者也應被認為是消費者。在司法實踐方面,2014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指導性案例,其中第23號“孫銀山案”,孫銀山去超市發起索賠,協商未果便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超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5586元,最終江寧區人民法院判決認可了孫銀山的訴訟請求。
2017年8月,杭州互聯網法院在官方微信公眾號上發布了其之前審理的“十大涉網糾紛集中管轄典型案例十則”,其中第一個案件便涉及到“知假買假”。秦喬系被告淘寶店主,劉艷系原告于2016年6月至7月多次在該店買日本奶粉,后劉艷以所購奶粉無中文標簽,無檢疫證明,即不符合國家食品安全標準為由,訴至法院,要求被告退一賠十,并主張淘寶平臺疏于審核應承擔連帶責任,最終法院判決駁回劉艷的訴訟請求①。此案件中法院審理認為,原告是資深購買奶粉者,理應對這些熟知,劉艷的行為屬于“知假買假”,并不是為了自身消費,而是在牟利,所以不是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保護的“消費者”。指出,就算依據《食品安全法》規定的“十倍賠償金”也不應保護以牟利為目的的“知假買假”的這種惡意購買的行為。
兩個案例同是食品、藥品類侵權案件,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判決。可見,“知假買假”行為的主體認定問題仍然處于有爭議的狀態,“知假買假”在實踐中能否獲賠依舊沒有定論。
二、懲罰性賠償制度存在的問題
我國《食品安全法》中的懲罰性賠償制度規定在第148條第2款,即生產或銷售明知是不符合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了要求賠償損失之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一千元的,為一千元。立法意圖是為了提高食品企業的違法成本,促使其合法經營,提升《食品安全法》對食品生產經營主體的威懾力,并維護消費者權益。但是,其也存在如下問題。
(一)忽略了食品企業的利潤規模
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價值就在于,通過讓商家支付高昂的賠償金,以起到懲罰的作用。現代機械化的企業為了實現利潤的最大化,普遍采用批量生產,那么,消費者如果按照《食品安全法》對缺陷產品主張賠償,只是對購買的那一小部分食品索賠,對于其他剩余的絕大部分食品卻沒有提起訴訟索賠,即便是法律規定的“十倍賠償金”,這相對于企業批量生產的食品獲得的利潤來說,卻只是不值一提。違法成本太低是目前我國消費行業存在問題的原因之一。企業根本感覺不到遭受的利益損失,也起不到“殺雞儆猴”的作用,這樣一來,懲罰性賠償便不能達到預期目的。
(二)消費者的舉證責任過重
根據《食品安全法》第148條的規定,生產者所承擔的責任是無過錯責任,即他只要生產了不符合標準的食品,就要承擔巨大的賠償金,這是不容懷疑的。而對于經營者來說,只承擔過錯責任,即明知食品不符合標準還要銷售的時候,才承擔懲罰性賠償。而我國在《食品安全法》中并沒有明文規定舉證責任倒置,也就是說采取的是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消費者主張賠償,消費者就要證明經營者“明知”的一個態度,但是,這對于本來就處于弱勢地位的消費者來說是難上加難。食品的價格是有限的,但是在訴訟中承擔過多的舉證責任,導致消費者付出的時間、精力和金錢的成本就過高,和最終獲得的賠償金以及或者敗訴的訴訟結果是不相對的。所以,這樣的舉證責任分配是不合理的。當消費者發現訴訟成本比獲得的賠償性收益更高時,就會放棄訴訟。這樣一來,也不能達到維權的目的,更不能對經營者起到遏制和震懾作用。
三、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完善
(一)提高食品安全的違法性成本
當消費者發現違法成本只有利潤的千分之一時,違法又算得了什么呢。“價款十倍或者損失三倍的賠償金”的計算方法過于僵化,缺乏靈活性,相對于特別重大的、惡劣的,又或是輕微的食品的侵權類案件缺乏個案上的公平公正。正如有學者說到:“作出這樣一種機械死板卻毫無回旋余地規定的最大好處在于替法官免去了思考的痛苦,最直接的壞處卻在于使賠償喪失了應有之義”。可以選擇設定一個有幅度的的計算方式,給法官留有一些自由裁量的空間。設定最高幅度和最低幅度,以免法官濫用職權;考慮消費者的實際損失,包括支付的食品價款、鑒定費、檢查費、訴訟費等;結合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明確損失的范圍;不可遺漏被告事后對消費者的補救措施和主觀態度。針對一些食品給消費者造成的身體的重大傷害和心理創傷的嚴重損害案件,把精神損害賠償納入考慮的范圍。
還要建立完備的信用體系,對于那些已經被判處賠償的食品商可以采取信息公開的方式,把他們的違法行為公之于眾;嚴重的,終生禁止進入食品領域活動。只有做到從各個方面加大食品商的違法成本,讓他們知難而退,才能遏制違法行為。
(二)減輕消費者的舉證責任
經營者負過錯責任,這卻加大了消費者的舉證難度。食品是很容易過期的,除非當場發現,否則舉證是非常困難的。如果經營者抗辯稱是消費者存放不周等原因造成的,消費者又該如何證明食品變質的原因不是由自己造成的呢?同時,“明知”應當做擴大解釋,就包括“知道”或者“應當知道”。《食品安全法》第96條規定,生產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此時,應當由經營者自己來證明履行了法律規定的的審查義務。如果將這個舉證責任分配給消費者,對經營者來說,無疑是“助紂為虐”。
筆者認為,經營者的責任,應當適用過錯推定責任,食品經營者只要存在了經營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的行為,就可以推定他主觀上有過錯,由經營者自己來證明自己履行了標準的審查義務以及其他的應盡的義務,如果不能證明,消費者就可以要求其承擔相應的懲罰性賠償責任。這樣一來,就能大大降低了消費者的舉證難度。
注釋:
①參見杭州互聯網法院,涉網糾紛集中管轄典型案例十則.微信公眾號,2017-08-25.
參考文獻:
[1][日]金澤良雄.經濟法概論[M].滿達人,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
[2]壬子.何山:"還我一個寧靜的公序良俗"——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有關問題訪談錄[J].中國律師,1998(3):35.
[3]梁慧星.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與適用[EB/OL].(2018-03-26)[2020-01-26].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583.html.
[4]最高人民法院.指導案例23號:孫銀山訴南京歐尚超市有限公司江寧店買賣合同糾紛案[EB/OL].(2014-01-29)[2020-01-26].http://www.court.gov.cn/shenpan-xiangqing-13326.html.
[5]張莉,曾國真.我國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研析[J].河北法學,2012(7):140.
[6]王貞,宋國棟.論食品安全責任懲罰性賠償制度[J].法制博覽,2017(25):76-78.
[7]李響.我國食品安全法“十倍賠償”規定之批判與完善[J].法商研究,2009(6):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