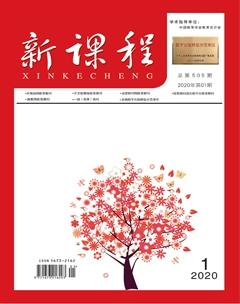結構化:小學說理文教學的應有策略
周雅婷
摘 要:結構化是指每一門學科都有其基本結構,每一門學科的教學都要讓學生掌握這一學科的基本結構。說理文教學應該從結構著眼,采用相應的結構化教學策略。目前,說理文教學出現的問題主要原因有三個方面:目標把握不夠精準;教材解讀不夠深入;學情分析不夠準確。因此,在小學說理文教學的時候要把握教材編排的結構化;把握所選事例的結構化。
關鍵詞:結構化;說理文;教學策略
一、小學說理文教學的四大罪狀及其根源
(一)小學說理文教學的四大罪狀
說理文,隸屬于議論文的一個分支,顧名思義,是講明一個道理的一種文體形式。大致的文路是擺出一個觀點、舉事實進行論證,最終得出一個結論。
在蘇教版國標本小學語文課本中,說理文所占比例不高,但是跨越了第二、三學段——第七冊15課《說勤奮》、第九冊22課《滴水穿石的啟示》、第十冊20課《談禮貌》、第十一冊23課《學與問》、第十二冊14課《學會合作》。正因如此,說理文教學普遍存在以下幾大缺陷:
1.咬文嚼字——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很多教師在教學中將說理文同其他課文同樣處理,將重點放在了語言文字的品味上。這是沒有必要的。因為說理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說清一個道理,一定會運用淺顯易懂的語言來講述。對這一類文體來說,品讀一詞一句,猶如身處森林之中,卻只能看見一棵樹,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2.思想教育——只見道理不見語文
既然說理文是為了說清一個道理的,那么教學重點就應放在道理的理解與教育上。課堂上,很多教師就是這樣做的,即使他們知道這樣是不合適的,知道這不是語文教學的主要任務,但是經常會不自覺地走上這條道路。這就讓語文課說理文的教學變成了思品課的思想教育課。
3.照單貼簽——只見外殼不見內涵
說理文的基本結構是提出觀點—舉例論證—得出結論。這一點,所有語文教師都知道。所以在教學中,把說理文各個部分就照著這個基本結構一一貼上標簽。可問題在于,雖然每篇說理文的結構都是相似的,但是,說理文各個部分之間是有內在的邏輯關聯的,不論是語言的外在形式還是表達的深層內涵,都是有一定規律的,這一點,很多教師因沒有深入解讀教材根本沒發現。
4.忽視學情——只見教案不見學生
這一點猶為常見。蘇教版國標本課文中,說理文跨越了二、三學段,很多教師往往用著四年級的教法,教著六年級的學生。在他們看來,說理文不論在四年級還是在六年級,差別不大,都是在擺事實講道理,所以教法也無需變動。所以,我們經常看到,四年級的說理文教學與六年級的教學,課堂區分度不明顯。這一做法不適應學生語言發展需要,也不適合學生語言能力發展需要。
(二)原因分析
上文列舉了目前小學說理文教學普遍存在的四大缺陷,這些缺陷的出現,根本原因在哪里?依筆者多年一線教學經驗與觀察研究,覺得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1.目標把握不夠精準
很多教師認為,說理文教學的主要目標,就是讓學生明白課文講的道理。明白道理應該是語文課應有的主要教學目標嗎?有哪一篇說理文的道理不是淺顯的?難道還需要用一節課時間來理解嗎?所以,一旦教學目標把握不準,教學很容易走樣。
2.教材解讀不夠深入
很多老師覺得,說理文只有“提出觀點—舉例論證—得出結論”三個部分,備課時,我先找準三個部分在哪,解決“提出什么觀點?舉了哪些事例?最終告訴我們什么道理?”三個問題就夠了。這樣的教材解讀是遠遠不夠的。正因為老師這樣的經驗主義做法,導致教材解讀不深入,所以教學中抓不住語文的要素,摸不清文本的內涵,不能提高學生的能力。
3.學情分析不夠準確
二、三學段學生的語文能力發展要求是大不相同的,學生語文能力的需求也是大不相同的。所以不同學段的說理文教學是大不相同的。從學生語言發展規律來看,說理文教學從低段到高段應該呈現逐漸深入、逐步推進的邏輯上升狀態。在分析學情時,老師最起碼應該思考以下幾個問題:學生之前學過沒有?學生已經學會了什么?學生還不會什么?哪些是我這節課應該教學的?哪些是我以后應該教學的?基于以上問題的學情分析,才能夠讓我們的課堂保持循序漸進的狀態。
二、什么是結構化
結構化教學理論,是美國心理學家布魯納(Jerome Seymour
Bruner)在結構主義教育理論及皮亞杰結構主義心理學的基礎上提出的教學理論。這一理論的主要觀點是每一門學科都有其基本結構,每一門學科的教學都要讓學生掌握這一學科的基本結構。
依據這一理論的基本原理,從語文教學角度來看,宏觀上說,語文學科也有語文的基本結構;微觀來看,每一種文學體裁都有它們的基本結構。說理文這一文體的基本結構就是“提出觀點—舉例論證—得出結論”。教學中,我們需要讓學生掌握這一文體的基本結構,所以說理文教學應該從結構著眼,采用相應的結構化教學策略。
三、結構化:小學說理文教學的應有策略
為避免走進說理文教學的誤區,在充分關注文本語文要素、深入解讀教材、準確把握學情的基礎上,說理文教學可以從其結構入手,展開如下教學。
(一)把握教材編排的結構化
說理文安排在小學第二、三學段,教材的編排是有道理的。說理文從四年級開始出現,這時期的學生習作能力處于低級發展區,所以這一學段說理文的教學,只需要讓學生了解文本的基本結構“提出觀點—舉例論證—得出結論”,明白文章講了一個什么道理。從教材編排的結構來看,這一階段屬于“認識說理文”階段。
縱觀教材的編排,說理文雖然不多,但是第三學段幾乎每冊課本都有,可以揣測編者的意圖是,到第三學段,五、六年級的孩子有一定的習作表達能力,有一定的閱讀積累。并且,說理文教學是中學議論文教學的基礎入門。所以第三學段,老師應該重點引導學生做到由“會學說理文”到“學寫說理文”。
從“認識說理文”,到“會學說理文”,最后“學寫說理文”,這樣的編排是具體邏輯結構化的做法。
(二)把握所選事例的結構化
“提出觀點—舉例論證—得出結論”是文體特有的邏輯結構,老師都能夠準確把握。可是,文體特有的結構遠不止于此,并且是很多老師沒有準確把握好的。
從篇幅上看,說理文的重點是“舉例論證”。說理文教學的誤區,很大部分問題就出現在這一環節。舉例論證簡單說就是“擺事實講道理”,選取特定的事例,對道理進行闡述。所選事例的結構化教學,是很多老師沒有把握好的。
1.事例選取的典型性
說理文選取的事例都是具有典型性的代表事例。例如《說勤奮》一文選取了司馬光做“警枕”勤奮讀書和童第周發奮學習的事例。
這兩個事例典型在哪里?司馬光從小就是個聰明的孩子,所以他長大以后成就卓著應該是順理成章的。可是,即使像司馬光這么聰明的孩子,想要成功,也是離不開勤奮的。而童第周,從小資質一般,完全是依靠勤奮成功的。這兩個事例典型在于,聰明人成功需要勤奮,笨人成功也需要勤奮,總而言之,所有人想要成功,必須勤奮。這就是本課的結論。
2.事例安排的邏輯性
說理文往往選取二到三個典型事例,對觀點加以證明。這些事例的排列順序是隨意的嗎?
以蘇教版國標本第十冊20課《談禮貌》為例。課文依次選取了岳飛、女青年和周總理三個事例。三個事例可以換一換順序嗎?筆者在一次公開教學展示時,有學生提出可以調整順序為“岳飛、周總理、女青年”。這就說明,學生并不明白說理文事例排列的原則——邏輯性。
最初接觸說理文,教師沒有必要讓學生理解什么叫邏輯性,更不需要讓學生掌握選取事例的邏輯性原則。可是到了五年級、六年級,在教學中有必要讓學生了解說理文事例的排列是有順序的,這個順序叫邏輯性。從《談禮貌》一課來看,岳飛、女青年和周總理三個事例的邏輯性在哪里?岳飛的事例告訴我們,有求于人,你必須要有禮貌;女青年的事例告訴我們,你犯了錯傷害了別人,你必須有禮貌,這是增進理解、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有求于人自然要有禮貌,傷害別人應該有禮貌,而周總理的事例告訴我們,即使被別人傷害,也應該有禮貌,這不光是增進理解、化解矛盾的基礎,更能體現個人思想情操和文化修養。這三個事例通過三種不同情況下禮貌用語的具體作用,是由淺入深的——無禮討人嫌、增進理解化解矛盾、體現個人修養。這就是這三個事例的順序,也是文本說明禮貌重要性的邏輯性。
3.事例講述的概括性
說理文的要點在于說理,所以所選事例的故事性、趣味性等要求不高,最好是簡明扼要直指道理。
以蘇教版第十一冊23課《學與問》為例。文中舉了沈括讀《大林寺桃花》的事例。課文中這一段事例,加上標點一共198個字;而這個故事的原文,共計545字。對于六年級的學生來說,不光要會讀這個事例,明白事例所要提示的道理,更應該學著選取事例試著寫說理文。所以教學中,第一步,教師要引導學生對比思辨,課文事例與原文哪一個更好?第二步,課文為什么要簡單講述?答案自然是課文比較好,課文的寫作目的是為了講道理,而不是為了講生動的故事,所以事例只要概括性地講述。在明白這兩點以后,課文與原文對比找一找,課文刪減了哪些語句?找出這些語句的共同點,也就找到了概括性講述的方法,學會了寫說理文事例的竅門。
4.選取事例的針對性
有些教師在說理文教學中,會讓學生為課文增補一到兩個事例。這一教學環節設計的目的是檢驗學生對事例典型性、邏輯性和概括性的掌握情況。或者教師給出一個觀點,讓學生選取事例對這個觀點進行論證,最終得出道理。
這一教學方法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卻很容易在事例選取的針對性上出現問題。
同樣以《談禮貌》一課為例。在教學中,我設計了兩個活動:(1)為課文增加一個事例;(2)從老師提供的事例中選取幾個,論證“誠實守信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這一觀點。
五年級的學生,學過兩篇說理文以后,大體了解說理文選取事例要選取名人故事,這叫典型性;事例最好覆蓋古今中外,這是道理的普遍適用性,更具說服力;事例要按一定的順序排列。很多學生為《談禮貌》一文增補了外國名人故事,因為這是課文缺少的;在論證“誠實守信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這一觀點時,同樣選取了古今中外名人事例按時間順序排列。
問題出在哪里?事例不具有針對性。《談禮貌》一文開頭提出的觀點是“禮貌待人,使用禮貌語言,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我們能選取外國人的事例來論證“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嗎?事例選取,必須針對文章的中心,針對說理文的中心論點來選,這就是說理文事例的針對性。
把握說理文的整體結構、把握說理文事例安排的結構與原則,以這些結構為教學的要點,將說理文教學目標定在發展學生思、辯、寫等語言文字的運用上,這才是說理文教學的應有視點,是說理文教學走出教學誤區的應有策略。
參考文獻:
[1]李曉麗.布魯納學習理論及其對教學工作的啟示[J].教育探索,2015(11).
[2]肖少北.布魯納的認知:發現學習理論與教學改革[J].外國中小學教育,2001(5).
[3]鄭旭東,陳榮,歐陽晨晨.皮亞杰與布魯納的和而不同與整合發展:兼論教育技術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三重縱深[J].現代遠程教育研究,2017(5):2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