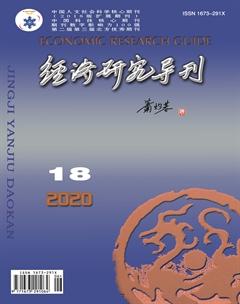鄉村振興與縣域鄉村空間發展規劃
郭佳君 李茜
摘 要:鄉村振興是一個系統工程,在推動鄉村振興發展過程中,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縣域鄉村空間規劃是優化鄉村空間開發格局的重要手段,是調控和引導資源配置、集約利用的空間政策工具。為有效地解決鄉村振興發展過程中的不平衡性問題,應圍繞產業發展、生態修復、管控治理驅動力,有效地實施縣域鄉村空間規劃,形成系統、有序空間格局,推動鄉村振興發展。
關鍵詞:鄉村振興;縣域;鄉村空間;發展規劃;發展策略
中圖分類號:F323? ?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0)18-0035-04
引言
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面臨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在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背景下,人們在各方面的需求快速增長,城鄉發展水平的差距明顯,造成了諸多不平衡的現象。隨著城鎮化建設引領著越來越多的政策和資源走向農村,為如何在有限的空間區域充分利用資源達到推動農村發展、減小不平衡差距成為研究熱點。2019年5月,自然資源部發文:“建立全國統一、責權清晰、科學高效的國土空間規劃體系,整體謀劃新時代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綜合考慮人口分布、經濟布局、國土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等因素,科學布局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扎實推進鄉村建設,塑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新格局,加快補齊農村人居環境與公共服務短板是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鄉村空間規劃整體上反映著鄉村地區的經濟、社會、環境水平,展示著其資源配置及利用的程度,更涵蓋著生產、生態、生活三大領域。縣域鄉村空間規劃是實施國土空間規劃項目中承上啟下的重要銜接部分,既要貫徹落實上級部門下達的規劃編制要求,又要向下級鄉鎮傳達并引導具體的規劃路徑安排。根據縣域的不同識別特征,研究其內在的發展訴求,結合相關因素考慮,以主要驅動力為主導形成一套合理的規劃方案對于縣域鄉村空間布局的構造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劉紀遠、張增祥等(2009)認為,國家宏觀政策、區域發展政策及社會經濟發展是21世紀初期土地利用變化的主導驅動因素[1];郭曉東、馬利邦、張啟媛(2012)利用GIS空間分析方法,對在基本生活需求與改善生活條件的內在驅動力、基本價值觀、市場參與能力,以及政策制度的約束力和驅動力等多種因素的對鄉村聚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研究[2];王竹、沈昊(2016)以景觀變化為驅動力,做出鄉村的空間規劃探究[3];朱紀廣、李小建等(2017)分析以交通、特色產業、政府機制為向導的空間形成機制[4];薛東前、陳恪、賈金慧(2019)將地勢、河流、道路、人口、經濟、工業化與城鎮化、政策調控等作為空間規劃的驅動因素[5];楊歡、何浪(2019)基于“驅動力—狀態—響應”的理念,對鄉村空間進行劃分,提出具有適宜性的空間整合模式[6]。
本文以產業發展、生態修復、管控治理為三大初始驅動因素,結合縣域鄉村不同發展,為有效地實施縣域鄉村空間規劃,形成系統、有序空間格局,推動鄉村振興發展提供一定依據。
一、鄉村振興與驅動力為主導的縣域鄉村發展規劃
鄉村區域的發展有很多重要的組成或推動要素,這些要素在空間發展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是不相同的,某個更具活力的要素一定會影響或推動其他要素的存在,這種最活躍的要素就是鄉村區域的主導驅動力。鄉村社會是一個由比較封閉的發展模式到比較開放的城鄉統籌謀劃模式轉變過程。鄉村振興需要有效地解決相應不平衡性問題,諸如鄉村空心化及老齡化、勞動力嚴重不足、生態環境惡化、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等等。以驅動力為主導的鄉村規劃,成為解決不衡性問題的切入點。
第一,產業發展驅動力。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和經濟基礎是產業興旺,以優化產業結構、發揮各生產要素之間協同作用為導向,促進產業融合發展、轉型升級,增加產品附加值,開拓產業多功能性。不同的產業結構意味著鄉村區域土地利用方式不同,具有差異性的土地利用方式意味著不同的生產效益。因此,產業發展對于鄉村區域格局優化具有直接顯著影響,產業發展成為縣域鄉村空間規劃的主要驅動因素之一。產業發展充分挖掘鄉村產業特色,依據鄉村產業空間格局打造集復合化與景觀化為一體的發展模式,驅動促進空間經濟效率提升。
第二,生態修復驅動力。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任務是生態宜居,聚焦生態恢復、保護優先的理念,統籌山水林田湖草協同化治理,因地制宜地打造綠色空間區域。生態修復投入的多少決定著區域環境的改善和生態效益的提升,對生態修復的重視程度對鄉村地區不平衡發展具有正向驅動作用,分析重點生態功能區退耕還林還草等修復性工程、權衡保護與發展造成的人地矛盾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核心所在,以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因此,生態修復對于鄉村區域格局優化具有直接顯著影響,生態修復成為縣域鄉村空間規劃的主要驅動因素之一。生態修復發展充分挖掘鄉村資源,依據鄉村生態空間格局打造保護與發展為一體的發展模式,驅動促進空間生態效率提升。
第三,管控治理驅動力。實現鄉村振興必須發展和完善鄉村治理體系,政府出臺相應的政策體系嚴格實行用途管制,堅守用地原則,加強土地監管,逐步完善各項規劃機制,提升土地利用效率。貫徹落實鄉村振興戰略一定要以“以人為本”的思想,關注鄉村社會的發展水平提升與鄉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避免制度與實際脫離的現象。為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夯實各部門組織在鄉村治理中的核心領導作用,管控治理驅動的縣域空間規劃以法治為本,深入推動著鄉村內部發展不平衡的局面扭轉。因此,管控治理對于鄉村區域格局優化具有直接顯著影響,管控治理成為縣域鄉村空間規劃的主要驅動因素之一。管控治理發展充分依據鄉村社會空間格局打造制度與發展為一體的發展模式,驅動促進空間社會效率提升。
以產業發展驅動力、生態修復驅動力和管控治理驅動力的鄉村空間規劃,驅動促進鄉村空間經濟效率、生態效率和社會效率的提升,是緩解不平衡壓力,打造高質量鄉村建設的主要動力。
二、驅動縣域鄉村空間發展的內容
以驅動力為主導的縣域鄉村發展規劃驅動促進鄉村空間經濟效率、生態效率和社會效率的提升。
(一)產業發展驅動提升鄉村空間經濟效率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貫徹實施,許多鄉村地區為了促進產業興旺、解決空心化和老齡化的問題,著重關注產業的發展。
1.產業類型發展。以產業為主導驅動力的縣域鄉村空間通常可以分為以第一產業為主的傳統農業型、以一二產業為主的農工混合型以及一二三產融合發展型。重慶市榮昌區以鄉村產業為主導驅動力,根據鄉村地類結構,對鄉村產業分區,劃分鄉村產業類型[7],將產業類型分為傳統農業型、現代農業型、農工混合型以及非農主導型。傳統農業型地區以傳統的農業種植業為主導,具有生產條件落后、交通條件差、地質災害頻發的特征;現代農業型地區作為重慶市重要的糧油生產區,具有鄉村土壤肥沃、耕地分布比較集中、生產條件優越的特征;農工混合型鄉村則坐落著一些高污染、高耗能企業,其種植業與工業并重發展,從而帶動著經濟水平的提升;非農主導型鄉村以工業和旅游服務業為主導產業,其人口密度較大,土地利用強度較高,是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點建設區域。
2.轉型發展。江蘇省無錫市將鄉村產業視為主導驅動力,根據地域特色,鄉村形成新型農業推動下的環境優化型、工業升級引導下的分離與集中型和三產發展促進的特色塑造型三種具備產業特色的鄉村空間轉型模式[8]。
(二)生態修復驅動提升鄉村空間生態效率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貫徹實施,許多鄉村地區面臨著保護與發展關系矛盾的問題,尤其是許多生態敏感的欠發達地區。
1.山地和河谷平壩生態修復發展。云南省滇西地區90%以上都是山地,河谷平壩不到5%,適宜城鎮發展和耕種的地區都集中在河谷平壩[9],城鎮建設占用大量農田,致使空間資源要素配置比例失衡。山地和河谷平壩生態修復成為云南省滇西地區鄉村振興的重點內容。
2.旱塬生態修復發展。渭北鄉村旱塬區位于渭河平原和陜北黃土丘陵溝壑區之間,防范自然災害的能力較弱,面臨著水土流失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結合坡度、坡向、高程、河流、規模、道路等多種空間因素考慮,旱塬生態修復成為渭北鄉村振興的重點內容。
(三)管控治理提升鄉村空間社會效率
實施管控治理的職責邊界明晰,涉及到各部門權力與利益影響的耕地、濕地、林地、園地、荒地等地之間規劃使用的管控,避免交叉沖突。
三、驅動縣域鄉村空間發展策略
縣域鄉村空間發展規劃引導并控制鄉村空間發展向良性方向逐漸轉變,使鄉村空間加快新陳代謝速率,實現可持續發展。
(一)“三生三產”復合
鄉村生產空間中的耕作方式比較粗放,土地細碎化現象較多,進一步導致耕地拋荒的現象也時有發生。農民在生活空間里常常會產生人地矛盾,人居環境被各種垃圾污染的現象也屢見不鮮,存在著許多住宅分布散亂、用地效率差的問題。在鄉村生態空間中,由于村民對環境問題的輕視與工業制造的排放造成土壤污染、水源污染、大氣污染的問題日漸嚴重。由此看來,縣域必須明晰空間規劃的必要性與空間重構的重要性。
以產業為主導驅動力的縣域鄉村空間發展特色農業,同時擴展第二三產業,集生產、加工、制造、采摘、銷售、參觀等一體化,推進“生產—生活—生態”復合空間的整合建設。安徽省合肥市鳳橋社區以發展生態農業為中心建立了多家大規模的農業產業園。農業生態園主要以特色種養業為主,部分為傳統農業,拓展發展休閑農業,將生態農業景觀化[10]。在各項規劃發展政策的驅動下,復墾宅基地,將分散的農戶集中搬遷至設施比較齊全的村民中心,由此便可實現勞動力聚集,為打造集中化、高效率的產業基地提供便利。在生活空間方面,鄉村社區能夠實施統一管理,完善學校、醫院、農貿市場等基礎服務設施。村民垃圾可實行統一處理,避免垃圾被亂丟至多處對村容村貌造成不利影響。該地區通過產居一體化將生產、生活、生態空間進行重組,將初始以產業為驅動的空間規劃為“三生三產”聯合發展的復合性空間。
在鄉村振興發展中,傳統農業型空間區域應當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篩選出不宜耕作的土地退耕還林,促進土地經營權的流轉,優化種植結構,以綠色產業代替傳統農業種植方式,孕育特色農業,對初級農產品加工,在做好第一產業的基礎上適當發展第二與第三產業;現代農業型空間區域要進一步提高基本農田建設標準,培育高質量、高附加值的農業產品;農工混合型空間區域應當重視周邊生態環境惡化問題,提倡發展生態農業,保證該空間的可持續發展能夠順利推進;非農主導型空間區域的目標則是充分利用城鎮邊緣地區的農業景觀,進一步完善農業園區的建設,加大觀光旅游業的宣傳力度。
(二)移民搬遷、土地整治以及產業重構
鄉村生態系統和其他的非純自然的生態系統一樣,由人工和自然要素共同組成,它們之間相互干擾、相互融合形成一種多結構、多層次、多功能、多形態的復合人工生態系統[11]。良好的生態環境是人類社會與經濟發展壯大的基石,鄉村的生態空間是生產和生活空間的基礎,生產和生活空間又影響著生態空間的運作。鄉村的基礎環保設施缺乏建設與完善,生產廢棄物和生活垃圾隨意亂丟以及不正確處理的現象頻頻發生,對鄉村的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大的污染與破壞。鄉村的生產、生活、生態空間時常處于失衡狀態,尤其表現在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方面,直接降低農業生產效益。
鄉村生態環境脆弱不堪的零星居民點空間規劃應以生態移民為起點,組織發動相關部門對分散的零星居民點進行搬遷引導,使分散的小農戶向地勢較低且相對平坦的區域合并遷移,興修農田水利設施。此舉措不僅可以很好地保護水源涵養區和生態保護區,還有利于之后的生態功能的修復工程。保留居民點空間區域重點放在土地的集約利用上,開發土地綜合整治技術,進行適當的土地整治。廢棄或閑置的宅基地,避免一戶多宅與土地資源的浪費的現象,將土地盤活利用,改善土地用途,推動該空間區域經濟水平的增長。作為具有良好區位優勢的中心居民點的空間,完善道路交通設施,加強產業連通性,積極拓展特色農業與鄉村旅游業,把山、水、林、田、湖的生態景觀注入到產業中,充分激發鄉鎮村莊之間各要素的流動,利用其連接城鄉的樞紐效應,推進城鄉共同發展。
鄉村地形地勢、土壤質量、河流道路分布都是影響縣域空間規劃布局的客觀條件,應將其劃入鄉村空間重構的重要因素中。土地整治是鄉村空間重構過程中的強硬基石,為了避免鄉村聚落空心化現象的加重以及構建出生產有序、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縣域鄉村空間,將土地整治與產業重構列為進一步優化新渠道,實現真正的空間可持續發展。重慶市石坪村土地整治逐漸邁向綜合化、生態化模式,土地利用由傳統粗放耕種向規模化、精細化種植轉變,產業結構由單一種植向一二三產業鏈閉環延伸,實現了土地整治—產業轉型—鄉村重構的無縫接合[12]。通過空間規劃體系的建立,重慶市石坪村產業發展集采摘觀摩、趣味體驗、度假休閑于一體化,吸引著外來投資,為村民謀幸福。
(三)多規合一,信息聯動
縣域鄉村空間規劃中各部門方案策略不一、上下層級管制不銜接的問題,要想實現空間規劃的一張藍圖,必須深入貫徹落實“多規合一”的政策,避免各部門層級之間管控不統一導致的相互沖突。運用國家整體策略引導縣域空間規劃格局優化,是縣級政府科學合理地對空間格局進行優化的必要手段。
1.以國家政策為統領,各部門層級之間形成統一的目標并達成共識。各部門層級之間相互溝通建立兼顧多方利益的協調機制與統一管理平臺,通過制定規劃目標、發展定位、實施戰略等重大事項構建規劃框架,進而形成各資源要素合理配置的優化布局。同時,推進“多規合一”改革應明確推進改革的“減量規劃”思維,樹立“紅線意識”[13],根據不同尺度與層級空間規劃的相關管控要求分級落實,并保持各個規劃的用地標準、生態紅線與城鎮邊界等相統一。在建立總體指導思想的基礎上,以管控治理為驅動的縣域空間規劃需形成用途管制體系,其管制要素由單一走向保護農業用地、發展建設用地、開發閑置土地的多元化方向轉變,輔以配套政策加強“農地、農有、農用”的管制,有序地推進限于國土空間的集約高效發展。
2.機械地生搬硬套一些規劃策略,很可能導致“千城一面”的現象,沒有針對性的實施方案會喪失鄉村原本的特色。自然在鄉村規劃中擔任著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鄉村的空間規劃要從實際出發,把鄉村與自然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按照其本身的發展規律,探索出一條適合自身的規劃方案,因地制宜,生產活動順應自然,生態環境尊重自然。為了推進縣域空間規劃的開展,合理地進行資源配置,使得規劃方案具有針對性與可行性,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和空間開發適宜性評價作為重要標準,要嚴格按照國土空間規劃的總體規劃、詳細規劃、專項規劃的要求,分類指引,加強空間規劃的頂層設計。同時,應建立“多規合一”的指標數據庫,把城鄉建設、土地資源、道路交通、環境保護等空間要素疊加至一起,建成全縣統一的信息聯動平臺,進行差異化管控的同時實施精細化管理,科學地統籌農業、生態和城鎮功能空間。
參考文獻:
[1]? 劉紀遠,張增祥,徐新良,匡文慧,周萬村,張樹文,李仁東,顏長珍,于東升,吳世新,江南.21世紀初中國土地利用變化的空間格局與驅動力分析[J].地理學報,2009,(12):1411-1420.
[2]? 郭曉東,馬利邦,張啟媛.基于GIS的秦安縣鄉村聚落空間演變特征及其驅動機制研究[J].經濟地理,2012,(7):56-62.
[3]? 王竹,沈昊.基于景觀變化驅動力的鄉村空間規劃策略研究——以浙江莫干山鎮勞嶺村規劃設計研究與實踐為例[J].西部人居環境學刊,2016,(2):6-10.
[4]? 朱紀廣,李小建,王德,牛寧,楊慧敏.傳統農區城鄉體系空間結構演變及其形成機制研究——以河南省周口市為例[J].人文地理,2019,(4):126-134.
[5]? 薛東前,陳恪,賈金慧.渭北旱塬鄉村聚落演化的影響因素與空間重構——以黃陵縣為例[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9,(4):22-30.
[6]? 楊歡,何浪.基于“驅動力—狀態—響應”的鄉村聚落類型劃分及空間整合模式研究——以咸陽市為例[J].小城鎮建設,2019,(8):11-18.
[7]? 魏耀華,陳榮蓉,楊朝現,信桂新.丘陵區村域鄉村性空間分異及發展類型研究——以重慶市榮昌區為例[J].地域研究與開發,2019,(3):170-175.
[8]? 陶岸君,王興平.市縣空間規劃“多規合一”中的國土空間功能分區實踐研究——以江蘇省如東縣為例[J].現代城市研究,2016,(9):17-25.
[9]? 李瑞強.滇西地區市縣空間規劃的探索與實踐——以大理州永平縣“多規合一”為例[J].城鄉規劃,2018,(6):98-106.
[10]? 儲文娟,李俊峰.土地流轉背景下鄉村空間轉型及效益研究——以合肥市鳳橋社區為例[J].安徽農業科學,2019,(11):249-252.
[11]? 余侃華,祁姍,龔健.基于生態適應性的鄉村產業振興及空間規劃協同路徑探新[J].生態經濟,2019,(3):224-229.
[12]? 閆建,姜申未,熊想想.基于產業發展與土地整治聯動的鄉村空間重構研究——以重慶市石坪村為例[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9):79-89.
[13]? 張克.市縣“多規合一”演進:自規劃體系與治理能力觀察[J].改革,2017,(2):68-76.
[責任編輯 文 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