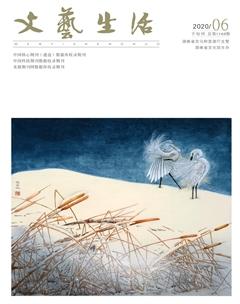呂祖謙學派的學術傳承與發展初探
李贊
摘要:由于呂祖謙早逝,呂學的傳播遭受重創。但呂學的傳承并未中斷,從南宋至明初,形成了呂學四代學術傳承體系,第一代以呂祖儉為中心,第二代以北山四先生和王應麟為呂學大宗,第三代以柳貫、黃潘等婺州群儒為代表,第四代以宋濂、王袆為盟主的呂學續傳。在四代傳承者中,始終貫徹著經史并重、經世致用的呂學風格。
關鍵詞:呂祖謙;呂學;傳承發展
中圖分類號:B2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20)18-0017-02
一、前言
南宋時,呂祖謙學說與朱熹、陸九淵之學鼎足三分,風靡天下。呂祖謙弟子眾多,早在乾道三年(1167年),呂祖謙服母喪守墓武義明招山期間,附近學者慕名前米問學不在少數。乾道四年(1168年)秋,呂祖謙從武義明招山回到金華曹家巷的麗澤堂,并于這年冬天在麗澤堂授業講學,且制訂了第一個麗澤規約,四方學者更是爭相趨之,“一時人傾心向往”。僅查《宋元學案》中的《東萊學案》與《麗澤諸儒學案》,呂祖謙的嫡傳有近百人之多。
然而呂祖謙不幸英年早逝,呂學頓失核心領袖,許多呂門弟子或歸于朱學,或趨向陸學,呂學已不復呂祖謙生前盛況。然呂學的傳承并未消歇,尤其是呂祖謙傳學重鎮一婺州,“被東萊之教尤深,至今名士班班,其傳蓋未艾也。”又經南宋至明初四代傳承者的前后相接,逐漸構成了以婺學這一以地望為紐帶聯結的學者名儒集團,且傳承達數百年之久,為婺州贏得了“小鄒魯”的美譽。
二、呂祖謙逝世:以呂祖儉為中心的第一代傳承
淳熙八年(1181年),呂祖謙因病逝世,麗澤諸儒痛失導師。此時,東萊胞弟呂祖儉,毅然獨肩大任,繼續傳承呂祖謙學說,形成了為呂祖儉為中心的呂學第一代傳人。
呂祖儉(?-1200年),字子約,號大愚,從小受業于父親呂大器和兄長呂祖謙,故得父兄中原文獻之傳。呂祖謙在世時,呂祖儉曾協助乃兄創辦麗澤書堂,常代呂祖謙給眾弟子講學。東萊逝世后,呂祖儉一方面繼續與朱、陸、永嘉之學相互往復論辯,另一方面又與麗澤諸儒共同傳播東萊學說而不遺余力,成為繼東萊之后講述呂學的中心人物。關于這一點,呂門弟子喬行簡日:“祖謙死,凡諸生皆承事祖儉,呂氏之學益明。”呂學再傳王柏也說:“麗澤輟響,而大愚先生實嗣其音,故于同門朋友,拳拳篤敘若家人。”在以呂祖儉為中心的麗澤弟子主導下,婺州一地,呂學繼續廣泛流傳,“有若李正節、侯茂欽、監察御史喬公世用、通判眉州趙公周錫,皆成公之高第弟子,或以忠義顯,或以政事稱,或以文學著,傳之當世,布之簡書,相去一百余載,人尤象而法之。嗚呼,何其盛也!”
三、宋末元初:以北山四先生和王應麟為“呂學大宗”的第二代傳承
朱熹雖生前常到婺州講學,接引弟子眾多,但真正“得朱子之學髓”,能代表金華朱學的首推由朱熹高足黃干傳下的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前承后繼,史稱“北山四先生”。由四先生開創的北山學派被視為朱學嫡脈,在元朝時成為官學,在婺州及全國廣泛傳播,影響深遠。然細察北山學派的學術淵源,其與呂學有著較深關系。金華為呂祖謙傳道的核心地域,作為鄉后學的北山四先生,在師友淵源和鄉里聲氣的推動下,且王柏、金履祥、許謙三人又常講學于研究與傳承呂學的中心——麗澤書院,因而與呂學關系密切。
北山四先生雖一生不仕,堅辭朝廷以及地方官的征辟,但為學并不空談心性,而是積極關注國事,致力于學術的經世致用。何基雖終日研究朱熹之學,至老不衰,但不廢經史制度之學,且對現實政事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北山(何基)雖居山林,而憂國之切,故有廟堂議和、子文(王埜)除擢之問,則其厚于君臣之義,又何如哉?”而王柏更是積極關注現實政治社會問題。南宋后期國家衰頹,局勢每況日下,王柏為此痛心疾首,并痛陳時弊,希望統治者能除弊革新。他曾指斥科舉“一次于三日之虛文”,無以治理天下,主張恢復古時的考選制,又認為國貧民病,是吏治腐敗“勢家巨室”不輸王賦的結果,并提出“富國強兵,必以理財為本”,強調“理財無巧法,止得輸其所當輸者足矣。但輸其所當輸,當自公卿大夫始”的解決辦法。
四、元代以柳貫、黃溍、吳師道為首的婺州群儒的第三代傳承
北山四先生以降,呂學在婺州地區有了更為繁榮的發展,這些呂學弟子在當時代表并引
領著時代的學術思潮。《宋元學案》也曾云:東萊學派,二支最盛:一白徐文清(僑)再傳而至黃文獻(溍)、王忠文(袆);一白王文憲(柏)再傳而至柳文肅(貫)、宋文憲(濂),皆兼朱學,為有明開一代學緒之盛。”元代呂學的杰出代表即是分別在兩支東萊學派續傳中承上啟下的柳貫與黃溍。
當年呂祖謙眾多弟子,在元代也有諸多后人不墜家學,研習呂氏學說,因而也成為元代呂學的重要傳承者。如東陽人李裕(1294-1338年),高祖李大同從呂祖謙游,伯高祖李大有私淑呂祖謙之學,家學氛圍濃厚。李裕自己也博學多才,詩文“披文相質,落紙斐然”。又有戚崇僧,金華人,呂祖謙弟子戚如琥之后,祖戚紹、父戚象祖都是王柏的講友。戚崇僧一直致力于家學延續,后又從學于許謙,清苫白處,被同門推為高弟,著有《四書儀對》、《昭穆圖》、《春秋纂例》等。
五、元明之際:以宋濂、王袆為盟主的第四代傳承
元末,朱元璋起兵反元,在江浙曾建立以婺州為中心的浙東根據地,并在婺州網羅了大批文士,為定鼎天下出謀獻策,貢獻尤多。洪武建國后,朝廷禮儀、文教等制度決策,又多有賴于婺州士人的裁定,正如劉基所說:圣天子龍興江右,文學之士彬彬然為朝廷出者,金華之君子居多。”不僅如此,婺州諸儒在元末明初理學傳承的斷層期,起了重要的承接作用,“元明之間,守先啟后,在于金華。”婺州一地的理學也成為洪武儒學的主流。而婺州諸儒中的盟主,非宋濂與王袆莫屬。
宋濂、王袆二人,在學統上,均可追溯到呂祖謙,又都以振興呂學為己任。只是在為學氣象上,宋濂既重心性道德,亦重經史文獻、利義事功,最得東萊呂氏之學的學術態度,通諸家之說而取其長,匯諸家之博大氣象,成為婺學的集大成者。而在史學精深方面,王袆更忠實于呂學精髓的原貌,無論在史學的見地上還是在治史的功底上,都要略勝于宋濂一籌,因而稱其為明初史壇的盟主并不過分。一博一精,二人共同繼承和發揚東萊呂學的優良傳統。正基于此,《宋元學案·東萊學案》中將宋濂、王袆二人列為“呂學續傳”。
從上述四代呂學傳承系譜中可以看出,文學的氣氛越來越濃重。而這,也可說是貫徹了呂學重視文學的優良傳統。呂祖謙不僅在理學內部調和朱陸之學,而且在理學外部也主張重道不廢文,融合理學與文學,自元祜后,談理者祖程,論文者宗蘇,而理與文分為二。呂公病其然,思融會之。”從呂祖謙開始,呂學弟子一直重視文學創作,婺州諸儒都有大量詩歌與散文作品,但吟誦的并非風月之詞,而是始終貫徹文以載道的文學理念。當然.作為呂學精髓的經史并重與崇尚務實的學術風格一直或隱或顯地傳遞延續,由于受學術發展內在邏輯和社會時代背景的影響,有時被文學掩蓋,以致黃百家作出“金華之學,自白云一輩而下,多流而為文人”的誤判,但黃氏仍認為理學的因子深深根植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得以傳承,夫文與道不相離,文顯而道薄耳,雖然,道之不亡也,猶幸有斯!”理學如此,史學亦是如此。正因為此,南宋至明清數百年間,浙東地區形成了“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浙東學派,歷久不衰。
參考文獻:
[1]鄧鐘玉.《光緒金華縣志》卷七《學校》,民國四年刻奉.
[2]張廷玉.明史》卷二八九《王袆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4.
[3]傘祖望,《宋元學案》卷八十二《北山四先生學案》[M].北京:中華書局,1986.
[4]宋濂,《思媺人辭》,《宋濂傘集》第一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5]何炳松.浙東學派溯源[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6]歐陽玄.《浦陽人物記原序》,《宋濂傘集》第四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7]薛應旃.《浦江宋先生祠堂碑》,《宋濂傘集》第四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