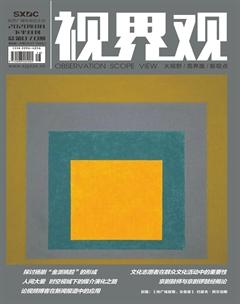從余金平二審改判案件看控審關系
摘要:近日,余金平交通肇事罪二審改判案件引起熱議,其背后體現出的程序法問題為諸多學者所爭論。本文以認罪認罰具結書的效力為切入點,從本案體現出的控審關系問題出發,探尋健康的控審關系。
關鍵詞:創業;發展規劃;控審關系;認罪認罰;余金平二審改判案件
一、案情及焦點
1.案情
(1)案件經過
2019年6月5日21時許,中國中鐵股份有限公司總部紀委綜合室工作人員余金平酒后駕駛白色豐田牌小型普通客車由南向北行使至北京市門頭溝區河堤路1公里處時,車輛前部右側撞到被害人宋某致其死亡,撞人后余金平駕車逃逸,隨后,被告人余金平在自家地下室擦拭車身血跡并步行返回案發現場觀望,之后逃離。2019年6月6日5時許,被告人余金平到公安機關自動投案,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但其供述罪行中表示事發當時并未發覺撞人。2019年6月6日5時30分許,被告人余金平經呼吸式酒精檢測,血液酒精濃度為8.6毫克/100毫升,經北京市公安局門頭溝分局交通支隊認定,被告人余金平發生事故時系酒后駕車,且駕車逃逸,負事故主要責任。2019年6月17日,被告人余金平家屬賠償被害人宋某的近親屬各項經濟損失共計人民幣160萬元,獲得被害人近親屬的諒解。公訴機關提起公訴,并根據余金平自愿認罪認罰,提出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的量刑建議。
(2)一審
一審法院北京市門頭溝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余金平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酒后駕駛機動車,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并負事故全部責任,且在事后逃逸,其行為已構成交通肇事罪,應依法懲處;被告人余金平作為一名紀檢干部,本應嚴格要求自己,其明知酒后不能駕車,但仍酒后駕車從海淀區回門頭溝區住所,并在發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特別是逃逸后擦拭車身血跡,回現場附近觀望后仍選擇逃離,意圖逃避法律追究,表明其主觀惡性較大,判處緩刑不足以懲戒犯罪,因此對公訴機關判處緩刑的量刑建議不予采納;被告人余金平自動投案,到案后如實供述犯罪事實,可認定為自首,依法減輕處罰;被告人余金平系初犯且已積極賠償被害人家屬經濟損失并得到諒解,可酌情從輕處罰。并據此做出了被告人余金平犯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的判決。
(3)抗訴
一審判決做出之后,原公訴機關北京市門頭溝區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認為原判量刑錯誤:本案不屬于法定的改判情形,余金平自愿認罪認罰并在其辯護人的見證下簽署具結書,符合緩刑適用條件,公訴機關提出的緩刑建議不屬于明顯不當,不屬于量刑畸輕畸重影響公正審判的情形,一審法院改判屬程序違法;一審法院以余金平為紀檢干部為由加重處罰沒有法律依據,一審法院的認定是將酒后駕車和事后逃逸作為加重的犯罪情節與量刑情節予以評價,系對同一情節的重復評價,本案屬過失犯罪,且余金平自動投案,悔罪態度良好,已得到被害人家屬的諒解,一審法院認定余金平主觀惡性大不準確,因此一審法院不采納量刑建議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人余金平犯罪情節較輕、悔罪態度良好,沒有再犯危險,宣告緩刑對其所居住的社區沒有重大不良影響,符合適用緩刑條件;一審法院對類似案件曾判緩刑,對本案屬于同案不同判。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支持抗訴。同時,原審被告人余金平不服提出上訴,請求撤銷一審判決,改判兩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適用緩刑。
(4)二審
二審法院認為余金平交通肇事后逃逸,因而構成交通肇事罪的加重犯而非基本犯;一審法院并未將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情節二次評價為從重處罰情節,余金平對事故負全部責任并非基于肇事后逃逸,本案中的逃逸行為屬于法定的加重情節而非入罪情節,因此不存在二次評價的問題;一審法院將余金平肇事后逃逸作為不適用緩刑的理由之一,并不違反禁止重復評價原則;本案中余金平身為紀檢工作人員,應更加嚴格要求自己,模范遵守法律法規,法院在評估時應做考慮本案中種種證據表明,被告人并非過失犯罪,其主觀惡性較大,犯罪情節惡劣。并決定駁回北京市門頭溝區人民檢察院的抗訴及余金平的上訴;撤銷一審判決;作出上訴人余金平犯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的判決。
2.主要爭議焦點
從控審關系看,本案爭議焦點主要有:公訴機關確定余金平具備認罪認罰條件是否合理;人民法院是否可以調整認罪認罰從寬案件的量刑;檢察機關在認罪認罰從寬案件中的抗訴權問題;人民檢察院提起有利于被告人的公訴二審法院是否可以做出更重的判決。
二、認罪認罰具結書的效力
1.對認罪認罰的解讀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實際上是國家公訴權的減讓,實現公訴權由檢察機關“一手遮天”向檢察機關與當事人、辯護律師協商型的轉變。其目的在于幫助被告人認罪、悔罪,修復社會關系[1]以及推動刑事案件的繁簡分流、節約司法資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認罪認罰并與檢察機關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則可以從寬處理,這在形式上看來相當于是檢察機關代表國家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形成了一個合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主動減輕司法機關的負擔,減輕自己的社會危害性,而國家則給他相應的從寬處理。然而《認罪認罰具結書》并不是檢察機關對被告人作出的保證和誓言,若遇到證據采信、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等問題時,還應當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及時調整認罪認罰工作,比如重新簽署《具結書》,又或是撕毀《具結書》[2]。
2.訴訟合意對法官有限的約束力
3.法官量刑權與檢察機關量刑建議
(1)人民法院有權對認罪認罰案件調整量刑
(2)人民檢察院有量刑建議調整權
三、本案體現出的控審關系問題
1.人民檢察院濫用抗訴權影響人民法院判決的權威
2.人民檢察院雙重身份有悖司法公正
3.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
4.人民法院逾越裁判角色,“自訴自審”
四、健康的控審關系
1.三角結構
2.控審合作,互相配合
3.控審分離,相互制約
我國當前立法對相關內容規定較為模糊,難以很好的規制問題,有效做到控審分離,因此在日后的司法改革中,應當全面審視相關問題,在立法方面做出改變,從而自根本處優化控審關系,解決由此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參考文獻:
[1]吳春妹:《副檢察長解讀余某交通肇事案:上訴不加刑,抗訴求輕可加刑嗎?》,載刑事法庫,http://mp.weixin.qq.com/s/-T82QQCwZRoCgOH2xx9CgXw。
[2]吳春妹:《副檢察長解讀余某交通肇事案:上訴不加刑,抗訴求輕可加刑嗎?》,載刑事法庫,http://mp.weixin.qq.com/s/-T82QQCwZRoCgOH2xx9Cgxw。
作者簡介:叢琳(2000-),女,山東灘坊人,本科,研究方向: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