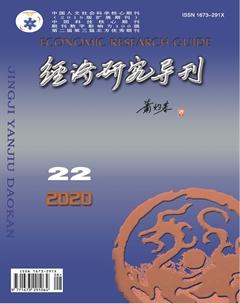美國宏觀審慎政策實踐及對中國的啟示
仵潔
摘 要:與危機相關的GDP損失可以歸因于兩方面,即金融體系的脆弱性,表現為非銀行金融中介杠桿率的上升和對短期融資的依賴,另一方面表現為家庭債務的累積。闡述美國宏觀審慎政策措施及其校準,并在審視美國宏觀審慎監管權力框架的基礎上,總結其實踐經驗對中國的啟示。
關鍵詞:美國;宏觀審慎政策;國際經驗;啟示
中圖分類號:F830 ?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0)22-0155-02
2009年3月,在全球金融危機嚴重爆發時期,時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對美國監管框架所存在的缺陷提出了彌補意見,建議建立一個專門負責監督和解決系統性風險的機構,來維護金融系統免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建立具有正確目標、激勵措施和政策工具的宏觀審慎框架,將使金融穩定成為一個可以實現的目標。本文描述了危機期間美國所實施的宏觀審慎政策,并總結了監管實踐中得到的啟示。
一、導致金融危機的斷層線
1.金融脆弱性增加。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幾年里,金融體系中的脆弱性顯著增加,即使是金融機構相對較小的損失也足以引發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問題。首先,債務融資的使用在各機構之間存在顯著差異。與儲蓄機構相比,經紀交易商,即美國的專業投資銀行、大型銀行集團的投資銀行子公司和政府支持機構的杠桿率要高得多。其次,除了不斷增加的杠桿作用外,傳統上經紀商交易高度依賴于短期的批發融資,這些資金中有很大一部分采取了回購形式。此外,其他形式的短期融資也經歷了快速增長,如商業票據發行。回購和票據的增長與貨幣市場共同基金規模的增加伴生,且貨幣市場共同基金沒有任何資本用以保護短期投資免受損失。該時期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非銀行信貸成為實體經濟日益重要的信貸來源,脆弱性在傳統商業銀行系統之外累積。總的來說,宏觀審慎監管機構需要找到一種方式,改變銀行和非銀行依賴債務融資的傾向和融資期限。
2.家庭債務增加。隨著金融體系中杠桿率和期限轉換明顯的增加,實體經濟中債務迅速增加,并集中在家庭抵押貸款上。首先,家庭債務總量激增。從2001年第四季度到2007年第四季度,抵押貸款翻了一番,而企業債務增長在此期間與GDP增長基本一致。其次,危機前期,貸款標準明顯放松。激進的信貸供應擴張,加上金融創新,更多信貸發放給負債累累的家庭,家庭資產負債表越來越容易受到沖擊。
3.去杠桿化和經濟收縮的反饋循環。首先,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意味著,房地產市場的低迷導致中介機構出現償付能力和資金流動性問題,使得放貸機構不愿或不能提供新貸款。這導致實體經濟出現“信貸緊縮”,進而對實體經濟活動產生不利影響。其次,當房價下跌時,負債累累的家庭通過大幅減少非住房消費來降低負債。這導致總需求溢出效應,在經濟努力重新分配資源的過程中,支出急劇萎縮導致失業和進一步削減支出的螺旋式上升,這些渠道對危機的成本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美國宏觀審慎政策的措施及校準
1.風險積累的識別。從21世紀初開始,雖然家庭債務的增加十分明顯,但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對次級抵押貸款部門風險的認識較晚。雖然,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已經意識到金融系統的脆弱性,例如對回購的依賴,但并沒有識別出金融系統內所有的斷層線,例如商業票據的增長。房地產泡沫在2005年后期被注意到,但仍早于危機之前,美聯儲并未預料到這對更廣泛的金融體系的恢復力產生的影響。危機以來,銀行系統壓力測試的開發有助于發現這種影響。為了揭示存在的脆弱性的所有程度,壓力測試必須包括某些非銀行和市場,如交易銀行、商業票據、回購和衍生品市場,以及結構性投資工具和渠道。但在危機發生之前,充分了解整個系統的資金流動尤為困難。從美聯儲在危機期間的實踐來看,對整個系統資金流動的認知不足,一方面與回購交易的數據缺失有關,另一方面與對商業票據市場風險認識的缺失有關。
2.減少杠桿的措施。在2008年危機最嚴重時期,通過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ARP),美國財政部投資2 000億美元購買15家大型金融機構的優先股,以提高市場對銀行體系的信心,從而提高其放貸能力。這種干預措施與隨后的監管資本評估計劃(SCAP)一起,旨在改善市場參與者對美國銀行系統償付能力。為了解決系統范圍內的杠桿問題,宏觀審慎資本工具的應用,如逆周期資本緩沖,以建立額外的損失吸收能力,并取得較上述救助計劃而言更好的政策效果。截至2005年,上述15家大型金融機構的風險加權資產總額約為8.4萬億美元,通過測算表明,若對其設立3%的逆周期資本緩沖,將提供與2 000億美元TARP相當的彈性水平。此外,若對其設定4.7%的逆周期資本緩沖,還可以通過允許銀行按照歷史信貸增長率繼續放貸,從而減輕TARP帶來的信貸緊縮效應。同時,若設定4.2%的逆周期資本緩沖,可以削弱2009年SCAP壓力測試評估要求上述銀行增加資本所帶來的信貸緊縮效應。
3.降低資金錯配的措施。危機期間,美聯儲創設了一系列新的流動性調節工具,為美國金融體系提供了約1.5萬億美元流動性。通過測算得出,對相關金融機構適用凈穩定融資率(NSFR),即巴塞爾協議III中限制流動性轉換的要求,會帶來類似的結果。對12家美國大型銀行和投行實施同一等級的NSFR將導致其長期融資規模在2007年底增長1.4萬億美元。如果危機期間企業通過使用長期債務置換1.5萬億美元的短期資金能夠有效減緩流動性外流,從而使央行免于提供特殊流動性工具,那么在危機重現的時候應進一步擴大宏觀審慎政策干預規模。
4.減緩家庭債務積累的措施。通過增加借款人信貸成本,提高資本和流動性要求,或將有助于降低房價、遏制家庭債務增長。然而,在繁榮時期實施這些措施的影響可能很小。因此,為了減少家庭債務累積,宏觀審慎監管機構需要采取更多行動。抑制家庭債務累積的常用工具為貸款價值比(LTV)、貸款收入比(LTI)限制以及償付能力測試。LTI限制和償付能力標準的實施主要影響借款人中最脆弱的群體,所以對該群體的影響可能會大于總體貸款關系所顯示的情況。大量證據表明,債臺高筑的借款者在經歷了房地產危機之后,削減消費的邊際傾向最大。引入這些工具旨在保護借款人免受或少受到沖擊來減少家庭消費的波動性,從而減緩不可持續的債務積累,并對危機期間總需求下降的外部性產生影響。
三、對中國宏觀審慎政策發展的啟示
1.完善宏觀審慎管理工作機制。一個具有清晰、透明、有力的宏觀審慎監管機構更可能成功地實施宏觀審慎政策行動。黨的十九大正式明確“健全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在此基礎上,應強化跨部門的信息及政策協調,將有助于提升宏觀審慎監管的有效性。當前,人民銀行被明確為宏觀審慎管理歸口部門,在此基礎上,建議在金融委協調機制下,成立宏觀審慎專項協調小組,并落實至省域層面,負責宏觀審慎政策的有效落實,并對系統重要性機構等特定機構或重大風險事件的管理和處置進行磋商。
2.加強風險意識宣傳。從處理危機的諸多事后觀點可看出,盡管在全球范圍內,宏觀審慎監管機構和央行對金融風險評估投入了巨大努力,但由于風險的積累并不總是明顯的實時現象,且在非危機時期,宏觀審慎工具的實施也具有廣泛的分配效應,對經濟活動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使得宏觀審慎政策面臨的“待驗證問題”比貨幣政策制定者所面臨的類似問題更為突出。因此,通過更廣泛的風險意識宣傳將有助于樹立宏觀審慎監管的信心問題。此外,建議加大宏觀審慎政策的宣傳力度,提高市場對宏觀審慎管理的認識。可考慮設立宏觀審慎自律機制,通過自律組織進行政策培訓、政策溝通以及窗口指導。
3.強調政策透明度及預期引導。對于一個獨立的宏觀審慎監管機構來說,授予其職權或更多權力,會帶來問責方面的挑戰。為避免宏觀審慎監管機構可能通過過度使用工具來防止危機,建立明確、規范的實施、評估、溝通流程,將有助于降低操作環節的風險。建議可借鑒當前人民銀行已定期發布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國金融穩定報告》,以及歐央行發布的《宏觀審慎報告》的形式,在保持政策透明度的基礎上,引導市場開展宏觀審慎政策分析和討論,提高市場對宏觀審慎管理的認知及理解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