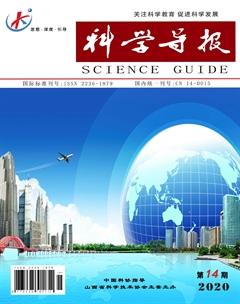論我國未成年被害人權益保護的現(xiàn)狀及對策
摘 要:隨著大量未成年人案件的產(chǎn)生,少年司法再一次成為社會熱議的焦點。我國目前對于未成年犯罪人的保護體系已經(jīng)初步產(chǎn)生;但是立法上對處于雙重弱勢地位的未成年被害人來說,基本是空白的。所以本文以未成年被害人為出發(fā)點,就其權益保護的現(xiàn)狀和不足發(fā)表一些自己的淺顯建議,認為強化未成年被害人的訴訟當事人地位、系統(tǒng)鞏固其參與訴訟的方式、創(chuàng)新證據(jù)取得途徑、建立國家補償?shù)戎贫葘暮艽蟪潭壬媳Wo未成年被害人的權益。
關鍵詞:未成年被害人;惡逆變;權益保護
隨著國外關于刑事被害人問題的關注,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也逐漸對刑事被害人相關問題有了初步探索。此后,國內(nèi)的研究焦點主要集中于刑事被害人的訴訟權利、訴訟地位和救濟途徑三大方面。旨在營造一種參與刑事訴訟各方當事人的權利相對平衡的訴訟機制來更好地保證訴訟結(jié)構(gòu)的科學化。這些研究開始將關注點轉(zhuǎn)移到刑事被害人身上,開始關注被害人這個大的弱勢群體,對我國刑事訴訟法的進步做出了很大貢獻。但是現(xiàn)在看來,其中忽視了既處于未成年人弱勢又處于刑事被害人弱勢,這一具有雙重弱勢地位的“未成年被害人”群體。后來的研究雖然也關注到了未成年人被害后的心理干預問題,但是關于系統(tǒng)保障未成年被害人參與刑事司法程序研究依舊較少。所以,關于刑事訴訟中未成年被害人權益保護的研究依舊有著很大的空間。
一、我國關于未成年被害人權益保護的現(xiàn)狀
(一)訴訟地位方面
我國在96年的《刑事訴訟法》中確立了被害人的當事人地位。后又考慮到未成年人的特殊性,2012 年的《刑事訴訟法》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訴訟程序又做出了專章規(guī)定,2019年的《刑事訴訟法》對此改變不大。但是,該特別程序主要關注涉罪未成年人,對未成年被害人的權益保護雖然稍有體現(xiàn),但是過于隱晦。例如:檢察機關在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以前應當聽取被害人的意見以及不服不起訴決定的被害人享有申訴的權利等等。可見法條只是將未成年被害人作為被害人這一大的群體做了一些規(guī)定,沒有考慮到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性。
(二)權益實現(xiàn)方面
1.大量案件難以進入立案程序
有學者提出,犯罪黑數(shù)的存在是一種普遍的現(xiàn)象,造成犯罪黑數(shù)的原因在于以下三個環(huán)節(jié):“第一,犯罪行為是否為社會中的個人所感知;第二,感知犯罪行為的人是否認為該行為構(gòu)成犯罪;第三,認為某項行為構(gòu)成犯罪的個人是否愿意向國家追訴機關報告。”相比于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感知行為是否構(gòu)成犯罪以及是否愿意尋求國家追訴方面,存在犯罪黑數(shù)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有很多的案件根本無法進入刑事訴訟程序。對于未成年被害人來說,有時候即使自己意識到需要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問題,告訴家長后,家長往往也會由于家長之間的“顏面”問題而置之不理。近年,媒體將“校園暴力”這一問題又一次推上了風口浪尖,細究校園暴力事件造成嚴重后果的成因,我認為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學校、家長甚至公安機關對此類案件發(fā)生的前期簡單的定性為孩子之間的“打鬧”行為,既沒有威懾到強勢的孩子,也沒有照顧到弱勢的孩子,從而導致強勢的孩子更加肆無忌憚。
2.對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解存在偏差
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88條明確的規(guī)定了刑事和解程序的兩種情形,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只有涉及其中法定情形,即第一,因民間糾紛引起的;第二,侵犯公民人身、民主、財產(chǎn)權利,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第三,除瀆職罪外的可能判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過失犯罪案件。才能適用刑事和解程序。然而在具體運用到實踐中的司法解釋上,卻擴大了未成年人案件刑事和解的范圍。例如最高人民檢察院在2017年發(fā)布的《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指引(試行)》第67條規(guī)定的刑事和解的范圍如下:一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的;二是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民主、財產(chǎn)權利,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三是過失犯罪的。司法解釋對和解范圍的擴大不論怎么解釋,在法理上都是說不通的。不僅如此,對和解范圍的擴大只是單純的站在未成年犯罪人的角度上來說的,關注點在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和處罰方面,對于沒有做任何錯事的未成年被害人來說,是對其權利的直接剝奪。在實踐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則遵循了“司法調(diào)解模式”,檢察機關并非扮演末端參與的角色,而是積極主動地進行各種居中調(diào)停工作。有的時候甚至替未成年被害人選擇了原諒。
3.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大量運用是對未成年被害人權力的排擠
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是在辦理未成年人案件的過程中,給予檢察機關更大的裁量權。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實施意味著眾多未成年人案件不需要經(jīng)過法庭審判就可以解決。檢察機關既負責追訴,又負責案件的裁判,后續(xù)的執(zhí)行也由檢察機關來監(jiān)督實施,這種捕、訴、監(jiān)、防的“一體化”模式加大了集權程度。實踐中,檢察機關對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適用是缺乏制約和監(jiān)督的,雖然有法律規(guī)定檢察機關在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前以及考驗期滿后決定不起訴前也應當聽取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公安機關、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等主體的意見,但是這些主體面對強勢的檢察機關時,其意見并不具有實質(zhì)的約束。此時的檢察機關為了辦案考核的需要,無疑會大量的適用附條件不起訴制度來處理案件。但是,未成年被害人不服的話,法律既沒有規(guī)定能自訴,也沒有申訴程序。所以,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無疑會排擠未成年被害人的應有權利。
二、我國未成年被害人權益保護的不足之處
(一)缺乏訴訟中的專門保護
對于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在立案偵查、審查起訴和法庭審判各個階段都應當有體系性的專門保護,應當與普通案件劃出界限,特事特辦。我國《刑事訴訟法》針對未成年人的案件在程序運行中,只明確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詢問時要有合適成年人在場。對于未成年被害人只是說了參照執(zhí)行,沒有細致的規(guī)定未成年被害人在刑事訴訟各個階段的權益保護。但是通過上文中的分析可知,未成年被害人作為具有雙重弱勢的群體,其權益的保護更應該得到關注。還有一種更為嚴重的情況就是在庭審過程中,未成年被害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幾乎都不出庭,即使出庭也是旁聽人員,所以法律賦予未成年被害人以當事人的地位參與訴訟的規(guī)定實際已是名存實亡。
(二)刑事司法援助出現(xiàn)缺位
我國關于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對象僅僅是未成年犯罪人,對于未成年被害人的援助,法律并沒有做出規(guī)定。同樣是未成年人,未成年犯罪人既能得到法律援助,又能得到心理健康評估和社會調(diào)查幫扶;而未成年被害人既受到犯罪行為的侵害,又不能得到相對應的合理援助,可想而知,這一制度是多么的不科學。國家擁有刑事案件的控訴權,公訴機關代表國家行使這一權利,但是公訴機關能否滿足受到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譴責犯罪的強烈心理?結(jié)果顯然是否定的。由于缺乏法律援助的支撐,未成年被害人更多的時候都是“被原諒”結(jié)果的實際承受者。
(三)判決后續(xù)的保護過于乏力
緩解未成年被害人的仇恨心理,給未成年被害人合理的宣泄途徑是有效防止未成年被害人“惡逆變”的重要舉措。我國刑事訴訟過程中,未成年被害人在執(zhí)行以前的階段雖然權利保障不夠充分,但是好歹擁有一定的知情權;然而在執(zhí)行以及后續(xù)階段,未成年被害人幾乎是不能參與任何訴訟活動的,對于自己案件的犯罪人服刑情況、減刑情況更是無從知曉。這顯然切斷了未成年被害人合理發(fā)泄仇恨的途徑,對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健康只能產(chǎn)生不利影響。此外,結(jié)案后的未成年被害人因為犯罪行為的侵害,身心遭受到了極大地痛苦,對于其身心健康的恢復不能僅僅依靠家庭的力量,家庭在資金、專業(yè)疏導和教育等方面的能力是很弱的,后續(xù)的保護對于未成年被害人正常回歸社會生活,避免發(fā)生逆變極為重要;但是我國在這一方面的關注度幾乎為零。
三、構(gòu)建未成年被害人權益保護機制的對策
(一)發(fā)揮立案方式多元化的優(yōu)勢
應當以偵檢一體化作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立案、撤案監(jiān)督的改革方向。也就是說關于未成年人案件,公安機關處理的時候,不論立案還是撤案,都應當向檢察機關報備。近年的檢察機關大部制改革已經(jīng)完成,檢察機關已經(jīng)具有專門處理未成年人案件的部門,所以立案時專門的未成年人檢察機關就介入偵查是對公安機關隨意撤案的限制。能讓更多的未成年人案件進入到后續(xù)的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是對未成年被害人權益保護第一步。此外,對于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公安機關在辦理未達刑事立案標準的案件時應當采取相應的預防監(jiān)控措施,不能僅是簡單的教育處理;也應該考慮適度放寬未成年人案件的立案標準,正是由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所以在證據(jù)的收集方面比較困難,如果報案的當時就決定“證據(jù)不足,不予立案”的話,略顯草率。公力救濟實現(xiàn)不了的情況下,私力救濟就會盛行,尤其是對于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被害人而言。
(二)創(chuàng)立特別的取證模式
未成年人案件難辦的重要原因在于取證難。對于未成年人案件,既有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意識弱,沒有證據(jù)保全意識的因素,又有偵察機關辦案過程機械化,對未成年被害人造成二次傷害,致使未成年被害人表述混亂等因素。要求未成年被害人具有證據(jù)保全意識是一種苛責,所以針對國內(nèi)的情況,首先,應當在降低立案標準的同時,建立專門的偵查取證部門,并且該部門應當以女性偵查員為主。對于未成年被害人而言,女性細膩的性格語言優(yōu)勢,往往對證據(jù)收集的幫助更大。專業(yè)的團隊辦理專門的案件也能有效減少機械化問題的存在。其次,應當學習我國香港地區(qū)的“家居環(huán)境下的調(diào)查訪問制度”香港警方在向未成年人取證時都在“家居錄影室”進行,家具錄影室都是相對保密的民房,裝修布局跟一般家庭基本相同,且錄影時也是在隱蔽位置秘密進行。詢問全程也都有未成年被害人家長、心理專家陪同。法醫(yī)也能保證隨時到達,隨時取證,并且固定證據(jù)。這種模式的取證,既能將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壓力和二次傷害降到最低,又能高效的獲取證據(jù)并及時固定。此兩種取證方式的創(chuàng)新將更好的保護未成年被害人群體。
(三)未成年被害人案件要慎用刑事和解和附條件不起訴程序
刑事訴訟法中增加未成年被害人專門一章用于保證其權益得到實現(xiàn),是日后立法應當關注的地方。法律應當明確未成年被害人這一特殊群體的訴訟地位、明確規(guī)定對未成年被害人心理干預和幫扶教育的機構(gòu)、明確未成年被害人的知情權、表達權、律師參與權、合適成年人發(fā)表意見權等相應的權利。但是對于刑事和解制度的適用要充分考慮有表達能力的未成年人本人的意思,這里重點強調(diào)的是未成年被害人本人的表達權。不僅如此,檢察機關要注意自己的角色定位,不能作為未成年人案件的居中調(diào)停者,更不能成為二次傷害未成年被害人訴訟權益的推手。對于法律規(guī)定的“教育”方針,不能簡單的理解為寬容和輕刑,更應當發(fā)揮處罰的教育功能,在處罰的同時教育,其效果可能更佳。實踐中,很多未成年人都有“趁著十四歲之前大干一場”的想法,所以如果一味地寬容放縱,法律對未成年人的教育作用也就不能發(fā)揮了。對于未成年被害人權益如此的忽視,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的話,可能會導致新問題的產(chǎn)生。
附條件不起訴制度主要針對的是未成年犯罪人,比較未成年犯罪人和未成年被害人兩個群體實際所受的傷害,未成年被害人顯然更甚,所以對于附條件不起訴制度也應當做一個比較,當犯罪人和被害人都是未成年人的時候,適用附條件不起訴制度顯然對未成年被害人是不公正的。一味地強調(diào)未成年犯罪人的各種權益實際上有點本末倒置的嫌疑。
(四)建立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干預和國家補償制度
未成年犯罪案件中,防止未成年被害人“惡逆變”,是不容忽視的問題。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未成年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沒有合理宣泄的途徑,心中的怨恨和報復心理依舊很強;二是由于未成年被害人在訴訟結(jié)束后的心理疏導和繼續(xù)教育做的不夠到位,沒能讓其順利回歸社會;三是由于家庭或者外界的其他因素刺激導致未成年被害人心理發(fā)生變異,走向極端。上述第一條的情況可以通過加強未成年被害人的訴訟參與權得到解決;二、三條的情形更加偏重于社會責任,所以檢察機關應當承當起相應的社會責任,幫助未成年被害人順利回到社會。一方面建立未成年被害人心理干預工作的考核機制,以考核的方式推動檢察機關對未成年被害人心理和后續(xù)教育的關注。另一方面要建立國家補償制度,刑事案件的民事賠償一般都較難獲得,所以在未成年被害人家庭遭受重創(chuàng)的時候,也就是檢察機關在立案初期,就應該對生活困難的家庭給予持續(xù)時間較長的經(jīng)濟補償,通過經(jīng)濟補償、法律援助、心理干預等多措并舉的方式,幫助未成年被害人家庭順利度過難關。從而減少未成年被害人“惡逆變”現(xiàn)象的發(fā)生。
參考文獻
[1] 宋英輝 吳宏耀.刑事審判前程序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2] 陳瑞華.刑事訴訟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國的興起.中國法學.2006(5).
[3] 謝登科.集權與制衡:論附條件不起訴中的權力配置.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4] 陳衛(wèi)東.中國刑事訴訟權能的變革與發(fā)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5] 馬忠紅.香港警方辦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案件的做法及啟示.中國青年研究.2006(9).
作者簡介:周昊(1996-),男,漢族,甘肅張掖人,西北政法大學刑事法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訴訟法學(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