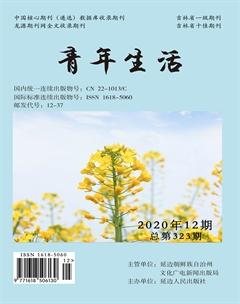GDPR被遺忘權對中國法治建設的啟示
賴秋蒙
摘要:被遺忘權(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是信息時代下的典型產物。在人類 ?的歷史長河中,早期,遺忘是常態,記得才是非常態,最初的結繩記憶法就是為了記住一件事情而大費周章。但是經過工業時代,伴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信息在網絡中很輕易地被一個網站,一些代碼記住,被遺忘反而成了需要額外操作才能完成的事情。 GDPR便是一個時代產物,本文將梳理被遺忘權從出現到發展的整個過程,對比分析被遺忘權與刪除權等等GDPR中規定的其他類似權利,列舉學界對被遺忘權的紛雜的看法,在這樣的系統介紹與對比之后,歸納被遺忘權對中國的信息保護與法治建設有何啟示。
關鍵詞:被遺忘權;GDPR;信息時代
1.被遺忘權的出現與發展
1995 年,歐盟出臺的《關于涉及個人數據處理的個人保護以及此類數據自由流通的指令(95/ 46/EC)》(以下簡稱《指令》)規定公民可以在其個人數據不再需要時提出刪除請求,以保護個人數據信息,這個《指令》被看作是被遺忘權的雛形。
2012年歐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公布了《關于涉及個人數據處理的個人保護以及此類數據自由流動的第2012/72、73號草案》,其中包含了被遺忘權。
2018年5月25日,歐盟出臺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大陸譯作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其中明確規定了歐盟成員國公民合法地享有被遺忘權,即歐盟公民有權在個人信息優于個人信息的前提下,要求信息控制者刪除其過時的、負面的、真實的信息。
最早涉及到被遺忘權的是2009年的Google Spain一案,“Google Spain”一案是由西班牙公民馬里奧·考斯特加·岡薩雷斯向西班牙數據保護局提起申訴,控告《先鋒報》、谷歌公司及谷歌西班牙分公司侵犯其數據隱私權,案件起因于網絡用戶通過谷歌搜索原告姓名,搜索結果顯示了《先鋒報》報紙刊登岡薩雷斯數年前房地產因欠費而被強制拍賣的內容。
Google Spain一案法院對案件的判決是最初的被遺忘權的邊界,西班牙公民馬里奧·考斯特加·岡薩雷斯的在提起申訴時的訴訟標的不僅僅要求谷歌總部以及谷歌西班牙刪除能夠進入到關于其負面報道的鏈接,還徑直要求《先鋒報》刪除特定的那一篇報道,但是The Spanish Data Protection Agency卻拒絕了要求媒體方刪除原本報道的訴訟請求,而將義務限定在了搜索引擎一方,也并沒有將責任從西班牙延申到美國谷歌總部。
El País一案突破了被遺忘權義務沒有附加到新聞媒體本身的限制,西班牙最高法院以“El País作為新聞檔案的經營者,有技術能力向搜索引擎一方提示是否要將特定文章納入其搜索數據庫”為原因要求El País報紙刪除了源報告。同樣的,德國漢堡的政客戀童癖丑聞一案,報道此事的新聞媒體也被要求處理原報告。
2016年的比利時一案中,法院判決新聞媒體處理原報道的理由則不再是技術原因,而是對比新聞媒體的言論自由與個人的隱私權利,來得出該案中所涉及的個人隱私權利要優于新聞媒體的言論自由權利。
緊接著比利時法院的決定,意大利最高法院提出了更為大膽的看法,其認為新聞報道有一定的保質期,像食品一樣,壞掉了就應該被處理,所以采取了刪除報道的處理方法。
這幾個典型歐洲案例使得被遺忘權的邊界越發擴大,一開始因為言論自由而沒有承擔被遺忘權義務的新聞媒體開始承擔著義務,并且法院要求處理原報道的手段,從去引擎化到匿名化處理到直接刪除,愈加突破新聞媒體的底線。
至今,GDPR中的被遺忘權已經伴隨著歐盟成員的全球化流動強勢地突破了地理的限制,這給了許多資料控制著,也就是許多社交網絡的運營商很大的法律應對壓力,也給技術人員應對被遺忘權出了一道難題。全球化趨勢不可避免,勢不可擋,歐盟作為一個世界級大經濟體,它的法律必然會被世界上各個大國考量,那么,被遺忘權在全球的滲透也是不可避免的[1]。
2.被遺忘權與GDPR中其他權利的對比
2.1被遺忘權與刪除權
被遺忘權與刪除權是最容易混淆的兩個權利,但需要明確的是被遺忘權并不是單純地賦予資料主體一個絕對的刪除資料的權利,而是調節、調和各種錯雜和沖突的利益的權利,其更優先的衡量還要落在被遺忘權行使的標的信息是否已經過時,即對公共利益來說已經無關緊要或者說雖然還有關緊要但是不優于個人信息保護。
資料主體都不愿意有關自身的負面的真實的信息存留在信息網絡里面,此時被遺忘便是資料主體要行使的權利,有些信息已經年代已久,雖然真實但是已經對公共利益沒有影響,這個時候法院往往會判定對信息進行或者去引擎化處理,或者匿名處理,或者刪除處理。但是一些信息,譬如說犯罪記錄,對于公共利益有很大的影響,就不可以輕易地刪除,而是要保留在信息網絡中讓人們可以查詢,然后避免對公共利益產生不良影響。
2.2被遺忘權與個人信息權
個人信息權的價值基礎是“信息自決”,信息自決的核心在于個人對信息的支配和控制。部分學者認為: 信息主體被認為享有知悉個人信息被處理,個人信息正確和完整及信息使用符合特定目的等利益。此外,信息主體不僅可以公開自己的信息,還可以參與信息公開之后的維護,在公開的信息被不當使用或超出特定目的使用時,信息主體可以要求使用人承擔侵權責任等。這樣的個人信息權具有了所有權特性,具有對世性。但實踐中,個人信息往往與公共領域相互交織,個人信息權與公眾知情權,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難以人為分割。因此,過分強調個人信息權,過度擴張個人信息權的外延,難以實現個體與公眾雙方利益平衡。
這一點也體現在GDPR第三章標題為“數據主體的權利”而非“個人數據權”。被遺忘權是在數據已脫離主體控制、支配后,主體為維護自身“人格特性”而自主采用的權利形式[2]。此時客觀上,數據已不受主體控制,顯然已不再是個人信息權的范疇,否則就有過度擴張個人信息權之嫌。因此,我認為被遺忘權是獨立于個人信息權的一項民事權利。
2.3被遺忘權與隱私權
被遺忘權常常與隱私權聯系在一起,早些年司法實踐中,法院也常用隱私權來保護個人數據。因此,過去學者們普遍認為被遺忘權與個人信息權同屬于隱私權范圍。但比較發現二者之間的區分還是很明顯的。依據中國現行法律規定,隱私權的客體為“未公開的私密信息“。而被遺忘權的客體還包括已公開的或已被采集和處理的信息,如:消費記錄、借貸信息等。因此,被遺忘權不能等同于隱私權[3]。
2.4被遺忘權與名譽權
大數據時代,公眾可以通過采集某個人的基本信息、消費記錄、行動路線等數據,還原該主體的“人格特性”。因此,數據的準確度、全面性會直接影響該主體的社會評價。
這也是被遺忘權與名譽權相聯系的原因。但依據現行法律規范及司法解釋規定,名譽權的核心在于因虛假、捏造的信息損害主體利益。而被遺忘權的對象不僅僅是虛假信息,還包括真實的信息,只是隨著時間形勢推移,該信息已無法客觀反映主體的真實“人格特性”。因此,被遺忘權不能等同于名譽權。
3.中美學界對被遺忘權的看法比較
中國學者普遍認為中國的個人隱私保護法應當被完善與推廣,目前個人隱私保護的法律實踐尚不完整,中國公民也缺乏保護個人隱私的意識,所以相對于臺灣的《個人資料法》來講,中國對于個資的保護還停留在相當初級的階段,個人的手機號碼被資料控制者隨意出賣,網頁瀏覽記錄被網站管理者隨意使用,因此中國學界認為GDPR是一個良好的示范,并且其在全球化過程中必然會推動中國對公民隱私的保護。
美國學者則是擔憂規定了被遺忘權的GDPR會因為邊界過度擴張而影響到美國社會注重的言論自由,新聞媒體是記錄歷史的重要平臺,如果因為被遺忘權的肆意行駛,其報道內容必然會經常面臨各種處理,這樣的成本巨大,新聞媒體還如何報道別人的負面新聞呢。
4..被遺忘權對中國法治建設的參考
經過對被遺忘權的介紹與對比,在簡單地認識了被遺忘權之后,筆者試圖就被遺忘權來對中國法治建設提出一點點參考。
首先,中國需創制一部完整的個人信息保護法,這樣在有了法律的創制之后,保護個人信息的意識才會逐漸在公民心中建立起來。而且在有了自身的個人信息保護法以后,才能更好地面臨GDPR伴隨著歐盟成員國公民泛濫全球化的趨勢與現象。才能作為一個大國有豐富完整的應對全球化策略。且通過建立個人信息保護法包含了被遺忘權的內涵。被遺忘權是一種既有精神利益也有物質利益的權益,這與個人信息的內涵是一致的,在個人信息保護立法中寫入個人信息刪除權,是保護被遺忘權合理有效的方式。
其次,應當在《侵權責任法》中建立針對侵犯被遺忘權的救濟措施與歸責機制。要讓被侵犯權利的公民能夠有清晰的途徑來尋求權利救濟,不僅要在民法中規定這項權利,提供權利基礎,還要在侵權責任機制里面賦予權利人求償的權利救濟方式。
結語
GDPR的大勢不可避免,被遺忘權僅僅是各個國家、各個信息網絡運營巨頭需要多加關心的一個方面,而GDPR其他更為苛刻更為嚴格的個人信息保護的要求更是需要全球來共同矚目的部分。
參考文獻:
[1]滿洪杰. 被遺忘權的解析與構建: 作為網絡時代信息價值糾偏機制的研究[J]. 法治與社會發展,2018( 2) .?
[2]劉文杰. 被遺忘權: 傳統元素、新語境與利益衡量[J]. 法學研究,2018( 2) .?
[3]李承亮. 個人信息保護的界限———以在線平臺評價為例[J]. 武 漢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