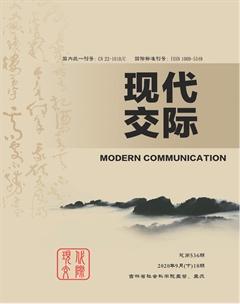試論《水滸傳》中暴力描寫及其藝術(shù)功能
文伊沆
摘要:從作品創(chuàng)作的現(xiàn)實(shí)語(yǔ)境與歷史背景,考察暴力描寫“由惡化美”的美學(xué)潛質(zhì)與價(jià)值,是客觀看待《水滸傳》中暴力描寫的重要途徑之一。《水滸傳》中暴力描寫,對(duì)于文本藝術(shù)功能的提升作用主要有三點(diǎn):一是拓展該作品在中國(guó)古典小說(shuō)史中的文學(xué)意義;二是完善敘事文本的敘事記人功能;三是經(jīng)過(guò)實(shí)現(xiàn)暴力描寫“由惡化美”的轉(zhuǎn)化,從而提升文本的美學(xué)潛質(zhì)與價(jià)值。
關(guān)鍵詞:《水滸傳》 暴力描寫 藝術(shù)功能 藝術(shù)價(jià)值
中圖分類號(hào):I207.41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9-5349(2020)18-0108-03
對(duì)《水滸傳》中暴力描寫的探究,有利于對(duì)暴力描寫產(chǎn)生“歷史的同情與審美的接受”,以辯證地看待《水滸傳》及其歷史文化價(jià)值。
一、《水滸傳》中暴力描寫概述
《水滸傳》是中國(guó)歷史上最早用白話文寫成的章回小說(shuō)之一,其對(duì)于中國(guó)乃至東亞的敘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都有極為深刻的影響。近幾十年來(lái),學(xué)界乃至社會(huì)輿論對(duì)《水滸傳》的批駁主要針對(duì)文本中大量的暴力描寫,如顏翔林在《第二批判:〈水滸傳〉的美學(xué)批判》中曾嚴(yán)詞指出,“(《水滸傳》)推崇原始暴力與非理性本能沖動(dòng)”,“是一部體現(xiàn)思維暴力和暴力美學(xué)的流俗作品”[1]。誠(chéng)然,《水滸傳》中確實(shí)存在大量暴力場(chǎng)面的文本描寫,若不考慮作品創(chuàng)作的現(xiàn)實(shí)語(yǔ)境與歷史背景,不考察暴力描寫“由惡化美”的美學(xué)潛質(zhì)與價(jià)值,只是一味批判其“暴力”“血腥”,毫無(wú)疑問(wèn)是有失偏頗的。
除去作品中人物運(yùn)用“非思考、超常人”的力量攻克難關(guān),如“魯智深倒拔垂楊柳”;或人物在遭遇威脅時(shí)正當(dāng)、恰當(dāng)?shù)淖晕曳佬l(wèi),如“武松景陽(yáng)岡打虎”的描寫。《水滸傳》中的暴力描寫可劃分為兩類:第一,戰(zhàn)爭(zhēng)時(shí)將軍士兵彼此間的拼殺。“戰(zhàn)爭(zhēng)”一詞本身便蘊(yùn)含殘忍、暴力、血腥,且互動(dòng)性戰(zhàn)爭(zhēng)的根源包括政治、軍事等復(fù)雜原因,絕非“暴力”一詞可一以概之;第二,梁山一百零八將對(duì)弱者生命的肆意傷害或殺戮,此類“暴力”對(duì)象又有兩種:一是罪有應(yīng)得、十惡不赦者,二是手無(wú)縛雞之力的無(wú)辜受害者。目前,對(duì)《水滸傳》暴力描寫的批駁主要在于第二類情景。對(duì)讀者而言,只有暫時(shí)跳脫現(xiàn)代社會(huì)的道德準(zhǔn)則與法律環(huán)境,不片面地以現(xiàn)代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作為判斷古典作品價(jià)值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我們才可以客觀探究這些暴力描寫對(duì)于豐富《水滸傳》文本藝術(shù)功能的成就與作用。
二、暴力描寫的藝術(shù)功能
《水滸傳》中的暴力描寫提升文本藝術(shù)功能的作用主要有三點(diǎn):一是豐富《水滸傳》在中國(guó)古典小說(shuō)史中的藝術(shù)貢獻(xiàn)與意義;二是完善敘事文本的敘事記人功能,推動(dòng)情節(jié)發(fā)展、體現(xiàn)文本主題;三是實(shí)現(xiàn)“由惡化美”的轉(zhuǎn)化,提升文本的美學(xué)潛質(zhì)與價(jià)值。
(一)在古典小說(shuō)史上的意義
1.對(duì)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丑惡面的文學(xué)補(bǔ)充
《水滸傳》之前的敘事文學(xué)中,由于社會(huì)環(huán)境、文化氛圍的影響,作家多傾向于創(chuàng)作符合讀者期待的作品,對(duì)故事有“大團(tuán)圓式結(jié)局”、傳達(dá)“真善美”意蘊(yùn)等“文本期待”,而對(duì)社會(huì)的“假、丑、惡、黑”多用隱晦筆法描寫或一筆帶過(guò)。《水滸傳》中對(duì)暴力場(chǎng)面的“直接”而不失文力的書寫,很好地補(bǔ)充了對(duì)社會(huì)中殘忍、暴力、血腥一面的真實(shí)描繪,為讀者提供“直面淋漓鮮血”的機(jī)會(huì)及更全面認(rèn)識(shí)社會(huì)的窗口。
以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中的家庭描寫為例。家庭是社會(huì)最小的構(gòu)成單位,以婚姻為主要維系方式的家庭面貌常真實(shí)反映出社會(huì)生活的基本形態(tài)與輿論氛圍。《水滸傳》在為數(shù)不多的家庭、婚姻描寫中,濃墨重彩地張揚(yáng)了婚姻中的暴力與非正義色彩。如鎮(zhèn)關(guān)西強(qiáng)媒硬保金翠蓮為妾,不久后卻將其拋棄并追討原典金銀,最終該婚事以魯提轄拳打鎮(zhèn)關(guān)西的暴力結(jié)局而告終。再如有夫之婦潘金蓮與西門慶通奸,并合謀殺害武大,最終武松將潘金蓮剖腹剜心,并割下西門慶首級(jí),方解其復(fù)仇之氣。《水滸傳》中的婚姻與家庭打碎了人們對(duì)傳統(tǒng)家庭中夫妻“舉案齊眉、相敬如賓”的理想,反而將婚姻中冷漠甚至殘忍的可能展現(xiàn)出來(lái),以“籠罩著濃重的暴力陰霾”的書寫,為讀者呈現(xiàn)了關(guān)于家庭和婚姻的破碎一面。
2.打破人物性格塑造單一化局限
在以往的敘事文學(xué)中,創(chuàng)作者對(duì)人物的塑造多囿于“好人無(wú)一處不好,壞人無(wú)一處不壞”的限制,由此形成的人物形象趨向于片面化、單薄化、簡(jiǎn)單化。而《水滸傳》借暴力描寫,生動(dòng)地刻畫各人物在不同遭遇之下做出的反應(yīng),顯示人物性格中單純與魯莽、率性與暴力、懷忠義之心與行殘暴舉動(dòng)等人性的真實(shí)與復(fù)雜面,為讀者帶來(lái)了一百零八位在英雄個(gè)性與個(gè)人氣概上皆鮮明可指的人物群像,為中國(guó)古典小說(shuō)的人物史奉獻(xiàn)了多位特征鮮明、性格復(fù)雜、個(gè)性真實(shí)的英雄形象。
以曾是八十萬(wàn)禁軍教頭的林沖為例。林沖有正義感強(qiáng)、為人磊落光明,前期表現(xiàn)出委曲求全、忍辱負(fù)重的忍耐性格;而當(dāng)遭遇年少好友陸謙的暗算和背叛時(shí),其沉默之后的爆發(fā)主要通過(guò)暴力行為表現(xiàn)出來(lái)。在“林教頭風(fēng)雪山神廟”一回中,文本這樣描繪了林沖的反抗和報(bào)復(fù)行動(dòng):“把陸謙上身衣服扯開(kāi),把尖刀向心窩里只一剜,七竅迸出血來(lái),將心肝提在手里。回頭看時(shí),差撥正爬將起來(lái)要走。林沖按住喝道:‘你這廝原來(lái)也恁的歹!且吃我一刀。又早把頭割下來(lái),挑在槍上。回來(lái),把富安、陸謙頭都割下來(lái)。把尖刀插了,將三個(gè)人頭發(fā)結(jié)做一處,提入廟里來(lái),都擺在山神面前供桌上。”[2]82這樣的暴力書寫為有力展現(xiàn)林沖人物性格特征的復(fù)雜和多樣提供了有利的論述,也讓讀者看到了一個(gè)在逆境中反抗、在無(wú)路時(shí)爆發(fā)的烈性豹子頭形象。
(二)對(duì)敘事功能的完善
《水滸傳》暴力描寫的存在是對(duì)文本敘事功能的完善,對(duì)于推動(dòng)情節(jié)發(fā)展、體現(xiàn)文本主題有重要作用,是《水滸傳》文本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在《水滸傳》第52回“李逵打死殷天錫,柴進(jìn)失陷高唐州”[2]429文本中,柴進(jìn)遭困時(shí)試圖運(yùn)用法律公文向當(dāng)權(quán)者討公道,李逵大聲嚷道:“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李逵的話語(yǔ)體現(xiàn)出封建官府的無(wú)能與腐敗,體現(xiàn)當(dāng)時(shí)所謂“法之條例”遭權(quán)貴小人踐踏、喪失法律權(quán)威,更無(wú)須談?wù)撈淠転榘傩站S護(hù)公平、主持公道之現(xiàn)狀。在第26回“偷骨殖何九叔送喪,供人頭武二郎設(shè)祭”[2]218之后,武松為兄長(zhǎng)報(bào)仇之后受罰解押至東平府時(shí),民眾對(duì)殺了人的武松卻慷慨解囊、誠(chéng)心幫助,“這陽(yáng)谷縣,雖是小縣分,倒有仗義之人:有那上戶之家,都資助武松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松的”。民眾的價(jià)值取向和實(shí)際行動(dòng)體現(xiàn)其對(duì)為正義而施行暴力之舉的認(rèn)同及支持,這亦從側(cè)面體現(xiàn)了在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暴力是民眾爭(zhēng)取話語(yǔ)權(quán)與生存權(quán)的途徑之一。當(dāng)法律等途徑受到阻礙,暴力便成為伸張正義的唯一方法,具備了正當(dāng)性與必然性。
學(xué)者竺洪波就《水滸傳》中暴力描寫可否去除提出了觀點(diǎn):“就反映主體而言,《水滸傳》是‘英雄傳奇;就欣賞主體而言,它是一則‘底層民眾生存的神話……如果要求水滸英雄放棄暴力,等于取消了《水滸傳》的藝術(shù)本體;要求施耐庵放棄暴力描寫,則等于取消了《水滸傳》作為‘英雄傳奇的陽(yáng)剛風(fēng)格。”[3]這也說(shuō)明了暴力描寫在《水滸傳》文本中的重要意義。
總之,暴力行為的產(chǎn)生之于“水滸”時(shí)期的歷史背景具有必然性,而暴力描寫之于敘事文本的創(chuàng)作、敘事功能的實(shí)現(xiàn)則起到完善作用。
(三)美學(xué)價(jià)值的提升
1.暴力描寫的詩(shī)意賦予
《水滸傳》中的暴力描寫并非公式化、刻板化、僅一招一式之格式描繪,作者在暴力描寫時(shí)進(jìn)行了個(gè)性化的藝術(shù)處理,為暴力書寫賦予了詩(shī)意,增強(qiáng)其可讀性和藝術(shù)感。
在“血濺鴛鴦樓”一回中,武松殺人后出城,從城墻跳下后,只見(jiàn)“把哨棒一拄,立在濠邊。月明之下,看水時(shí),只有一二尺深。此時(shí)正是十月半天氣,各處水泉皆涸。武松濠塹邊,脫了鞋襪,解下腿絆,抓扎起衣服,從這城濠里走過(guò)對(duì)岸。卻想起施恩送來(lái)的包裹里有雙八搭麻鞋,取出來(lái)穿在腳上。聽(tīng)城里更點(diǎn)時(shí),已打四更三點(diǎn)。武松道:‘這口鳥(niǎo)氣… …今日方才出得松臊。”[2]246
孫紹振曾在《演說(shuō)經(jīng)典之美》中對(duì)該描寫這樣評(píng)價(jià):“殺了這么多人,逃出城了,如果是一般人物,還不趕緊溜?可是武松,居然從容到在月光下看城濠里的水,只有一二尺。看得這么細(xì)致,不愧當(dāng)過(guò)都頭,端的是,寓從容于緊迫之中……更精彩的是:‘聽(tīng)城里更點(diǎn)時(shí),已打四更三點(diǎn)。'充分寫出了聽(tīng)覺(jué)的放松,從聽(tīng)覺(jué)的放松,暗示了心情的放松;‘這口鳥(niǎo)氣終于出了。說(shuō)明在這以前,是憋著一口鳥(niǎo)氣。憋得很久,憋得很深,這樣冷峻,這樣清醒,這樣有余暇閑心。實(shí)乃水滸之大手筆也。”[4]
“月明之下,看水時(shí),只有一二尺深。此時(shí)正是十月半天氣,各處水泉皆涸。”在前段對(duì)暴力描寫后,再寫武松出城后于月明之下看水的情景,似忙亂后的偷閑,舉重若輕般,將敘述的語(yǔ)言轉(zhuǎn)向詩(shī)意化,不僅凸顯武松心中的坦蕩、正氣與磊落,也沖淡了此前殺戮描寫給予讀者的沖擊性,為暴力描寫賦予了一種特殊的詩(shī)意與美感。
2.“以惡化美”的轉(zhuǎn)換辯證
首先,“暴力”常與破壞、毀滅、血腥、殘酷等概念聯(lián)結(jié),屬于美學(xué)中“丑”的范疇,然而它也是一種審美對(duì)象,有其無(wú)法忽略的審美價(jià)值。真正的藝術(shù)不抗拒表現(xiàn)“丑”,因?yàn)樵诿缹W(xué)意義上,丑的描繪并不在于對(duì)丑的宣揚(yáng),而在于挖掘“丑”之根源與意蘊(yùn)。同樣《水滸傳》中對(duì)于暴力的描寫,也不意味著對(duì)暴力與野蠻的鼓勵(lì)與贊美,而在于表現(xiàn)暴力背后的歷史緣由與深刻意蘊(yùn)。
其次,從社會(huì)歷史實(shí)踐的根源性上看,矛盾是社會(huì)發(fā)展的基本動(dòng)力,而種種矛盾與矛盾之中必然的“不美”,則成為歷史發(fā)展的推動(dòng)力。美學(xué)家李澤厚曾在《美的歷程》中闡釋,奴隸制時(shí)代“獰厲之美”的概念,“獰厲”之態(tài)常以殘酷、野蠻的面貌呈現(xiàn),然而從審美文化上看,卻蘊(yùn)含一種關(guān)于勝利、關(guān)于強(qiáng)大的威嚴(yán)雄壯之美,“在那看來(lái)獰厲可畏的威嚇神秘中,積淀著一股深沉的歷史力量。他的神秘恐怖正是與這種無(wú)可阻擋的巨大歷史力量相結(jié)合。才成為崇高美的”[5],我們不得不承認(rèn),正是曾經(jīng)那些殘忍、血腥的“血與火的洗禮”的經(jīng)歷,才推進(jìn)了社會(huì)歷史的節(jié)節(jié)前進(jìn)和世界文明的不斷演化。
最后,從社會(huì)歷史實(shí)踐的必然性上看,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政治現(xiàn)實(shí)是朝廷無(wú)明君、民間無(wú)清官,“天”已然無(wú)法正常“行道”,世間的不平事只能由這有本領(lǐng)、有膽量、有不平之氣的一百零八人來(lái)除暴安良、“替天行道”。他們是敢于打破“壞”社會(huì)的先行者,他們戳破封建官府的黑暗本質(zhì),也激勵(lì)有力者抗?fàn)帲屓藗冊(cè)诜簽E的專制黑暗中看到了生機(jī)的存在。因此,《水滸傳》的暴力描寫,從根本上是符合人類社會(huì)的理性法則與人民內(nèi)心的感性期待的,它們正是在與“巨大歷史力量”結(jié)合的過(guò)程中,實(shí)現(xiàn)了由“獰厲”之惡化為崇高之美的歷程。
三、暴力描寫的藝術(shù)價(jià)值
《水滸傳》中的暴力描寫是歷史時(shí)刻在文學(xué)上的反映,也是對(duì)于歷史敘事的具體表現(xiàn);其從題材及內(nèi)容上對(duì)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丑惡面的描繪進(jìn)行補(bǔ)充,打破了以往文學(xué)創(chuàng)作人物性格塑造單一化局限,豐富了《水滸傳》在中國(guó)古典小說(shuō)史中的藝術(shù)貢獻(xiàn)。同時(shí),文本通過(guò)賦予暴力描寫以詩(shī)意特征,實(shí)現(xiàn)“由惡化美”的轉(zhuǎn)化,提升了作品的美學(xué)價(jià)值。
《水滸傳》中暴力描寫的藝術(shù)價(jià)值自藝術(shù)功能承接。“《水滸》作者渲染暴力場(chǎng)景,但并未葬送文明。”[6]水滸的江湖世界匪氣十足,而其氣光明勇敢;梁山的英雄制造暴力,然心間坦蕩純粹;究其本質(zhì),無(wú)能的封建官府才是暴力的最終制造者。可以說(shuō),若無(wú)對(duì)暴力的描繪,便無(wú)水滸之浩蕩江湖;在《水滸傳》中,正是通過(guò)對(duì)暴力場(chǎng)面的書寫來(lái)表達(dá)對(duì)血腥、暴力行為的否定,表達(dá)對(duì)于社會(huì)建造與民族氣質(zhì)的思考。
四、結(jié)語(yǔ)
總之,只有在對(duì)文本的體悟中完整理解暴力描寫、在對(duì)全人形象的分析中考察暴力書寫、在對(duì)事件詳情的了解中感受暴力由來(lái)、在對(duì)全面歷史背景的把握中探究暴力之必然,才能真正接近《水滸傳》中暴力描寫的實(shí)質(zhì)及其藝術(shù)功能,從而有可能對(duì)于暴力描寫產(chǎn)生“歷史的同情與審美的接受”[7]。
參考文獻(xiàn):
[1]顏翔林.第二批判:《水滸傳》的美學(xué)批判[J].浙江社會(huì)科學(xué),2009(3):93-99+128.
[2]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M].湖南:岳麓書社,1988.
[3]竺洪波.《水滸傳》的暴力描寫與美學(xué)轉(zhuǎn)換[A].胡曉明.中國(guó)文論的學(xué)術(shù)史:古代文學(xué)理論研究(第四十三輯)[C].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6:422-436.
[4]孫紹振.演說(shuō)經(jīng)典之美[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5]李澤厚.美的歷程[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
[6]王前程.怎樣看待《水滸傳》中的暴力行為[J].湖北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5(6):71-74.
[7]杜貴晨.《水滸傳》中的“血腥描寫”及其文化闡釋[J].河北學(xué)刊,2016,36(1):91-96.
責(zé)任編輯:楊國(guó)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