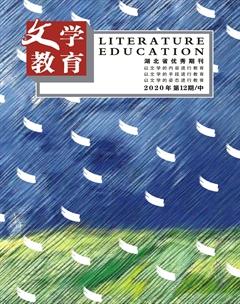空間與身份認同:論《野草在歌唱》的空間敘事
內容摘要:本文采用文本細讀的方法,分析了多麗絲·萊辛的第一部小說《野草在歌唱》中的空間意象和空間敘事,探索了空間和女性身份、自我認知的關系。囿于父權社會的性別分工和女性為“第二性”等既定價值觀的影響,主人公瑪麗在一系列空間中探尋并試圖建立自己的女性主體身份的努力均以失敗告終,并最終導致了她的悲劇結局。
關鍵詞:多麗絲·萊辛 《野草在歌唱》 空間敘事 身份認同
20世紀后期的“空間轉向”促成了空間研究和人文學科的聯姻,空間批評因而成為頗受學界關注的跨學科批評流派。在傳統的文學研究中空間被認為僅為呈現人物和推動敘事進程提供舞臺和背景,“而‘空間轉向后的空間批評則凸顯和強調空間的社會屬性和所蘊含的豐富的文化、歷史意義,重點分析文學作品中的政治、權力、身份、宗教、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等多維社會文化要素。其中文學作品中空間的身份屬性是學者們關注最多的內容。”[1]15
英國當代女作家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1919-2013)一生閱歷豐富,曾先后居住于伊朗、南羅德西亞(今津巴布韋)、英國等不同國家,因此,多樣化的地理空間對萊辛的寫作具有特殊的意義,正如盧拉·庫瓦斯(Lura Quawas)所強調的,“萊辛一直都對空間和陌生的領土感興趣,從遼闊的非洲草原到房間、房子和公寓的女性空間。”[2]112本文擬以小說的空間敘事為切入點,采用文本細讀法,深入解讀小說女主人公瑪麗的悲劇性命運。囿于既有的、二元對立的性別分工和空間區隔,瑪麗被局限于女性化的私人空間里,并默認了自己的從屬、邊緣身份,主動或被動的放棄了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最終在父權壓迫、種族主義的合力下走向毀滅。
一.童年小鎮:父母失敗的身份角色示范
《野草在歌唱》是萊辛的處女作,發表于1950年。小說從一個種族歧視引發的謀殺案開始,以倒敘的形式,追溯了白人婦女瑪麗在非洲殖民地南非的悲劇人生。瑪麗的人生歷程以空間劃分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小鎮(童年)、城市(單身)和農場(婚后),三個迥然不同的空間彼此獨立,又暗含因果關系,為瑪麗的人生奠定了灰暗、悲劇的總基調。主人公瑪麗在三個不同的空間中尋找自我,卻陷入由父權社會、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等強大的社會規范造成的泥潭中無法自救,最終精神崩潰,成為社會的犧牲品。強大的社會偏見和輿論,既定男女二元對立價值觀的影響,自身性格的被動、種族主義等等都是造成瑪麗對自我認知和身份認同出現偏差的因素。
瑪麗的童年是不幸、布滿陰霾的一段歲月。父親酗酒,無力養家,母親則啼哭悲怨,哥哥姐姐也因為貧困的家庭條件而相繼患病夭折。值得一提的是,在對瑪麗童年的描寫中,有一個不可忽視的空間意象——“店鋪”。“對瑪麗來說,這種店鋪才真正是她生活的中心,店鋪對于她甚至比對一般孩子還來得重要”[3]24店鋪對瑪麗來說具有雙重含義:一,是她生活的重心。她可以在那里買到一些生活必需品,并度過幾個小時的快樂時光;二,長大后她發現店鋪是父母爭吵的罪魁禍首,因為“店鋪就是她父親沽酒的地方。”[3]24因此,每到月底,店鋪成了一個“鐵面無情、威風凜凜送賬單來的地方。”[3]26為了這些賬單,“她的父母一年要打十二次架”[3]26關于店鋪的不愉快的記憶在幼小的瑪麗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陰影。在對瑪麗童年的刻畫中,“店鋪”這一核心空間意象是作者的一個重要敘事工具,圍繞這個中心意象,瑪麗的不幸童年生活展現在讀者面前。不僅如此,“店鋪”還陰魂不散,“尾隨”她到了婚后居住的農場:“在她兒時就威嚇著她的這種丑陋的店鋪,竟會跟著她到了這兒,甚至跟到了她的家里來。[3]86-87在瑪麗的童年和婚后生活中都出現了“店鋪”這一關鍵空間意象,可以肯定的是,這樣的前后呼應并非巧合,而是作者有意為之。關于瑪麗的童年,除了店鋪,文本中另外一個關于空間的關鍵的能指是“房子”。如萊辛所言:“房子是她作品中一個恒久的主題”[4]72關于瑪麗童年的住所,作者只用了寥寥數語描寫:“那座風吹得倒的小屋子,那屋子就像架在臺階上的小木箱似的。”[3]26房子不僅是人類生存的必需品,更具有身份屬性和社會含義。對于兒童來說,家理應是充滿美好回憶的場所,然而瑪麗家的房子像是風一吹就倒的小木箱,父母爭吵不斷,父親沒能承擔起養家糊口的重任,母親則樂于扮演哭哭啼啼的受害者角色。她在這個簡陋的房屋中所耳濡目染的種族主義思想,父親的無能形象引發的她對男人的憎惡、對婚姻的恐懼都在無形中對瑪麗的人格、價值觀起到形塑作用,也為她成年后的自閉心理和性格分裂埋下了伏筆。
二.城市:個人性格和社會期待的沖突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瑪麗的成長,故事的物理空間由店鋪林立的南非小鎮挪移到了小城。伴隨工業革命的發展,技術消除了男女兩性體力上的不平等,部分女性得以進入生產領域,擁有了經濟基礎,因而主體性得到確立。在城市這個相對平等的空間里,瑪麗憑著自己的技能得到了一個秘書職位,工作得心應手,生活平穩自由。在城市這個“相互友好而又各不干涉”[3]26的空間里,瑪麗的身份是能干、自由、獨立的職業女性,是有價值的主體。瑪麗在城市空間里的如魚得水得益于城市的疏離感。瑪麗在小城的生活空間主要有兩個,上班時在她的辦公室,做著打字、速記等雖然刻板她卻喜歡的工作;下班后回到她所居住的女子俱樂部。這兩處空間的共同特點是相對封閉,不需要與陌生人應酬,這正暗合了瑪麗內向、被動的性格特征。
瑪麗在城市里單身職業女性的身份最終證明也是最適合她的身份,然而這個身份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可是所有的女人,遲早都會意識到一種微妙而強大的壓力——結婚。”[3]32無意中聽到朋友們對她的閑言碎語對她也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瑪麗覺得自己必須找個男人結婚了。瑪麗看似一個獨立女性,但無法逃脫父權制社會對女性的角色定位——到了適婚年齡就結婚生子,回歸家庭空間。這種強大的社會規范通過朋友們的議論給瑪麗施加了巨大的精神壓力,直接影響了她對自己未來的選擇。“說到底她也是個不能脫離社會生活的人”[3]34瑪麗對于婚姻的選擇完成了父權制社會對她的角色期待,接受了社會對女性的性別定位。正如女權主義者波伏娃的觀點,城市空間雖然向女人敞開了工廠、辦公室、院系的大門,“但是,人們繼續認為,對女人來說,結婚是最體面的生涯,能使女人完全不用參與集體生活。”[5]195集體生活屬于公共空間,而公共空間是男性化的,女人則隸屬于私人空間,“家庭天使”是男權社會對女性的空間和角色定位。正如批評家羅斯所言:“女性的勞動根本上還是維持居家生活,并且由于早期的勞動分工,女人常常是和家庭及家務劃等號的。”[6]118倉促中瑪麗選擇了迪克·特納作為結婚對象。然而,兩人的個性、喜好迥然不同。瑪麗喜歡城市生活:“她喜歡這個城市,住在這里自由自在。”[3]36“迪克·特納不喜歡城市……看到這里的店鋪中擺滿了時髦女人穿用的時髦服裝和奢侈的進口食品,這使他感到不安和難受,簡直像在蓄意謀害他。”“他感到恐怖,他要逃走。所以他一到城里,總是盡快地逃回農場去,他只有呆在農場上才覺得舒適。”[3]36-37一個迷戀城市生活,另外一個只有在農場才感到舒適,兩個人仿佛天生就隸屬于兩個不同的空間,不同的世界。選擇了錯誤的伴侶,他們的結合因此注定要以悲劇收場。瑪麗的自我主體意識淡薄,盲目追求別人的認可,當她自身的身份定位與社會對女性的角色期待產生矛盾時她的選擇是屈從,這樣的選擇直接將她卷進了婚姻的桎梏。
三.農場:性別意識的困囿
英國劍橋大學地理系學者林達·麥道威爾(Linda McDowell)所著《性別、認同與地方:理解女性主義地理學》中提出了“性別化空間”,即“物理空間經常被讀作(和寫作)具有性別特征,這個世界至少被象征性地分為男性空間和女性空間。”[7]19
瑪麗的婚后生活主要圍繞農場、鐵皮屋、店鋪這三個物理空間展開。依據麥道威爾的“性別空間論”,農場廣袤無垠,無疑是公共的、生產的、男性化的空間,即瑪麗的丈夫迪克的空間;鐵皮屋和店鋪則是閉塞的、私人的、女性化的空間,即屬于瑪麗的空間。在涇渭分明的空間中,瑪麗試圖找尋和建構自己的主體身份,均以失敗告終。
婚后的瑪麗生活在農場。讀者目睹了在鄉下農場這片廣袤無垠的空間里,瑪麗是怎樣一步步從開始的滿懷希望,到精力耗盡,希望破滅,直到最后的精神崩潰,陷入與黑人摩西的感情糾葛,直至被其殺害。鐵皮小屋是瑪麗到達農場后的第一個落腳點,但小屋給她的第一印象不是能給人帶來歸屬感的溫暖家園,卻是“緊閉的、漆黑的、窒悶的”[3]44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空間生產》中指出:“房屋因為具有人性(與人類相關,人的居住),其意義如宇宙般廣闊,從地窖到閣樓,從地基到屋頂,既充滿夢想又不乏理性,既是活生生的現實又是美妙的天堂,家庭與自我的關系近乎具有了身份屬性。”[8]121壓抑的鐵皮屋是是屬于瑪麗的空間,其暗淡、窒悶,因此也預示了瑪麗看不到希望的未來。
從城市到農場的空間的轉換,從單身職業女性到為人妻的角色轉換并沒有帶來美好生活的希望,反而使瑪麗覺得自己在重復母親的悲慘命運。即使是在房子這個貌似專屬瑪麗的女性空間里,她的發言權也少得可憐。關于房屋修整、家庭生活,生兒育女,這些發生在屬于女性的空間的房屋里的事情,作為家庭主婦的瑪麗卻處于失語、附屬的地位,毫無發言和決定的權力,這是迪克固執的性格和男權思想合謀的結果,改變自己的人生無望,瑪麗的精神就這樣一步步走向崩潰,最終釀成慘劇。
在漫長的成長歲月中,女性對自我的認知和身份的認同早就打上了父權社會的烙印,并內化為女性的自覺無意識。因此,瑪麗雖然對農場、店鋪、乃至迪克本人都心存不滿,卻極少抗爭,“現在一想起迪克,她腦子里就聯想起自己童年時代的灰暗和悲慘,那簡直就好像同命運本身爭辯一樣。”[3]88事實上嫁給迪克后瑪麗有過一次同命運的“爭辯”:她曾試圖悄悄逃回城里,結果發現女子俱樂部不接受已婚婦女,她原來的工作崗位也早已被他人取而代之。唯一一次同命運和自己的身份抗爭的努力以失敗告終。對于瑪麗來說這是致命的大潰敗,因為“這是她內心崩潰的開始。起初只是一種感覺上的麻木,好像她從此再也沒有知覺,再也不能奮發有為了。”[3]96
在小說中,農場是完全男性化的空間,是迪克的領域。困囿于對自我的定位,瑪麗自覺的認為農場事物應歸于迪克管理,她希望他成為一個有主見、有能力的堅強男人,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成功。“如果他的意志力確實比她強,并因此真的占了她的上風,那她一定會愛她,也絕不會再怨恨自己所遇非人。”[3]120瑪麗對于自我“他者”身份的認定,既是因為長期浸淫于強大的父權制文化氛圍中,耳濡目染,接受并成為自己的無意識,也是家庭環境的影響以及個人性格等因素綜合作用的必然結果。
“地理空間的敞開與封閉往往隱喻了人際關系的親疏,也反映了女性個體對空間的自我認知”[9]758自家農場是一個敞開的、開放的空間,瑪麗本來可以隨意進入。但她封閉的個性將其終日困于鐵皮屋中,對于農場以及相關的一切不僅毫無興趣,甚至有恐懼之感。“雖然在這兒生活了這么久,可是一想起四周荒涼的草原和出沒在草原上的野獸,以及那些發出奇怪鳴叫的鳥兒,她仍然感到驚恐。”[3]154-155草原、野獸、樹叢對于瑪麗來說是充滿敵意的空間和事物,心理層面的生疏和情感層面的對立暗示了瑪麗對農場的疏離之感,農場不是屬于她的空間。
四.結語
“真正會表現空間的小說家決不胡亂描寫空間,他們筆下的空間總是要在敘事中起作用的……他們不僅僅把空間看作故事發生的地點和敘事必不可少的場景,而是利用空間來表現時間,利用空間來安排小說的結構,甚至利用空間來推動整個敘事進程。”[10]95空間或代表空間的意象不再僅僅是為故事發展提供的空洞的物理空間,更起到了表征人物內心世界,表述人物對自我的認知、身份的認同的作用,并因此積極參與文本主題意義的建構。正是通過這種獨具匠心的空間敘事策略,作者為廣大讀者構建出了一幅殖民地時期南非窮苦白人凄慘生活的畫面,對白人中的弱勢邊緣群體——白人女性的命運給予格外關照,彰顯了作家一貫堅持的社會責任感和對邊緣群體的人文關懷。
參考文獻
[1]Gilian Rose. Feminism and Geography[M]. HongKong: Polity Press, 1993.
[2]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M].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6.
[3]Quawas, R.: “Lessings ‘To Room Nineteen: Susans Voyage into the Inner Space of ‘Elsewhere”[J]. Atlantis? (1): 112, 2007.
[4]William E.Cain. Between the Angle and the Curve: Mapping Gender, Race, Space and Identity in Willa Cather and Toni Morrison[M]. London: Routledge, 2006.
[5]多麗絲·萊辛.野草在歌唱[M]. 一蕾,譯. 南京:譯林出版社,2008.
[6]杜洪晴. 解讀《神諭女士》中的女性空間敘事[J]. 沈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12): 758-762.
[7]姜仁鳳.《野草在歌唱》中的房子與自我[J]. 外國文學研究,2017(3): 71-77.
[8]龍迪勇. 空間敘事學[M].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9]吳慶軍. 英國現代主義小說空間書寫研究[M]. 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6.
[10]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 鄭克魯,譯.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作者介紹:趙琪,浙江工業大學之江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英語語言文學,教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