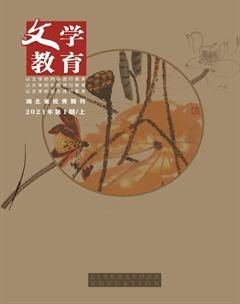從精神生態(tài)學(xué)視角解讀《柏林,亞歷山大廣場(chǎng)》
羅曼
內(nèi)容摘要:德布林的代表作《柏林,亞歷山大廣場(chǎng)》 是一部關(guān)于世界大都會(huì)——柏林的小說(shuō)。它通過(guò)大量的數(shù)據(jù)和新聞報(bào)道式的寫(xiě)實(shí)把一個(gè)既充滿(mǎn)魅力,又充斥著丑惡的現(xiàn)代大都會(huì)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本文從精神生態(tài)學(xué)視角切入,對(duì)工業(yè)社會(huì)中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之間逐漸疏離乃至對(duì)立的狀況進(jìn)行探討,揭示工業(yè)社會(huì)的異化現(xiàn)象和人失去自我的嚴(yán)重精神危機(jī),進(jìn)而思考當(dāng)下的生態(tài)問(wèn)題,反思人類(lèi)自工業(yè)革命以來(lái)的發(fā)展道路。
關(guān)鍵詞:生態(tài)批評(píng) 精神生態(tài) 城市 異化
阿爾弗雷德·德布林(1878-19
57)不僅是享有世界聲譽(yù)的現(xiàn)代德語(yǔ)經(jīng)典作家,而且憑借其對(duì)德語(yǔ)文學(xué)的杰出貢獻(xiàn),成為國(guó)際公認(rèn)的語(yǔ)言大師和文壇巨匠。其最為著名的小說(shuō)是1929年發(fā)表的《柏林,亞歷山大廣場(chǎng)》。這部小說(shuō)標(biāo)志著德布林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頂峰,體現(xiàn)了內(nèi)容和形式,思想性和藝術(shù)性的完美結(jié)合,是德國(guó)文學(xué)史中第一部重要的大都市長(zhǎng)篇小說(shuō)。小說(shuō)的主人公弗蘭茨畢勃科普夫從監(jiān)獄釋放后來(lái)到大都市柏林,他決心開(kāi)始新的生活,但他最終沒(méi)能戰(zhàn)勝?gòu)?fù)雜而險(xiǎn)惡的人際關(guān)系和社會(huì)環(huán)境,自己的愛(ài)人也沒(méi)能逃過(guò)被殺害的命運(yùn)。在小說(shuō)的結(jié)尾,舊的弗蘭茨在與死神的搏斗中得到徹悟,迎來(lái)了新生。
德布林創(chuàng)作生涯前期的許多作品都體現(xiàn)了他對(duì)人與自然關(guān)系問(wèn)題的思索,在小說(shuō)《柏林,亞歷山大廣場(chǎng)》中也涉及了很多關(guān)于自然和人文方面的描述,顯現(xiàn)了現(xiàn)代文明下精神生態(tài)危機(jī)的普遍性。本文將從精神生態(tài)學(xué)的角度,對(duì)《柏林,亞歷山大廣場(chǎng)》中體現(xiàn)的精神生態(tài)下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的關(guān)系進(jìn)行分析,探討小說(shuō)中隱含著的豐富的精神生態(tài)思想。
一.精神生態(tài)下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
20世紀(jì)20年代的柏林城是小說(shuō)故事發(fā)生的背景,也是主人公畢勃科普夫特被迫登上的“戰(zhàn)場(chǎng)”。在柏林,畢勃科普夫走完了一條“通向徹底清除、消滅和摧毀的道路”[1]。德布林筆下的柏林是一座現(xiàn)代工業(yè)化的城市,同時(shí)也充斥著混亂和犯罪。酗酒、賣(mài)淫、兇殺和斗毆的新聞屢見(jiàn)不鮮。變幻無(wú)常的大都市令剛邁出監(jiān)獄大門(mén)的畢勃科普夫感到陌生和不安。
人們的物質(zhì)生活水平隨著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的進(jìn)步而不斷提高,卻也因此打破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tài)平衡,觸發(fā)了各種生態(tài)問(wèn)題。在《柏林,亞歷山大廣場(chǎng)》這部小說(shuō)中,主人公畢勃科普夫所處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非常惡劣。亞歷山大廣場(chǎng)上巨大的打樁機(jī)和水泥機(jī)在視覺(jué)上帶給人的壓迫感,以及它們?cè)趫?zhí)行工作時(shí)伴隨著的震耳欲聾的聲音,都營(yíng)造出不安和令人恐懼的氛圍。這種不安和恐懼讓弱小的人們更加感到心靈枯竭。城市的建設(shè)破壞了舊有的生存環(huán)境,現(xiàn)代工業(yè)席卷著城市生活中的每一個(gè)人,打樁機(jī)和水泥機(jī)摧毀著人們的個(gè)性和私人空間。
關(guān)于畢勃科普夫之前的歷史,小說(shuō)中只用了少量筆墨,通過(guò)這些只言片語(yǔ)讀者可知,他作為前線(xiàn)戰(zhàn)士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首先是在戰(zhàn)壕里,在普魯士軍隊(duì)那里,然后在特格爾。我已經(jīng)不再是個(gè)人。”[2]戰(zhàn)爭(zhēng)對(duì)畢博科普夫的精神造成了創(chuàng)傷。對(duì)于有創(chuàng)傷經(jīng)歷的畢博科普夫來(lái)說(shuō),大城市的環(huán)境不斷觸發(fā)他慘痛的記憶,帶來(lái)的后果是更加強(qiáng)化的心理創(chuàng)傷。[3]對(duì)于剛刑滿(mǎn)釋放的畢博科普夫而言,他還不能適應(yīng)大城市的新興事物,比如,在小說(shuō)中,畢博科普夫?qū)Π亓帧半S時(shí)會(huì)倒塌”的出租房的屋頂感到深深的恐懼,“屋頂是在房子上的,漂浮在房子上,他的眼睛迷惑地往上看著:但愿這些屋頂不會(huì)滑下來(lái),但是房子是直直地立著的。我這可憐的魔鬼應(yīng)該到哪兒去。”[4]這些屋頂一次次地喚醒了從戰(zhàn)爭(zhēng)中歸來(lái)的主人公的創(chuàng)傷。作為大城市的底層民眾,畢勃科普夫在現(xiàn)代生活中是迷茫的,沒(méi)有歸屬感的,他像一頭野獸一樣在急促而混亂的城市中橫沖直撞。
從自然環(huán)境來(lái)看,主人公穿行在雜亂喧囂、高樓林立的大都市柏林,與孤獨(dú)、異化、墮落為伍。現(xiàn)代都市的的壓迫感使人變得麻木、精神質(zhì)、無(wú)所適從。這也就為弗蘭茨·畢勃科普夫終究要面對(duì)的“命運(yùn)之擊”和人格異化埋下了伏筆。
二.精神生態(tài)下人與人的關(guān)系
精神生態(tài)的異化不僅體現(xiàn)在周?chē)h(huán)境對(duì)人的壓迫威脅,還體現(xiàn)在人際關(guān)系的緊張畸變。小說(shuō)處處揭示著人與人之間感情的淡漠與缺失。
在與女性的交往中,畢勃科普夫常常訴諸于暴力,表現(xiàn)出極端的自大。他更是將女性物化為自己的“附屬品”,其行為完全受欲望所支配,因此,他對(duì)待女性常常顯露出極端的情緒。即便對(duì)待最?lèi)?ài)的女友米澤,畢勃科普夫依然持一種蔑視的不平等態(tài)度。他曾在盛怒之下打死了另有所愛(ài)的妻子伊達(dá),并因此進(jìn)了監(jiān)獄。出獄后,他并未吸取教訓(xùn),而是強(qiáng)暴了伊達(dá)的妹妹米娜。他并未對(duì)此有任何悔過(guò),反而因此獲得了自信,感到幸福和狂喜。
雖然畢勃科普夫十分寵愛(ài)米澤,米澤也十分忠誠(chéng),兩人相處甚好,但是,當(dāng)畢勃科普夫得知米澤曾經(jīng)對(duì)其他男人有過(guò)愛(ài)慕之情后,便對(duì)她大打出手,“弗蘭茨猛地轉(zhuǎn)過(guò)身來(lái),照著她臉上打去……他緊接著撞擊她的肩膀,她倒了下去,他騎在她的身上,他的兩只手在她的身上亂抽……她坐在那里,身上的襯衣已經(jīng)撕破,一只眼睛已經(jīng)睜不開(kāi)了,血從鼻子里流了出來(lái),左臉和下巴沾滿(mǎn)了血。”[5]畢勃科普夫仿佛一只不受控制的野獸般粗魯沖動(dòng),對(duì)女性的暴力實(shí)際上滿(mǎn)足了他成為“征服者”的夢(mèng)想。作為處在柏林社會(huì)底層的無(wú)產(chǎn)者,畢勃科普夫的傲慢和自負(fù)在充滿(mǎn)敵意的社會(huì)面前不斷地受到打擊。在以男性為主的競(jìng)爭(zhēng)叢林中畢勃科普夫顯然是無(wú)能和失敗的,他所缺失的男性尊嚴(yán)只能通過(guò)體力上的優(yōu)勢(shì)來(lái)彌補(bǔ)。
面對(duì)男性,畢勃科普夫試圖用狂妄放肆的態(tài)度來(lái)掩飾自己的怯懦。他向呂德斯炫耀自己的拳頭和肌肉,并且吹噓自己和一個(gè)寡婦偷情。然而,肉體上的強(qiáng)壯并不能掩飾精神上的孤獨(dú)。他明明知道是呂德斯欺騙了他,卻選擇逃避和沉默的方式對(duì)抗;他明明知道自己的殘廢是萊因霍德所致,卻不去告發(fā)他,在埃娃和赫爾伯特的追問(wèn)下仍不敢開(kāi)口。畢勃科普夫仿佛將自己囚禁在一只鐵箱中,不讓任何人靠近。當(dāng)赫爾伯特和埃娃要為他伸張正義時(shí),他卻以手臂也不會(huì)因此長(zhǎng)出來(lái)為由拒絕,甚至把自身所遭受的不幸視作命運(yùn)的“懲罰”。正是由于畢勃科普夫怯懦逃避、聽(tīng)天由命的生活觀(guān),促使萊因霍德對(duì)他施加更為肆無(wú)忌憚的欺凌。最終,萊因霍德殺死了畢勃科普夫的女友米澤,并設(shè)法嫁禍于他。這次打擊終于使畢勃科普夫的精神世界徹底崩塌。
三.異化了的自我——一個(gè)盲目、無(wú)意識(shí)的主體
德布林以無(wú)序荒誕的大都市作為社會(huì)圖景,通過(guò)展現(xiàn)主人公的日常生活狀態(tài)和心理活動(dòng),塑造了一個(gè)盲目的、喪失了意識(shí)的異化主體。
主人公畢勃科普夫是一個(gè)“無(wú)意識(shí)”的典型。德布林在書(shū)中多次將畢勃科普夫比作動(dòng)物,他的無(wú)知和盲目使他的行為不受意識(shí)的支配,顯得被動(dòng)而魯莽。首先,他在小說(shuō)中被比喻為成年野獸。他的傲慢和優(yōu)越感來(lái)自他對(duì)自己軀體的關(guān)注:“我這個(gè)人什么都不怕。我有兩只拳頭。看哪,我的身上長(zhǎng)著什么樣的肌肉。”因?yàn)椤案ヌm茨有的是肌肉”,所以使用暴力成為他解決問(wèn)題時(shí)唯一引以為傲的手段。他對(duì)自身肉體的自信令他具有雄性動(dòng)物一般的攻擊性,處處想彰顯自己力量上的強(qiáng)大。此外,畢勃科普夫的傲慢和自負(fù)還體現(xiàn)在對(duì)待政治的態(tài)度上。他接觸過(guò)各種團(tuán)體和派別的思想,但他的頭腦一片混亂,無(wú)法明確自己的政治信仰。在他眼里,只有他自己才是世界上建立秩序的人。他的這種觀(guān)點(diǎn)完全是建立在對(duì)世界一無(wú)所知的基礎(chǔ)上,是沒(méi)有理性可言的。
然而,與其魁梧強(qiáng)壯的外表和盲目的自信相對(duì)的是畢勃科普夫脆弱孤僻的內(nèi)心世界。這里,他又被比喻為“蛇”,比如,小說(shuō)中描寫(xiě)畢勃科普夫失去米澤后孤獨(dú)頹然的形象:“……孤零零的弗蘭茨畢勃科普夫,雖然有些搖晃,但畢竟是在走路。你們看哪,那條眼鏡蛇,它在爬行,它在跑動(dòng),它受到了傷害。”[6]以及:“我們的弗蘭茨·畢勃科普夫,這條眼鏡蛇,這位鋼鐵般的斗士,孤獨(dú)地、非常孤獨(dú)地坐著。”[7]褪去外表的偽裝之后,他是一個(gè)孤立于人群,并且與身處的時(shí)代脫節(jié)的弱者,渾渾噩噩生活著的畢勃科普夫顯然與日新月異的大都市格格不入。在面對(duì)命運(yùn)的沉重打擊時(shí),畢勃科普夫?qū)θ怏w的自信變得不堪一擊,他的內(nèi)心完全沒(méi)有能力對(duì)抗“命運(yùn)之擊”,唯一能給予他歸屬感的的地方是他經(jīng)常逗留的羅森塔爾廣場(chǎng)旁的小酒館。
四.結(jié)語(yǔ)
小說(shuō)《柏林,亞歷山大廣場(chǎng)》展現(xiàn)了主人公畢勃科普夫從盲目、無(wú)知到冷靜、理性的轉(zhuǎn)變歷程,反映了作者對(duì)現(xiàn)代文明下人類(lèi)生存現(xiàn)狀的關(guān)注和憂(yōu)慮。小說(shuō)通過(guò)展示一幅精神生態(tài)下人與自然、 人與人以及人與自我的生態(tài)不和諧畫(huà)面,警示我們?cè)谖镔|(zhì)生活不斷豐富的今天,我們更加不能忽視精神生態(tài)的平衡,應(yīng)樹(shù)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態(tài)意識(shí),追求人類(lèi)自身精神的成長(zhǎng)。
參考文獻(xiàn)
[1][德]阿爾弗雷德·德布林.柏林·亞歷山大廣場(chǎng)[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
[2]余星.從生態(tài)批評(píng)視角解讀譚恩美的《喜福會(huì)》[J].上海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8,40(2).
[3]魯樞元.文學(xué)的跨界研究:文學(xué)與生態(tài)學(xué)[M].上海:學(xué)林出版社,2010.
[4]吳曉群.伊恩·麥克尤恩筆下的精神生態(tài)荒原[J].懷化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8,37(3).
[5]劉小楓.詩(shī)化哲學(xué)[M].濟(jì)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87.
[6](德)Michael Ostheimer李雙志譯.創(chuàng)傷、城市與回憶———以阿爾弗雷德·德布林的《柏林亞歷山大廣場(chǎng)》和W·G·澤巴爾德的《奧斯特爾里茨》為例[J].德語(yǔ)人文研究,2013,1(2).
[7]馬嫽.城市空間中的犧牲者:《柏林,亞歷山大廣場(chǎng)》中的暴力隱喻[J].外國(guó)語(yǔ)文,2016,32(6).
[8]羅煒.評(píng)《柏林,亞歷山大廣場(chǎng)》——德布林哲學(xué)思想的演繹[J].外國(guó)文學(xué)評(píng)論No.4,1993.
[9]付昌玲.城市中的荒原———生態(tài)批評(píng)視角下的《水泥花園》[J].浙江工商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7,3.
注 釋
[1][德]阿爾弗雷德·德布林.柏林·亞歷山大廣場(chǎng)[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第498頁(yè)。
[2][德]阿爾弗雷德·德布林.柏林·亞歷山大廣場(chǎng)[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第14頁(yè)。
[3](德)Michael Ostheimer|李雙志譯.創(chuàng)傷、城市與回憶———以阿爾弗雷德·德布林的《柏林亞歷山大廣場(chǎng)》和W·G·澤巴爾德的《奧斯特爾里茨》為例.德語(yǔ)人文研究,2013,1(2); 6-7.
[4][德]阿爾弗雷德·德布林.柏林·亞歷山大廣場(chǎng)[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第225頁(yè)。
[5][德]阿爾弗雷德·德布林.柏林·亞歷山大廣場(chǎng)[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第411頁(yè)。
[6][德]阿爾弗雷德·德布林.柏林·亞歷山大廣場(chǎng)[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第216頁(yè)。
[7]同上,第356頁(yè)。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