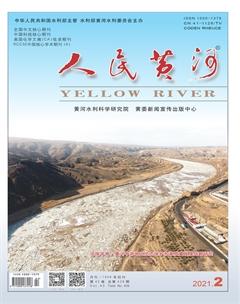黃河中游地區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研究
任保平 杜宇翔
摘 要:黃河中游地區是我國重要的農牧業和能源生產基地,也是文化資源豐富地區。黃河流經中游地區的黃土高原核心區域,該區域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環境脆弱,是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進程中需要解決的難題。分析了黃河中游地區的地貌特征、氣候環境特點、水土環境和經濟發展基本狀態,以及存在的水資源供需矛盾、水土流失、環境污染、管理機制矛盾和公眾參與治理不足問題等。從推進綠色發展、注重協同發展、促進產業發展、加強共建共享、弘揚黃河文化和加快城市群建設六個層面做出了戰略設計。提出黃河中游地區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新格局的實現路徑,即加強頂層設計、完善生態保護治理機制、創新管理體制、構建新發展格局和深化市場化改革等。
關鍵詞:綠色發展;生態保護;高質量發展;新格局;黃河中游
Abstract:The Middle Yellow River is an important agricultural and energy production area in China and it also has rich culture. However, the Yellow River flows through the Loess Plateau, where has serious soil erosion and fragile ecology. It poses a serious challenge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d the geographical feature, climate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soil and water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status of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As well as,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water supply and demand, soil erosion, pollu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imperfect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n, the strategy design was made from six aspects including promoting green development, construct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promot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rengthening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promoting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and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city groups. Finally, a bracing system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op-level design, improving water control mechanisms, innovating governance, constructing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promoting market-oriented reforms was established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It was expected that this paper could lay a certain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foundation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Yellow River.
Key words: green development; ecological protec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w pattern; Middle Yellow River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重大國家戰略,為我國中西部發展描繪了發展路線。“共同抓好大保護,協同推進大治理”的戰略思路,體現了新型區域發展理念,即綠色發展和協調發展理念。目前黃河流域生態脆弱、環境污染嚴重,這要求必須擺脫傳統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以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為抓手,落實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本研究中“黃河中游地區”指內蒙古、陜西、山西、河南4個省(區),黃土高原的核心區位于其中,該核心區是黃河流域生態保護的重點區域。
1 黃河中游地區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狀態
黃河中游是從內蒙古托克托縣河口鎮至河南省鄭州市桃花峪的河段,該河段長1 206 km,流域面積34.4萬 km2,約占全流域面積的45.7%。該地區是我國重要的農牧業和能源生產基地,也是文化資源豐富地區,但存在水土流失嚴重、生態脆弱等問題。
1.1 主體功能區劃分和地貌特征
黃河是我國主體功能區戰略落實的重要載體,根據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以及中游的區位特征、生態特征和環境承載能力,對黃河中游地區大致進行如下劃分:黃河中游的黃土高原大部分區域屬于限制開發區域,陜西渭河谷地和陜南漢中地區屬于重點開發區域,黃河中游的副省級中心城市和發展已經較成熟的地市級中心城市屬于優化開發區域(包括西安、太原、鄭州等中心城市)[1]。黃河中游地貌特征空間差異大且支流眾多,水土流失嚴重導致大多地區表現為地形破碎的侵蝕地貌,流域內有平原區、高原區、丘陵區以及溝壑區等[2]。
1.2 氣候環境特點
黃河中游地區屬于中溫帶和暖溫帶半干旱區,該地區的氣候環境特點是:降水從西北向東南逐漸增加,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并以暴雨的形式為主。黃河中游地區冬春干旱,夏秋多雨,其中6—9月的降水量約占全年降水量的70%,7—8月的降水最盛,可占全年降水總量的40%以上;冬冷夏熱,四季分明,全年日照百分率在50%~75%。據統計,陜北地區多年平均大風日數在30 d以上,沙暴日數和揚沙日數較多,近年來隨著生態的恢復揚沙和沙暴天氣日數有所減少。可以說,氣候環境條件是導致黃河中游地區水資源匱乏和生態脆弱的重要因素。
1.3 水土環境情況
黃土高原是世界上土壤侵蝕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其中黃土丘陵溝壑區和黃土高塬溝壑區面積約為25萬 km2,又是黃土高原地區水土流失最為嚴重的地區。易蝕松散的黃土物質、植被覆蓋率低和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是造成黃土高原嚴重土壤侵蝕的重要原因[2]。早在20世紀50年代,我國就開始對黃土高原進行生態治理,水土保持理論研究和治理實踐也取得一定成效。20世紀60年代以來旱作梯田、林草種植和淤地壩建設等大規模生態工程實施,1999年以來退耕還林還草的開展,以及自然因素如氣溫升高、降水減少等,使得黃河中游地區的水土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目前,黃河中游地區尤其是黃土高原水土流失仍然嚴重,生態環境脆弱。
1.4 經濟發展基本狀態
黃河中游地區是我國重要的經濟區域之一,該區地域遼闊、物產豐富,是我國重要的能源生產基地,也是農牧業經濟生產的重點區域,盛產小麥、谷物、棉花、畜牧產品等。畜牧業主要分布在內蒙古中西部和陜北地區,農產品生產主要在中游南部的汾渭盆地和關中平原。黃河中游地區的礦產資源豐富、品種齊全,煤炭、石油、天然堿等的儲量在全國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別是煤炭資源尤為豐富,原煤產量多年來占全國總產量的40%以上,是我國重要的煤炭生產基地和以煤炭為原料的電力、化工工業的重要生產基地。2019年,黃河中游經濟區的GDP約為11.43萬億元,約占全國GDP的11.5%。
2 黃河中游地區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面臨的問題
黃河中游地區的經濟發展主要依靠農牧業生產和能源開發,長期以來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模式對生態環境產生不利影響。水資源短缺、水土流失嚴重、生態脆弱、環境污染等成為黃河中游地區潛在生態風險。
2.1 水資源供需矛盾的限制
黃河的水資源總量有限且人均占有量低,水資源總量不到長江的7%,人均占有量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27%,但流域水資源開發利用率卻高達80%,遠遠超出了國際上公認的40%的警戒線[3]。隨著太原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等城鎮化進程加快和工業化發展提速,黃河中游地區的用水需求還會繼續增長,未來發展進程中所面臨的水資源短缺的壓力會持續增大。水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是黃河中游地區高質量發展中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與此同時,黃河中游地區還存在水資源利用粗放、工農業用水效率低等問題。黃河水資源總量供需矛盾明顯,據2019年《黃河水資源公報》,該年黃河流域的用水中農田灌溉用水總量占比高達67.8%,工業生產用水總量占比9.3%,生活用水總量占比6.0%,而生態用水總量占比僅僅為10.1%。可見,黃河流域農業用水量較大、生態用水量較小,導致流域內生態修復能力較弱。
2.2 水土流失的制約
黃河多年平均年輸沙量達16億 t,而平均年徑流量較小,水沙關系不協調[4]。截至2018年年底,黃河流域累計治理水土流失面積27.5萬 km2,水土流失問題得到了改善。根據2019年全國水土流失動態監測結果,黃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積占流域土地面積比例最大,為33.25%;中度及以上水土流失面積占水土流失總面積的比例最大,為37.39%。黃土高原地區植被建設、生態工程建設等體制機制仍需進一步完善[5]。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能不能種樹,種什么樹合適”,哪些地方“要大力建設旱作梯田、淤地壩”,哪些地方“要以自然恢復為主”等問題尚未得到解決[3]。隨著黃河中游地區城鎮化進程的加快等,人為水土流失防治任務更加艱巨。
2.3 環境污染的制約
傳統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給黃河中游地區帶來了嚴重的生態環境污染,并且該區域植被覆蓋率低、環境承載力弱,導致生態治理難度增大[6]。如陜北重工業區域污染物的擴散轉移給周邊區域乃至中下游,造成嚴重的生態環境污染溢出效應[7]。同時,較低水平的環境規制會導致資源開采與土地財政擴張,也會加劇環境污染效應[8]。《2019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在黃河流域監測的137個水質斷面中,Ⅰ~Ⅲ類水質斷面占73.0%,比2018年上升6.6個百分點;劣Ⅴ類占8.8%,比2018年下降3.6個百分點,但仍在全國平均水平之上。其中,黃河干流水質為優,主要支流為輕度污染,主要污染指標為氨氮、化學需氧量和總磷,黃河流域整體仍屬于輕度污染。
2.4 “九龍治水”亂象難以在短時間內徹底消除
我國對水資源實行的流域管理和行政區域管理相結合的管理體制在理論上能夠實現資源的高效管理,但在實際工作中會出現條塊分割的問題和“九龍治水”亂象,管理主體權責不清,導致管理效果不佳。胡鞍鋼等[9]在黃河水利委員會的調查表明,在流域治理中干部評價最大的矛盾是部門沖突,其次為沿黃省(區)間的矛盾。2020年年初,水利部成立了推進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工作領導小組,有效建立了中央統籌的工作機制,但其在實際運行中和地方的配合情況還有待觀察。當前存在的“九龍治水”亂象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黃河流域整體的治理能力不強。
2.5 公眾參與治理不足
公眾參與公共資源治理,既是公民應有的權利,也是實現環境治理的重要途徑[10]。我國自2019年起開始實行生態環境部發布的《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辦法》,體現了政府對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重視。但是,參與機制不完善、公眾缺乏經驗,導致實行過程中出現許多問題。社會公眾參與的不足與流域管理機構是一個封閉系統有關,流域管理機構關注自身與社會的聯系較少,造成了政府對流域的壟斷管理。這也與地方政府在流域治理中未做好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等有關。在這種情況下,公眾參與的范圍和深度都會受到限制,導致政府和公眾之間協同乏力。同時,公眾參與治理不足也與民眾對政府的依賴有關,部分民眾缺乏主動向政府部門反映環境污染問題的意識。
3 黃河中游地區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新格局的戰略設計
結合黃河中游地區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狀態和存在問題,發現該地區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因此,需要從流域治理的整體層面入手,統籌經濟增長和生態保護的協調發展。從“共同抓好大保護、協同推進大治理”的戰略思路出發,以綠色發展開辟黃河中游地區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新格局。
3.1 推進綠色發展
綠色發展是開辟黃河中游地區發展新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該地區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導向:一是構建生態保護機制。首先,要求政府完善生態保護相關法律法規,設立地方政府生態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考核標準,根據區位及自然稟賦特征等建立差別化的考核機制;其次,要加強社會宣傳教育,轉變人的發展意識,從之前的“先污染、后治理”轉變為“生態優先”;最后,倡導綠色消費,改變消費主體的消費理念,形成良性互動的綠色消費機制。二是建立生態優先型經濟發展方式。在加快生態修復的同時,要持續優化能源結構、用水結構、用地結構等,打造生態優先型經濟發展方式,引導煤炭生產等能源行業以技術、綠色、智能化為發展方向,把發展生態優先型經濟作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模式、開辟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抓手。三是培育綠色產業。首先,要提高煤炭等傳統工業對資源的循環高效利用,加強資源節約技術的引進和研發,提升行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同時要加快資源的回收體系建設以實現資源的循環利用;其次,要加快形成新型能源節約型產業,加快新舊動能轉換,培育新型產業主體,為綠色產業發展奠定基礎;最后,要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優化市場環境,推廣能源管理新機制,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為推動綠色產業發展提供重要支撐。
3.2 注重協同發展
協同發展是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促進黃河中游地區高質量發展,要注重問題導向,堅持生態和經濟協同發展,主要包括以下三點:一是目標協同,即協同推進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實施重大國家戰略要科學設計,不但要解決黃河中游地區的生態問題,而且要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統籌協調好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制定生態、經濟、社會互相協同的發展目標,堅持生態保護、經濟發展、社會進步齊頭并進。二是機制協同。應打破現行區域管理機制,在保證流域發展整體性和協調性的基礎上,堅持中央統籌、省(區)負總責、市縣落實的組織機制,建立跨區域協調機制,落實各省(區)和有關部門主體責任,強化流域內水環境保護修復聯防聯控機制,促進流域內經濟社會發展與水資源開發利用的平衡[11]。三是河江聯動。與長江經濟帶相比,目前黃河流域在整體實力、城市群發展、中心城市實力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在實現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起步階段,應鼓勵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學習先進經驗并加強合作,在產業轉移、產業分工等方面形成緊密聯系,打造河江聯動的良好局面,增強長江流域對黃河流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引導和帶動作用。
3.3 促進產業發展
創新是產業發展的永續動力,也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因素。目前,全球范圍內的數據革命、產業革命正在加速演進,“創造性破壞”現象正在不斷涌現。黃河中游地區的產業發展根據現階段基本狀況應進行如下戰略設計:一是科技創新。《2019年中國、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五局發明專利統計分析報告》顯示,2019年西安市、太原市、鄭州市獲得的國家發明專利數量分別為9 023、1 732、2 866項,西安市的數量遠遠大于鄭州市和太原市的,但其與我國東南沿海的重要中心城市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推動科技創新需要做好中長期規劃,還應將科技創新成果運用于流域發展,建立生態化、系統化、多維度創新體系[12],進一步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二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要以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作為支撐,實現技術升級、能源結構改善,通過新技術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和產業的生態效率。推動工業產業的建設升級,加快煤炭等能源型行業的環境保護能力建設,實現資源型產品的循環利用。大力發展節水產業和節水技術,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13]。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大力發展商業飲食業、物流業等。三是培育新興產業。培育以信息、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核心要素的信息服務產業,構建黃河中游地區信息服務產業體系和人工智能產業體系,加快建設新經濟產業園,吸引資金、技術和人才流入。
3.4 加強共建共享
加強共建共享,要做到共建與共享的辯證統一,既追求共同享有,也要求共同參與:一是構建多元化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要為流域公共產品供給建立多元化、多途徑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同時建立橫向利益分享機制。二是強化企業主體在生態保護中的作用。政府要引導企業主體制定綠色發展戰略,以有效應對外部市場環境的變化,并使企業間的競爭處于良性的動態平衡,還應引導企業建立管理新機制。同時,政府要引導社會資金進入生態保護產業,如可適度將重大生態建設工程承包給企業等。三是完善公眾參與制度。目前,公眾參與制度在信息公開等方面存在缺陷,只有加以改正,公眾才能有效參與政策實施等[14]。要將公眾參與的范圍擴大并進行分類管理,落實信息公開與公民參與的便利化等。總之,要讓公眾參與成為黃河中游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3.5 促進生態、經濟、文化協同發展
黃河流域有歷史悠久且豐富的文化,是我國早期文明的主要誕生地。在開辟黃河中游地區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新格局中要彰顯黃河文化魅力、突出黃河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一是要加強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延續歷史文脈。二是要深入挖掘黃河文化的時代價值。發展區域文化產業、打造文化企業品牌、實施文化建設工程等;同時,要推動文化弘揚和生態旅游開發深度融合,以文化促進旅游產業發展。三是打造新型文化產品。打造“互聯網+文化遺產”“智能+文化遺產”的融合型文化產品,建設文化劇場、文化商場等多種體驗式消費場所。
3.6 加快城市群建設
當前,中心城市及城市群是推動區域高質量發展的增長極,黃河中游地區包含以鄭州、西安和太原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和太原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關中平原城市群是引領西部高質量發展的增長極,太原城市群是我國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和煤化工基地。這幾大城市群具有人口優勢、能源資源優勢、工業發展優勢以及空間優勢,隨著當前國內大循環的展開,要做好承接部分產業向內陸地區轉移的準備,積極建立內陸型核心城市群。要利用好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政策紅利疊加效應,推動這些城市群以新經濟和現代產業為載體實現高質量發展。
4 黃河中游地區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新格局的實現路徑與政策
黃河中游地區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目的是在兼顧生態保護的同時,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并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該地區生態脆弱,在選擇高質量發展的方向與道路時,應結合自身基本狀態和限制條件制定發展路徑與政策。
(1)做好頂層設計。將黃河中游地區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建立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長效機制,促進生態良性恢復,構建黃河中游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良性機制。在經濟建設中要立足區域一體化發展,強化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現代服務業發展,同時要實現資源要素的優勢互補,建立科學合理的產業分工體系。
(2)完善生態保護治理機制。加強水土保持生態工程建設,持續推進退耕還林還草、旱作梯田、淤地壩生態工程建設等。同時,要因地制宜、分類施策、尊重規律,結合不同區域的特點采取差別化的生態恢復措施:在黃土高原核心區域要以保護土壤、增加植被覆蓋、攔沙減沙等為主要任務,以植樹造林、退耕還林還草,以及旱作梯田、淤地壩生態工程建設等為重點,提高生態環境承載能力,減少入黃泥沙;在關中平原以及中原地區,以城市群建設和生態恢復等為基礎,增強現代產業生產能力等。同時,要著眼于減少水旱災害,完善防災減災機制,增強應對災害能力,保障黃河長久安瀾。
(3)創新管理體制。推動中央統籌、省(區)負總責、市縣落實的工作機制,通過流域管理部門和區域行政部門的協作管理努力建設幸福河。一是要建立黨政負責、公眾參與的工作機制,落實各省(區)和有關部門主體責任,建立新型治理及考核機制。二是要充分發揮河長制、湖長制的統籌協調作用,明確治水職責,整合流域資源,在綜合治理的過程中形成強大工作合力,消除“九龍治水”亂象。
(4)在開放合作中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開放合作是實現黃河中游地區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是促進黃河中游地區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是破解發展進程中難題的動力。首先,要積極參與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如陜西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的重要省份,要以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為契機,拓寬對外開放的道路。其次,將“走出去”和“引進來”相結合。讓黃河中游地區的資源優勢和市場規模優勢成為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的主要優勢。一方面在與世界的交流互鑒中展示黃河魅力、弘揚黃河文化,打造文化產品,實現產業轉移,提高市場開放度;另一方面加強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合作交流,大力引進高新產業、技術、資金、人才以及先進的管理經驗等,讓合作共贏成為黃河中游地區高質量發展的動力。另外,應重視內陸型自由貿易試驗區的作用。陜西自由貿易試驗區和河南自由貿易試驗區是我國內陸對外開放發展的標志性成果,在高質量發展進程中要強化自貿區先行先試、擴大開放的重要作用,優化屬地經濟結構,構建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合作發展的新平臺,培育黃河中游地區新的競爭優勢。
(5)深化市場化改革。首先,要充分發揮政府引導資金投向的積極作用。其次,要實現水資源的節約集約利用,加快動態水權管理、水資源利用的市場化改革,在水資源利用中堅持“有多少湯泡多少饃”的思想,把水資源作為黃河中游地區高質量發展進程中最大的剛性約束,以節水定額標準體系為基礎,建立反映水資源供求與供水成本的動態水價調整機制。再次,支持企業對黃河中游地區進行保護性開發,建立生態-經濟融合的新發展模式,鼓勵地方政府適當將流域開發經營的權力下放給企業,企業在進行生態保護的同時發展生態旅游等特色項目,更好地實現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結合,從而建立生態-經濟融合的長效發展機制。最后,在黃河中游地區創新發展的過程中,推動流域管理體制市場化改革,開拓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體制創新道路,通過制度紅利促進發展,進而推動黃河中游地區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在體制改革中,需要黃河中游各省(區)堅持深化市場化改革方向,加快推動資源的自由流動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同時要轉變政府職能,通過簡政放權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參考文獻:
[1] 郭晗.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中的可持續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J].人文雜志,2020(1):17-21.
[2] 陳浩,方海燕,蔡強國,等.黃河中游的侵蝕環境與植被恢復前景[J].地理研究,2007,26(4):735-744,858.
[3] 習近平.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J].求是,2019(20):4-11.
[4] 陳怡平.黃土高原生態環境滄桑巨變七十年[N].中國科學報,2019-09-03(8).
[5] 趙東曉,蔡建勤,土小寧,等.黃土高原水土保持植被建設問題及建議[J].中國水土保持,2020(5):7-9,19.
[6] 李瑞,胡留所,MELNYK L G.生態環境經濟損失評估:生態文明的視角:以陜北資源富集區為例[J].財經論叢,2015(9):11-17.
[7] 李國平,郭江.能源資源富集區生態環境治理問題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23(7):42-48.
[8] 李斌,李拓.環境規制、土地財政與環境污染:基于中國式分權的博弈分析與實證檢驗[J].財經論叢,2015(1):99-106.
[9] 胡鞍鋼,王亞華.如何看待黃河斷流與流域水治理:黃河水利委員會調研報告[J].管理世界,2002,5(6):29-34,45.
[10] 秦書生,王艷燕.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的環境治理體系體制機制[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45(2):13-22,195.
[11] 侯佳儒,孔梁成.黃河流域治理需有協同思維[N].經濟日報,2020-08-17(3).
[12] 王仕濤.推動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N].科技日報,2019-03-05(2).
[13] 金鳳君.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的協調推進策略[J].改革,2019(11):33-39.
[14] 任保平,張倩.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設計及其支撐體系構建[J].改革,2019(10):26-34.
【責任編輯 趙宏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