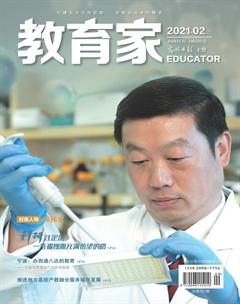加強教育教學科學性的建設
潘希武
通常講,教育是科學也是藝術。所謂科學,意味著一定條件或具體情境下存在可以重復驗證的規律。由于教育是一種極其復雜的活動,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建立起教育的科學模型,即沒有構建起某種特定的教育活動與學習效果之間的明確的函數模型。甚至說,我們也難以對復雜的特定條件或具體情境設計出大數據采集所需要的參數,自然就不好判斷具體教與學之間可能的數學關系。正因為如此,我們習慣于把目前難以說清楚的教育活動說成是教育的經驗或藝術。當然,教育也存在一定的藝術性,因為教育廣泛存在科學所無法把握或指導的情感活動;而且,科學也無法為教學奠定明確無誤的流程或細節規定,教師語言或情感仍然需要藝術性的發揮。
但是,教育不能停留于說不清的經驗和藝術,奠定教育的科學基礎是必要的。哪些教育活動應當是科學的或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以及科學基礎意味著什么或科學的限度在哪里,是值得討論的,這對于教育發展、教師專業發展以及學生發展都是有益的。
教育教學活動的科學性
無疑,教育發展規劃,包括人口預測與學位建設、學校布局、學校空間建設標準、師生比、班級規模、教育經費投入以及課程設置等,都需要科學設置和配備。存在疑問或需要探討的是教育教學活動如何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即要從根本上回答具體的教育教學方式方法采用的科學依據何在,教學效果或學生素養發展是否能夠進行科學檢測并獲得其有力支撐,從而減少經驗型的教學以及未經科學檢測或經不起科學檢測的教學方式。
教育教學活動的科學性體現為三個方面,一是教育教學建立在學生身心發展規律和認知規律之上,這取決于腦科學或學習科學等學科的進步;二是教育教學方式方法在達到特定教學目標上本身具有科學性,即是通往目標的科學途徑;三是教學效果,主要是學生綜合素養發展,經過科學的評價工具的檢測獲得量化的效果。
科學的學生綜合素養評價體系包括量化指標及問卷、試卷、操作、觀察等工具,盡管每一種工具的科學性還有待完善或驗證,比如不同內容的試卷測試體現為不同的結果,但并不妨礙我們對評價結果的整體判斷,原因在于評價指標總是有限的,需要追問的是指標本身是否科學。教育教學科學性的難點在于其是否符合學生身心發展和認知發展規律以及方式方法本身是否科學。身心發展、認知發展以及教學方式方法的科學性都需要加強建設。
建立科學的知識體系
從已有的科學研究來看,關于人的發展的不同領域的科學知識體系建設存在一定差異。從運動生理學和醫學的發展水平看,身體發展與健康領域已經建立起了一套科學知識體系,而且應用到教育領域。美國早期學習標準圍繞大肌肉運動、小肌肉運動、身體健康和安全四個子領域,建立起身體發展與健康領域的學習指標體系。當然,關于身體及其健康的認知還有待科學的進一步發現,體育教學或訓練方式的科學性也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兒童心理發展領域也已經建立了一套科學的知識體系,包括心理試驗方法的采用及臨床診斷技術的產生。研究表明,兒童不同時期的感覺知覺、注意力、語言、記憶、思維的發展都有自己的規律或特點;兒童不健康心理表現的心理機制產生也獲得科學的解釋。然而,人的心理活動畢竟十分復雜,心理科學研究還十分有限,但并不妨礙我們應用基本的心理學知識,把握兒童心理發展特點,實施更科學的教育。運用兒童心理發展科學,探索實施科學的教育方法,促進兒童的感官發展與心理健康發展,而不僅僅是矯正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仍然需要教育科學的探索。
腦科學研究成果為教育教學提供了科學依據
對人的發展的科學認識,最需要突破的是認知發展的研究。認知是腦和神經系統的心智產生的活動或過程。腦科學或腦神經科學關注人的認知發展。認知科學是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與納米技術、生物技術、信息技術一起被認為是21世紀最重要的帶頭學科。揭開人類認知奧秘,對改進人類生存方式以及其他相關學科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基礎性意義。教育要真正成為科學,最為關鍵的依賴或基礎在于認知科學的突破性進步。當然,人的意識畢竟異常復雜,破譯人類心智規律任重道遠。
盡管如此,人類應用腦成像技術,對大腦的結構和功能已經有了科學的揭示,研究表明,大腦結構的不同區域,具有不同的學習功能。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薛貴認為,腦科學對學習力的定義包括三個方面。即大腦的結構對應于特定的學習,比如大腦的感知覺平層和顳葉對應于系統的知識學習;大腦外側前額葉對應于注意力、記憶力、思維力、反應力等認知能力的學習;大腦內側前額葉對應于學習動力的激發和保持。根據大腦結構的分工,包括不同學習的分工、情緒的工作規律等,以及不同年齡的大腦發育特點,采用什么樣的教與學方式,就成為一個科學的問題。比如,學習分享與表達更能激活腦神經,有利于知識的深入理解;活動式教學更有利于促進學生的感官發展和身體經驗的學習;問題探究涉及情境、跨學科知識或綜合性知識與方法的運用,通過刺激大腦神經元,實現神經元的強聯結,促進學生心智結構完整發展。應當說,還有很多腦科學研究成果為教育教學提供了科學依據。對教育教學而言,如何吸收腦科學研究成果,探索科學的教學方式方法,是教育學本身要加強研究的問題。比如,活動式教學、項目式學習或探究性學習,究竟如何開展才是科學的,有沒有一個科學的流程或模型?或者說,雖難以建立起一個模型,但是否可以確定科學的教學若干環節或要點。
當然,有些領域并非完全是個科學問題。人的情感和生活問題似乎是科學不好回答和解決的。同樣,藝術的鑒賞和想象,雖需要具備一定的知識基礎,但主要還是情感與作品的共通及其審美意象的想象問題;人的道德發展更非為某種知識發展的問題,主要是個體與他者關系中的自我認知問題,說到底是自我的情感擺放問題。道德發展具有心理機制,也有相關的科學揭示,但個體意識究竟如何形成特定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仍有待科學的發現。因此,人的藝術發展和道德發展,雖具有相關的科學知識,但科學無法解決人的想象、情感和道德問題。進一步說,藝術教育和道德教育雖然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具有一定的模式或方式,但主要以提供某種體驗或實踐環境或者情感關懷作為主要教育方式,很難探索到某種科學的教學規律。尤其是人的道德成長環境復雜,道德教育本身存在著偶然性。盡管如此,藝術和道德的發展及其教育,仍然存在一定意義上的科學性問題。
教育應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一是要深化對人的發展的科學認識,其中最亟待突破的是對人的認知規律的研究。科學研究是無止境的,或許我們對大腦的研究還只是冰山一角,但不能否認已有認知規律研究的科學性及其對教學的指導意義。二是要加強教育教學方式方法科學性的研究。三是加強教育評價科學性的研究和建設。這是教育教學科學性建設的三個支柱,其中,關于人的發展的科學認知是教育教學科學性建設的基礎,缺乏科學認知,教育教學科學性就無從建設;科學的教育評價工具及測試系統是教育教學科學性建設的根本依據,缺乏科學評價體系,教育教學科學性無從獲得科學檢驗或驗證;難點或需要研究的是教育教學方式方法的科學性建設問題。應用腦科學、神經科學、心理科學等研究成果,依托教育評價,探索教育教學改革是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務,最需深入探索的不是課程內容設置,而是國家課程的創造性實施,即教學方式的變革問題。
教育需要有經驗的積累,更需要有科學的指導,并按科學推進教育教學改革,盡管科學尚不能回答人的發展的所有知識問題,但至少要為教育教學找到某些相對確定的科學方式,而不是完全的經驗總結。教育教學方式改革需要科學的解釋與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