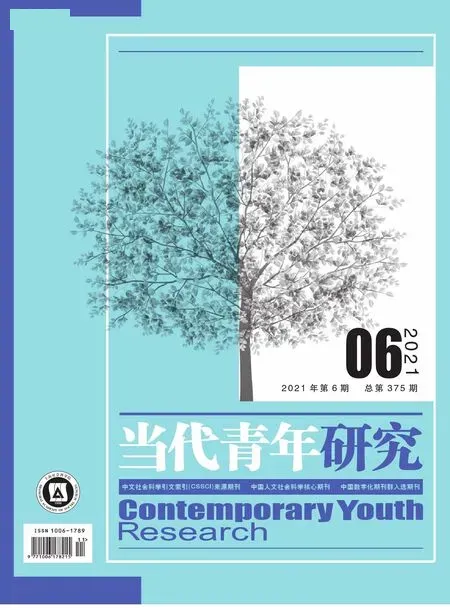農民工基督徒隨遷子女的家庭教育
崔 琪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
隨著進城務工人員的不斷增加,農民工隨遷子女群體也在不斷擴大,這一群體的成長問題成為社會各界日益關注的重要議題。這不僅關系到城鎮化率的實現,而且直接關系到社會公平正義的維護及農民工子女尊嚴的保障。[1][2]增強農民工子女教育,促進隨遷子女群體與流入地相融合,這不僅對隨遷子女群體發展及城市和社會的進步具有重要意義,而且關系到城市有序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3][4]隨遷子女跟隨農民工父母來到城市生活學習,一方面,隨遷子女得到父母更多的關愛和陪伴;另一方面,父母可以更好地陪伴子女,讓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家庭是個體的生活之基,潛移默化地影響并塑造著個體的價值觀念和行動策略選擇。[5]教育社會學的研究指出,家庭在形成和傳遞代際之間不平等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家庭文化和社會背景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兒童的發展軌跡和學習準備。[6]從微觀家庭視角來看,農民工家庭營造的氛圍對隨遷子女的成長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農民工基督徒作為“城鄉雙重邊緣人”,他們的隨遷子女家庭教育現狀既有非信教農民工隨遷子女家庭教育的共性,亦有區別信教農民工隨遷子女家庭教育的個性。本文通過訪談B市Z教會農民工基督徒及其子女,探討基督教教育在農民工基督徒身上呈現出何種特質,對其隨遷子女的家庭教育和城市融入具有什么影響,隨遷子女如何看待這種影響,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種基督教教育。
一、作為“問題”的農民工隨遷子女家庭教育研究
農民工隨遷子女家庭教育研究,大多集中于闡述農民工的文化素質、教育觀念、教育方法、家庭關系、家庭環境等,無一例外以“問題”的形式從外部環境因素和內部家庭因素予以呈現,并據此提出相關意見建議。具體而言,主要表述為缺乏社會關注和家校合作,家長職業地位低,文化素質低,教育觀念落后,教育方法簡單粗暴,親子關系疏遠,缺乏良好的家庭環境(氛圍)等。[6][7][8][9]為此,有學者將上述問題歸納為家庭教育張力問題,包括時間張力、環境張力、知識張力、習性和觀念的張力等四個方面。[10][11]
一方面,我們應該看到農民工因忙于生計、無暇顧及子女所造成的家庭教育問題;另一方面,家庭作為一個具有“面對面”交往特點的基礎群體,父母對子女的影響是通過情感的互動展開的,在互動中傳遞著情感能量。[12]子女作為家庭教育中的另一方,對他們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扮演,現有研究尚顯不足。目前,關于隨遷子女的教育關注,更多的是深入農民工子弟學校,沿襲保羅·威利斯在《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一書中所描繪的工人階級的“小子”反學校文化特征,試圖概括農民工子弟的“反學校文化”及其對于社會階級再生產的意義。[13][14][15][16]不可否認,通過對農民工子弟的就學文化、同輩群體互動的探討,呈現出農民工隨遷子女在城市求學的鮮明特征。但一個人的發展取決于和他直接和間接進行交往的其他人的發展[17],對農民工隨遷子女與其父母的家庭互動層面的研究,可以更加全面地呈現農民工隨遷子女的教育現狀。
當前有關農民工基督徒的研究,大多探討這一群體在“基督徒”和“農民工”雙重身份下的身份認同和城市融入[18][19][20][21],并未進一步涉及此群體的家庭教育面向。宗教作為一種文化資本,必然會影響到農民工基督徒的家庭關系和教育觀念,進而對其家庭教育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二、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民族志田野調查方法。在近一年的田野調查中,筆者以慕道友的身份參與B市Z教會的日常宗教活動,通過觀察及訪談的方式了解農民工基督徒的信仰情況,關注他們“如何運用基督教的教義與知識去解釋性地理解與建構自我生活世界的意義”[22]。筆者除了在信徒周末聚會期間觀察并參與教會的兒童主日學活動,還對農民工基督徒隨遷子女家庭進行多次訪談,搜集資料。
Z教會位于B市城郊的F社區,現有固定信徒近百人,絕大多數為租住在F社區及周邊的外來流動人口。信徒年齡跨度從20多歲到70多歲不等,其中,中老年女性占絕大多數,男性信徒10余人。教會信徒學歷普遍較低,甚至部分信徒為文盲。教會男性信徒多從事裝修、保安、司機等工作,月收入集中在4000~10000元;女性信徒因為識字不多或文盲,多從事商場保潔、家政小時工等工作,月收入集中在3000~7000元。與很多農村教會相似,該教會沒有對信徒進行專門登記,信徒數量沒有精確統計。[23]信徒隨遷子女的年齡大多集中在3~11歲,既有在公立學校就讀的,也有在農民工子弟學校就讀的。他們從小在B市長大,習慣了城市的生活,性格普遍開朗,受家庭影響,均從小參加教會的兒童主日學聚會。由于受入學教育政策影響,部分面臨升學的隨遷子女已經陸續離B市返鄉,因此,近年來參加教會兒童主日學的信徒子女明顯減少。
三、農民工基督徒隨遷子女的教育困境
(一)回鄉與留京
農民工基督徒家庭與其他農民工家庭一樣,面臨子女升學困境。對于面臨子女幼升小的部分農民工而言,由于缺乏勞務合同或者勞務合同不健全,無法提供在京務工證明,子女只能就讀農民工子弟學校。就Z教會信徒隨遷子女的入學現狀來看,年齡較大的子女均就讀于F社區的SY公立小學和鄰近社區的QA公立小學,并無在京就讀初中的信徒子女;年齡較小的子女大多在本社區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就讀。隨遷子女入讀不同學校,與當地的教育政策密切相關。前幾年,政策比較寬松,只要“五證”齊全,便可入讀公立學校;近年來,由于B市嚴控人口,政策明顯收緊,很多隨遷子女難以入讀公立學校,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終究要面對無法在隨遷地參加中高考的難題。
無奈之下,有的信徒選擇提早全家回鄉,有的選擇將孩子寄托給家里長輩或親戚照看。比如,WA基督徒,女,64歲,小時工,黑龍江人,作為隨遷老人在京務工8年,在農村老家信仰基督教并接受洗禮近20年。在面臨孫子女入學困境時,他們考慮全家回鄉。再如,小學生EY,11歲,BL基督徒的女兒,目前在F社區的QA公立小學讀書,明年秋季將面臨初中入學的選擇。父母打算在她小學畢業后,直接送她回老家讀初中,而不是像她哥哥那樣在初三時再轉回老家學校就讀。盡管她更傾向于留在B市讀書,但她也知道畢竟無法在B市參加中高考,而且老家的教材與B市的教材并不相同。為了能夠盡早適應老家的教學,參加日后的中高考,未來考取一個不錯的大學,她只能遵從父母的建議。BL信徒對此也頗為無奈:“現在政策越改越嚴,不是說要減少留守兒童嘛,我看著現在這么越改留守兒童越多了!”也有的信徒思想觀念比較開明,考慮到當前大學生畢業后同樣面臨就業難題,因此,他們并沒有將高考作為子女成才的唯一出路,而認為職業教育在日后的就業環境中更具競爭優勢。相比于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他們并不會給子女施加過多壓力,當前子女的健康成長才最為重要。他們相信在上帝的保守下,子女在未來的社會生存中會有立足之地。例如ZC與LX夫妻兩人早年來B市務工,不久便把女兒從老家接到身邊親自撫育。現在女兒10歲,日后也要面臨中學入學難題,回老家還是在北京就讀,夫妻兩人尚不確定。女兒目前在農民工子弟學校讀五年級,每年需繳納5000元學費。妻子LX信徒心態更為平和,她認為,如果女兒以后考不上大學,那么選擇高等職業教育也未嘗不可。又如,LM和SU夫婦兩人由于來B市較早,且有正式工作,“五證”齊全,所以兒女均就讀公立小學。對于B市當前越來越嚴格的幼升小、小升初政策,LM告訴筆者,許多隨遷子女都被迫返回老家,參加兒童主日學的人數逐漸減少便是一個顯而易見的證明。妻子SU指出:“回老家讀書也面臨不少難題,如果老家的長輩身體健康還好,可以幫忙照顧孩子;如果老家無長輩照看,那只能一人回鄉或夫妻兩人都回去。”至于他們的孩子未來道路怎么走,夫婦兩人認為只能“求神帶領”。夫婦兩人均表示尊重子女的意愿,如果選擇回老家,那便讀寄宿制學校,看他們自身的適應能力。
(二)區隔與融入
從城市融入的視角來看,農民工子女更傾向于群體內部的交往,很少與當地兒童交朋友,生活圈子相對封閉。[24]居住在F社區的農民工子女,不論是就讀于公立學校,還是農民工子弟學校,他們始終被貼有“他者”的標簽,處于“隔離教育”的境地,并無機會與B市本地的學生融合相處。有學者就曾指出:“研究調查所涉及的接納農民工子女的公辦中學,均位于城鄉結合部,從教育教學設施到師資力量,都無法與城市兒童集中就讀的學校相媲美。用教師的話說,‘來我們學校就讀的城市兒童也是比較差的’。即使進入了公辦學校就讀的農民工子女,也只能接受相對較差的義務教育。”[25]現實中,多數農民工隨遷子女是進入城市邊緣化的公立學校或農民工子弟學校接受義務教育。[15]雖然在師資配備、教學環境等方面存在較大差距,但作為服務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教育機構,這兩類學校在農民工隨遷子女城市融入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并無本質區別。甚至說,它們并不能從根本上促進隨遷子女的城市融入,顯性的教育區隔顯而易見,隱形的教育區隔“俯拾即是”。這種區隔從筆者對F社區公益圖書館的調查中可進一步了解。F社區除了擁有若干所幼兒園、小學外,還有一所公益圖書館和一所兒童之家活動室,致力于服務社區的外來務工群體。農民工基督徒家庭的子女大多在課后、周末或者假期去圖書館和兒童之家,免費接受志愿者的輔導教育。輔導項目主要有親子閱讀、繪畫、音樂、英語、數學等。在該圖書館工作人員看來,教育上的城鄉差距不僅僅體現在制度層面,農民工本身對教育的重視程度也遠不如城市居民。她向筆者舉例,就親子閱讀這項活動而言,市場化的教輔培訓機構費用不低,城市家長會積極陪伴孩子開展閱讀訓練。在這里,不僅免費舉辦活動,而且免費借閱圖書,但參與的家長寥寥無幾。
劉謙在對北京農民工隨遷子女的田野調查時發現,農民工面對現實的城市生存壓力:一方面,盼著孩子將來上大學,圓自己“這輩子就算沒白活”的“大學夢”;另一方面,是“他要是自己不爭氣,我就沒辦法了”“走一步看一步”的遲疑與迷惘。[32]農民工基督徒隨遷子女同樣面臨戶籍制度、城鄉分治、教育政策等制度性困境,[26]即使進入公立學校就讀,他們仍面臨著高考的制度約束、家庭和社區的影響。[15]因此,在這種困境下,他們與非信教農民工一樣:一種選擇是把孩子送回老家參加中高考,將來考取大學;另一種選擇則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作是無奈之下的妥協,選擇走職業教育之路。
四、嵌入隨遷子女家庭教育中的宗教信仰
雖然受到相同外部環境因素制約,但內部家庭因素在農民工基督徒隨遷子女成長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良好的家庭教育對于培養孩子的道德觀念、宗教情感、衛生觀念、語言能力,以及觀察自然及人事的能力功不可沒。[27]在筆者的調研中發現,教會信徒學歷普遍較低,他們也沒有能力對子女進行課業輔導。相比于其他農民工忽視家庭教育,采取專制型或放任型教養方式,農民工基督徒更多的是將基督信仰融入日常家庭教育之中,即“屬靈的生命”宗教信仰教育。
在談及基督教育在子女的成長道路上扮演的角色時,農民工信徒均表示讓孩子接觸基督教的主要目的在于讓其信耶穌。在他們看來,從小培養基督信仰,有助于子女更好地適應社會,懂得“愛”與“感恩”,知足常樂,行事光明,“活出基督的樣式”等。正如烏爾利希·貝克在《自己的上帝》一書中所寫:“世俗社會賦予宗教以‘道德的學校’這一新的功能和權威,即使身為懷疑論者的父母們仍然選擇將子女送到教會幼兒園,以求他們習得個體化的社會道德。”[28]這與Z教會的一些信徒家庭十分類似,即使夫妻單方成員信主,其伴侶也支持自己的子女參加教會的兒童主日學,接受基督教教育。農民工基督徒認為,基督教育是“屬靈的生命”,與世俗教育并無沖突,相比于后者的“知識性”,前者更注重“愛”和“屬靈”,注重道德養成,更有助于對后者的理解領悟。比如,QE基督徒,女,36歲,安徽人,小時工,來京務工10年,在京信仰基督教并接受了洗禮。她表示,信仰基督后明白與子女要平等相處,做女兒的好榜樣。把女兒帶到教會參加兒童主日學,就是為了讓她信耶穌。QE認為,在教會中長大的孩子,以后的人生道路會少些曲折,而那些不信耶穌的孩子在日后則容易貪戀虛榮、錢財等,會經歷更多的挫折。自從把女兒帶到教會后,她發現女兒的身心發生了不少變化:相信上帝的存在,遇到困難,自己也會禱告。而且,她認為基督教育與世俗教育是兩碼事,并不沖突。學校更多的是教授書本知識,道德教育有所欠缺,而主日學教育則有效彌補了這一缺陷,通過強調“愛”來提高孩子的道德修養。她也指出,書本知識需要學習,基督教育則是“屬靈的生命”,兩者均不可或缺。筆者提出“她女兒參加兒童主日學是否為自愿行為”這一疑問,QE回應稱:“去教會當然要告知女兒,征得她的同意。因為她從小就被帶著去教會,所以并不存在是否自愿的擔憂。她愿意去,這不能說是習慣,這說明是圣靈的感動!”再如,FA和KT夫婦兩人同為安徽人,丈夫FA為快遞員,妻子KT為小時工,夫妻兩人育有兩個兒子,均在F社區的農民工子弟學校讀書,一家四口十分和睦。他們讓兒子接觸基督教育,是希望孩子可以盡早信仰耶穌、信基督。在他們看來:“這是一條正道,能夠把人往正路上引,不讓你走邪路,只有在耶穌里面才有希望。而且信仰耶穌,閱讀《圣經》,可以讓他們從小就學會尊老愛幼。”關于基督教育與學校教育之間的關系,KT信徒認為兩者并不存在沖突,學校教育有時過于死板,不太注重心理層面的教育,反而基督教育是對學校教育的一種補充,更強調“愛”。他們夫婦兩人均認為讓孩子從小接受基督教育,對他們的身心成長大有裨益:“學校也是教育你怎么團結同學,尊敬他人,但是基督里面不光要叫你愛你所愛的人,連你的仇敵你都要愛。”
除了強調基督教育作為“屬靈的生命”與世俗教育相配合外,他們還將基督信仰融入日常家庭關系相處之中,以他們所理解的解經方式,將信仰與家庭教養相結合,期冀透過信仰的力量,增益子女的家庭教育。例如,SU信徒認為:“咱們先不從信仰方面談《圣經》,我認為它也是一本正能量的書。它從各方面鼓勵你,所以哪怕你不信,去看《圣經》都會得到很多益處。它教你怎么做人,怎么接待人,怎么服侍人。把他們帶到神的面前,我就不擔憂了。因為他們知道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我們自己沒那么多智慧,讓他們自己明白《圣經》,讓神來教導他們。只要他們走到正路上,走到耶穌那條路上,我就不怕他們怎么樣,就怕他們走偏了。我還是這種觀點,《圣經》就是一本正能量的書,不是引導人走異路的書。雖然老師們都不信耶穌,但我們在開家長會時,老師們總是提猶太人聰明。為什么猶太人聰明?因為他們有上帝,有神的保守!諾貝爾獎獲得者中猶太人也最多,具體我們也不懂,但是我們結合信仰來說,為什么他們這么聰明,因為他們有信仰。我們從小給孩子講《圣經》,說不定以后我們的孩子也可以像猶太人的孩子一樣聰明,獲得諾貝爾獎也不是沒可能。就看你根基扎在什么上面了。”作為虔誠的基督徒,農民工基督徒十分重視后代的“屬靈成長”,注重將信仰融入俗世日常,相信“神對子女的保守是最大的恩賜”;基督信仰也讓他們可以更好地尊重子女,以身作則,親子關系比較和諧。他們認為后代擁有基督信仰,可以在人生道路上“依靠神的指引,少走彎路、歧路”。為人父母,望子成龍,他們均認為基督信仰有助于后代的健康成長。
作為隨遷子女,又是如何看待他們所接受的這種基督教育?在筆者的調查中發現,他們都是從小被帶到教會參加兒童主日學。Z教會的主日學老師會通過做游戲、播放《圣經》動畫片,以寓教于樂的方式給教會中的隨遷子女傳遞基督信仰。在這種方式下,兒童大多樂于參加活動,與同輩群體共同接受基督教育的熏陶。由于從小在這種氛圍下成長,他們都能夠向老師和同學坦誠自己的信仰,并不對此有所避諱。由于“三觀”尚未成型,對信仰的認識還處于模糊、朦朧階段,但他們依舊認同基督信仰在成長道路上的價值。例如,LD是教會LM和SU夫婦的兒子,在QA公立小學讀書,愛好籃球、畫畫。從小到大,他十分懂事,活潑開朗,學習成績位列班級中上游,夫婦兩人對此表示這是蒙神的恩典。盡管隨遷的生活條件略微艱辛,但LD和妹妹十分理解父母,從不亂花錢。關于自己的基督信仰,他絲毫不避諱,老師和同學也都知道他的家庭信仰情況。從小被父母帶到教會參加兒童主日學,他視此為理所當然。除不可抗拒的因素外,他每個周日都會與妹妹一起去教會參加主日學。在平時,除了去教會參加兒童主日學聚會之外,他和妹妹也會在家跟著父母閱讀《圣經》和《圣經故事》,學唱贊美詩。因為信仰耶穌基督,相信神的保守,所以,每當遇到困難時他都會主動禱告。他十分坦率地告訴筆者,雖然自己以后很可能回老家讀書,未來充滿不確定性,但他并無太大的憂慮,相信上帝會帶領他,回老家后也會定期聚會敬拜神,成年后就接受洗禮。
五、農民工基督徒隨遷子女家庭教育與城市融入的思考
移民群體的城市融入是一個代際漸入的過程。隨著農民工隨遷子女群體的不斷擴大,盡快完善農民工隨遷子女的就學政策,這是促進外來務工人員更好地融入城市的前提基礎。現有研究也證實,子女隨遷確實顯著增進了農民工的城市認同感和融入感。[29][30]由于存在著城鄉二元體制的區隔,以及主觀層面農民工對子女教育的忽視,導致一些隨遷子女讀完小學或初中后便輟學務工,甚至不到法定婚齡就結婚生子。這意味著農民工子女向上流動和城市代際融入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社會縱向流動的停滯最終將加劇階層的固化,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與此同時,筆者在田野調查中發現,盡管農民工基督徒整體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們均重視子女教育,尤其是基督教的宗教信仰教育。他們較一般農民工而言,更認同宗教教育和學校教育在子女成長中的重要性,不主張子女早婚早育。在戶籍制度等因素的限制下,學校教育存在一定程度的區隔現象,但宗教教育促使信徒子女更加樂觀、積極地面對當下的學習生活。隨遷子女通過接受基督教宗教文化的浸染,在一定程度上舒緩了農民工基督徒子女的教育困境,這對城市發展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同時,我們應該看到,由于農民工基督徒文化程度偏低,無法給予子女足夠的課業知識輔導,他們只能間接“倚靠神,求神賜予孩子以聰明和才智”。
基督信仰對農民工基督徒隨遷子女的基礎教育和人格型塑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子女從小被帶往教會接受宗教教育,“明白神的道”,懂得“愛”與“感恩”,學習成績普遍較好,不至于像其他農民工子弟混日子般地消極讀書。[31]但城鄉二元體制使農民工后代面臨城市教育區隔,難以真正融入城市教育體系。農民工基督徒所看重的基督教宗教教育在下一代的城市融入中亦具有融入與隔離并存的特征:一方面,它強調信仰意義,輕視世俗的功利取向,注重培育子女的“愛”與“感恩”等理念,這無疑有利于下一代的城市融入。另一方面,農民工基督徒群體將后代在基督信仰上的“信”與“不信”劃分為“正路”和“邪路”,這種簡單的二分法顯然有夸大基督教教育價值的嫌疑,對基督教宗教教育的過分注重,必然對后代的社會認知產生負面效應,容易使其對外在的現實社會產生認知失調,甚至造成身份認同的混亂,這無助于下一代的城市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