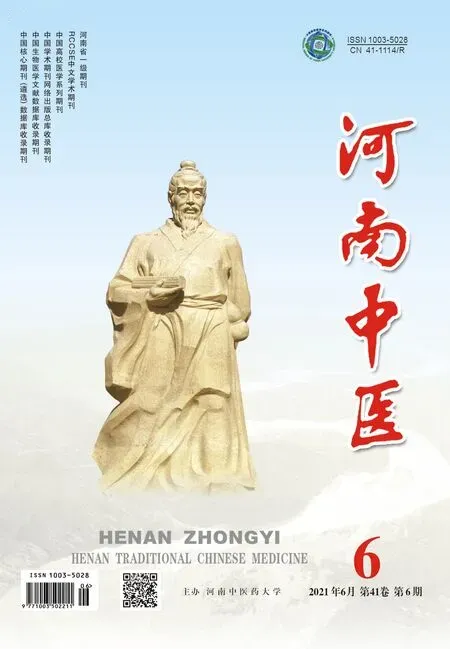中西醫(yī)治療神經(jīng)性耳鳴研究進展*
于艷艷,宋春俠,呂樹泉
1.承德醫(yī)學院,河北 承德 067000;2.承德醫(yī)學院附屬醫(yī)院,河北 承德 067000;3.滄州中西醫(yī)結合醫(yī)院,河北 滄州 061000
神經(jīng)性耳鳴又稱感音神經(jīng)性耳鳴,是指在無外界刺激或外界聲源的條件下所產(chǎn)生的主觀蟬鳴聲、嗡嗡聲、嘶嘶聲等單調或混雜的異常聲音感覺[1]。神經(jīng)性耳鳴發(fā)病機制具有復雜性和多樣性,且主觀性強的癥狀和多樣的病原學使得神經(jīng)性耳鳴很難獲得確切治療[2]。近些年,中醫(yī)藥治療耳鳴在臨床應用廣泛,充分發(fā)揮了中醫(yī)藥辨證論治的優(yōu)勢。為了明確中西醫(yī)治療神經(jīng)性耳鳴的主要治療方法及療效,以期更好地指導臨床用藥,現(xiàn)綜述如下。
1 病因病機
1.1 中醫(yī)認識神經(jīng)性耳鳴屬中醫(yī)學為“腦鳴”“蟬鳴”等范疇,發(fā)病機制論述最早見于《黃帝內經(jīng)》《靈樞·口問》曰:“耳者,宗脈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則宗脈虛,虛則下溜,脈有所竭者,故耳鳴。”[3]《衛(wèi)生寶鑒》曰:“五臟六腑、十二經(jīng)脈皆有絡于耳。”指出了耳鳴與經(jīng)絡的關系。從虛實論治,實證多為外感風邪、肝火上擾、痰濁內阻;虛證多為脾胃虧虛、腎虛精虧或氣血不足。從外感與內傷論治,其“內關五臟,外合六淫”,外感則為邪氣犯于少陽,而內傷多為臟腑虛損而致,主要是腎虛、脾虛。
1.2 西醫(yī)認識目前,西醫(yī)對神經(jīng)性耳鳴的發(fā)病機制仍然不清,病因復雜,多認為與中樞神經(jīng)受損(基底膜感覺細胞病變、延髓與腦干聽覺繼核病變、血管紋萎縮)、神經(jīng)遞質減少、微循環(huán)障礙等有關。迄今為止,西醫(yī)尚無能夠減輕或消除耳鳴的有效藥物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