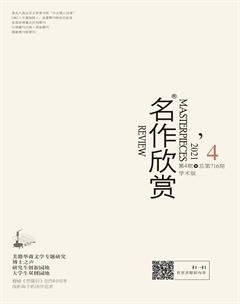簡·愛的身份困境與身份認同
摘 要:《簡·愛》是19世紀英國文學中的經典之作,其中塑造的女主人公簡·愛以強烈的女性反抗精神聞名于世,其形象是否具有矛盾性也引來了頗多爭議。從青少年時期的自我同一性危機到步入社會后的身份抉擇,簡·愛不斷面臨身份困境。作為男權社會主流價值體系中的一員,簡·愛對社會不平等準則的反抗并非以打破現有社會秩序為目的。簡反抗的原動力是其身份困境,斗爭的最終目標是獲得身份認同。當簡的自我身份認同與社會身份認同達到平衡統一后,簡的個人反抗也達到了終點。
關鍵詞:簡·愛 身份困境 身份認同 矛盾性
夏洛蒂·勃朗特所著《簡·愛》是19世紀英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經典之作,國內外學界有關這部作品的研究角度多樣,成果頗豐。簡·愛一向被看作文學史上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她敢于爭取自由、平等的性格為其在文學史上贏得了顯著的地位。但同時,也有學者對簡·愛的形象的反抗性持懷疑態度,認為這一形象在進行反抗的過程中暴露出矛盾性的特征。簡·愛這一形象的自覺意識不可否認,但其還不具備清晰的性別意識、階級意識,更遑論明確的女性主義、階級反抗思想。a
身份認同涉及對自我的確認,其基本含義指個人與特定社會文化的認同。b身份認同又是主觀與客觀的共同作用,包括自我身份認同以及社會身份認同這兩個對立統一的方面。個體認同是個體在時空上確立的自我意識;社會認同則指個體積極追求社會群體成員身份及在群體中的認可后實現社會化。c簡·愛自身作為男權社會主流價值體系中的一員,其對社會不平等準則的反抗并非建立在打破社會秩序的目的之上。簡·愛反抗的原動力是其身份困境,簡斗爭的最終目標是在現有社會秩序下獲得身份認同。簡最終回歸家庭,回到社會既定價值的軌道上,不只是因為簡·愛個人反抗力量的有限性,也是由于簡在獲得了自我身份認同以及社會身份認同后個人奮斗已達到終點。
一、青少年時期的自我同一性危機
自我同一性理論創始人埃里克森認為,自我同一性的形成是青春期的核心任務,青少年面臨著自我定義具體化的任務。d簡·愛幼年生長在蓋茨海德府,十歲進入勞渥德學校學習,直至十八歲離開學校。青少年時期的簡因自我同一性的危機而造成了身份困境,這種自我同一性危機是心理層面身份認同即心靈歸屬的危機。在蓋茨海德府,簡是寄養的孤女,她的家庭身份為其帶來困境;在勞渥德學校,簡于入學之初與離開學校之時兩度陷入身份困境,對這兩次身份困境的化解也是簡人生的轉折點。
(一)寄養兒童的身份困境
簡·愛的幼年時期在蓋茨海德府度過,她被寄養在舅媽里德太太家。寄養兒童這一身份的內在矛盾使簡在幼年便陷入了身份困境:簡不是一家之主的直系親屬,她并非蓋茨海德府的小主人;簡在家中也不從事勞動生產,她與蓋茨海德府也非雇傭關系。簡的自我與他者眼中的身份存在矛盾。
1.自我認同:蓋茨海德府的小主人
簡原本與蓋茨海德府有著血緣關系,蓋茨海德府的主人里德先生是簡的親舅舅。然而,當里德舅舅去世后,簡與蓋茨海德府的聯系發生了質變:舅媽里德太太成為蓋茨海德府的主人,其與簡之間沒有血緣關系。里德太太既沒有撫養簡的義務,也沒有撫養簡的情分,堅持撫養簡只是在履行里德先生死前被迫許下的承諾,而這一承諾違背了里德太太的本心。自此,簡與蓋茨海德府失去了親緣關系,其在蓋茨海德府安逸生活的根基倒塌了。
顯然,簡并沒有認識到自己在家庭中身份的變化。里德舅舅的疼愛使簡產生了慣性,在她看來,自己始終是蓋茨海德府的孩子,理應受到與約翰少爺、兩位小姐同等的待遇。基于此,簡對自己的處境感到不滿,認為里德舅媽苛待了自己。對于約翰·里德的打罵、里德小姐的蔑視、里德舅媽對待親生骨肉與對待簡的雙重標準,簡耿耿于懷;對于自己衣食無憂的生活,簡認為是理所應當的。
2.他者眼光:蓋茨海德府的多余人
“媽媽說你是個靠別人養活的人;你沒有錢;你父親沒給你留下錢;你該去要飯,不該在這兒跟我們這些紳士的孩子一起過活,跟我們吃一樣的東西,穿我們媽媽的錢買來的衣服。”e通過約翰·里德的話語,讀者可以發現,里德太太并未在物質生活上苛待簡。簡對自我身份的認知存在偏差,這一點不僅引起了主人的不滿,雇傭關系下自食其力的仆人們也對簡頗有微詞。在仆人看來,簡并非小主人卻享有著和少爺、小姐們同等的吃穿用度,簡沒有為她的物質生活付出任何勞動。阿葆特認為簡“比用人更沒有權利住在這兒”,白茜也說出簡幾乎從不干活這一事實。簡對自己的家庭待遇不滿,但也不愿放棄蓋茨海德府的物質條件與貧窮的父系親屬一起生活。
簡的幼年在身份困境中度過,由此造成了自我同一性危機。當這種身份困境隨著簡的成長演化為身份焦慮,終于以毆打里德少爺、辱罵里德太太的形式爆發,無論是簡自身還是他人都認為簡不再適宜留在這個家庭。
(二)求學時期的身份認同
簡·愛于十歲來到勞渥德學校獨立生活,在這里簡先后成為學生和教師。這一階段簡對于自身的認同于一定程度上建立在他者的認同之上,簡的自我身份認同向社會身份認同靠攏。
1.他者眼光下的自我認同
對于簡來說,勞渥德學校是一個全新的環境。初入學校的簡努力尋求認同——“我是想做個那么好的孩子,是想在勞渥德做那么多事;是想交那么多朋友,去博得尊敬、贏得愛。”這里沒有人糾結于她的過去,簡很快贏得了老師的贊揚、學生的平等相待。然而,布洛克爾赫斯特先生的突然出現打破了簡剛剛適應的新生活。他聽信里德太太的一面之詞,認定簡是個壞孩子,并不加分辨地在全校師生面前指責簡為撒謊者且對簡進行體罰。自幼缺乏關愛的簡十分看重新環境中他人對自己的態度——“要是別人不愛我,那我寧可死掉,也不要活著——我受不了孤獨和別人的憎恨。”面對布洛克爾赫斯特先生公然指控:“她有孩子的一般外貌……魔鬼已經在她身上找到了一個仆人和代理人”,簡很可能自暴自棄地走上成為小惡魔的道路。
在簡·愛的這場身份危機的化解中,譚波兒小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譚波兒小姐以師長的身份引導簡為自己辯護,并告訴簡自我意識的重要性——“你自己證明是怎么個孩子,我們就認為你是怎么個孩子。”在耐心聆聽了簡·愛的訴說后,譚波兒小姐主動寫信求證,繼而當眾澄清了對簡的指控。譚波兒小姐的教誨與善行幫助簡完成了一次救贖,這使得簡在勞渥德學校逐漸找到了自我身份與社會身份的平衡,成為學校優秀的學生、教師。
2.成年之際的自我懷疑
簡·愛入校八年后,譚波兒小姐離開勞渥德學校步入婚姻的殿堂,她的離去使簡又一次陷入了身份危機:
從她離開的那天起,我就不再是原來的那個人了;一切穩定的情緒,一切使我感到勞渥德有幾分像我的家的聯想,全都跟她一起消失了……我忠于職責,遵守紀律;我安靜;我相信我是滿足的;在別人看來,常常是在我自己看來,我似乎是一個受過訓練的、克己的人。
簡發現幾年來保持的諸多品性只是“從譚波兒小姐那兒借來的”,隨著譚波兒小姐的離去,簡失去了進入勞渥德學校以來心靈的平靜。盡管在他人看來,此時的簡是勞渥德學校出色的畢業生、受人尊敬的教師,但簡已經察覺自己的內心不再滿足于她的社會身份,她開始希望沖破現有身份的束縛,尋找可供靈魂安歇的新身份。
簡·愛在成年之際再次陷入身份認同危機,即他者對其福利學校教師身份的一致認同與其自身對社會身份不滿之間的矛盾。簡的身份認同危機導致了自我懷疑,這種內心矛盾外化為行動,促使簡渴求新的社會職位,開始走上新的生活道路。
二、身份抉擇中的社會認同
成年后簡·愛對身份認同的追求更多是一種對身份或角色在社會中合法性的確認。不論是對家庭教師、鄉村教師等社會身份的選擇,還是對妻子、情人等倫理身份的抉擇,簡的目的都是在自我認同的基礎上獲得身份認同。
(一)社會地位與身份困境
簡·愛對于社會身份的態度充分反映了維多利亞時代的價值觀念。在簡看來,工作是她獲得獨立地位與社會認可的基礎,靠工作謀生、自食其力是她的責任。f離開勞渥德學校后簡有過三次工作經歷,職業在為簡在贏得社會地位與社會尊重的同時也造成了身份困境。
1.家庭教師的身份困境
簡·愛在桑菲爾德府的職位是家庭教師,這一社會身份地位尷尬。家庭教師有知識,自尊心強,但也同仆人一樣受到雇傭關系的束縛,所受的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雇主的主觀意愿。簡也不例外,她在桑菲爾德府同樣面臨著身份困境。
來到桑菲爾德府,簡受到了客人般的待遇,女管家菲爾費克斯太太在初次見面時與簡說:“約翰夫婦倆也都是很正派的;不過,你知道,他們只是仆人,不能用平等身份同他們說話,還得跟他們保持一定距離,因為怕失去自己的權威。”可見在女管家心中,家庭教師簡·愛是有知識的、受人尊敬的,而非雇傭關系下應給予管教的仆人。桑菲爾德府的男主人羅切斯特先生雖不時擺出男主人的架子,但他對待簡從開始便不同于對待府上的仆人,甚至一度忘記簡是他付傭金雇來的。
簡在桑菲爾德府獲得了足夠的自由與尊重,但這一切平衡被貴族客人們的來訪打破了。簡應羅切斯特先生的要求,與客人們共同處于休憩室。在這個貴族聚集的空間,貴族太太、小姐們當著簡的面羞辱家庭教師這一社會群體,使自尊心極強的簡受到了傷害。這次聚會最令簡絕望之處在于,她意識到自己愛上了羅切斯特先生,卻也發現他們的愛情之間隔著的鴻溝——“要是上帝賜予我一點美和一點財富,我就要讓你感到難以離開我,就像我現在難以離開你一樣。”毫無疑問,盡管簡相信她與羅切斯特先生在精神上是平等的,但她也無法否認貧窮與相貌平平使得她在愛情中處于劣勢。
簡有著豐富的精神世界與崇高的精神追求,她甚至對貴族婦女枯燥乏味的精神生活表示輕蔑。然而,缺少美貌、財富與門第的簡社會身份低微,她那向往自由平等的靈魂不得不受制于社會規則。這一切使其陷入身份困境。
2.鄉村教師的身份困境
從桑菲爾德出走的簡·愛來到沼屋,機緣巧合下成為一名鄉村女教師。在簡看來,這份工作雖然卑微、辛苦但并不下賤,這是一個獨立的職業,不似在有錢人家做家庭教師一般依附于人。精神上的獨立自由掃除了簡此前作為家庭教師在經濟上依附于他人所帶來的屈辱感,但正如圣約翰所說,這是一份“貧窮、卑微的工作”。簡在接受這一職位后不得不承認,簡略粗劣的生活條件與缺乏教養的粗魯學生無法使自己感到安定與滿足,她感到“降低了身份”。 簡·愛不否認物質的重要作用,她一向認為精神上的平等不能超越物質上的不平等達到人格的自由和平等。鄉村教師的社會身份使簡陷入了物質與精神之間矛盾造成的困境,她開始認真思考在依附于人的衣食無憂與自由自在的貧窮落魄之間該作何種選擇。
(二)文化塑成的性別身份
簡·愛作為女性這一性別身份的抗爭與保守集中體現在她對愛情的抉擇上。正如波伏娃認為社會性別是“建構”的,女性角色由社會文化塑造。g簡在男權社會中抗爭難免會遇到認同困境,從而表現出保守的一面。
1.妻子或情人:女性的身份認同
當簡·愛與羅切斯特先生確立了戀愛關系后,簡對即將獲得的“羅切斯特夫人”這一身份感到抗拒——“這種宣布給我帶來的感覺,是一種與快樂不相適應的更為有力的東西——它使人不安,使人震驚;我認為幾乎是一種使人恐懼的東西。”這種恐懼源于羅切斯特先生訂婚后顯現出的男權思想與簡自由意識間的沖突,即女性性別身份帶來的焦慮。在19世紀初期的英國,簡·愛一類自食其力的女性生活在男權社會中,正處于社會對婦女“房中天使”形象認知與自身獨立形象認同的夾縫中。羅切斯特先生希望“完全抓住”“占有和保持”簡,企圖用珠寶服飾等財富“這樣的鏈條拴住”簡;而簡自尊自立——“永遠也受不了讓羅切斯特先生把我打扮得像個玩偶”。簡對羅切斯特夫人這一身份的抗拒是對傳統妻子“房中天使”形象的反抗,在簡看來夫妻雙方應當是平等的,妻子并非是丈夫的所有物。
在婚禮舉行之際,羅切斯特先生有一瘋妻子尚在人世的消息公之于眾。如果說此前簡的身份危機是妻子身份下不同價值標準之間的沖突,那么伯莎·梅森的出現則消解了簡作為妻子的身份。伯莎的存在使得簡再也無法成為羅切斯特先生的妻子,而與羅切斯特先生表明了愛情的簡顯然無法再以家庭教師的身份留在桑菲爾德府。可供簡選擇的只有兩條路:以情人身份留在桑菲爾德府,或離開此地重新踏上探尋自身獨立身份的道路。簡選擇離開桑菲爾德府,不僅是因為社會倫理觀念的威懾,也是由于羅切斯特先生在訂婚期間就表現出的強大控制欲。簡意識到如果此時屈從于羅切斯特先生的意志,自己極有可能淪為附庸。想要保持自己獨立自尊的平等地位,簡就必須離開桑菲爾德府。h
2.內心情感與道德約束:女性的道路選擇
對于簡·愛來說,在沼屋的時期是人生的轉折點。于極富浪漫主義色彩的情節中,簡的社會身份發生了很大變化:她找到了失散多年的親人——圣約翰兄妹,不再孤苦伶仃;同時,簡獲得了叔叔的遺產,成為財務自由的女繼承人。
在此時,簡·愛面臨著人生道路的選擇:跟隨內心情感與羅切斯特先生相守,或服從圣約翰的道德約束做一名傳教士的妻子。簡對圣約翰的拒絕是對于無法帶來自我認同的社會身份的拒絕,簡認為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遵循內心情感才是對婚姻與愛情的尊重。在簡動身返回桑菲爾德之時,她并不知道當初逼迫她離開的障礙已被清除,她依然面臨著是否成為情婦、成為附庸的兩難選擇。簡對回到桑菲爾德一事有過猶疑,但依然沒有停下腳步。簡在逃離圣約翰為她安排的命運,她意識到要討圣約翰喜歡,就必須“拋掉我的一半天性,扼殺我的一半才能”,引導簡選擇人生道路的是對自我身份認同的探尋。
三、自我身份認同與社會身份認同
身份認同是主觀與客觀認同的組合,包括自我身份認同以及社會身份認同這兩個對立統一的方面。自我發展理論認為自我狀態是逐步發展的,個體認同指個體對自己獨特性的意識,是個體在時空上確立的自我意識;社會認同理論認為,個體積極追求社會群體成員身份及個體在群體中的認可,最終實現社會化。i
簡·愛與劫后余生的羅切斯特先生在芬丁莊園重逢,并決定建立婚姻關系。對《簡·愛》一書結局的解讀眾說紛紜,有人認為一系列巧合塑造的大團圓結局違背了真實性,也有人認為回歸家庭的簡是女性反抗的失敗。但不可否認的是,簡·愛在芬丁莊園獲得了自我身份認同與社會身份認同的統一:
現在我已經結婚十年了……我認為自己極其幸福——幸福到言語都無法形容;因為我完全是我丈夫的生命,正如他完全是我的生命一樣。沒有一個女人比我更加同丈夫親近,更加徹底地成為他的骨中骨,肉中肉……我全部的信任都寄托在他身上,他全部的信任也都獻給了我;我們性格正好相合——結果就是完美的和諧。
簡走入婚姻,成為所愛之人的妻子,符合主流社會對她的身份期待;同時,簡受到丈夫的尊重與依靠,獲得了實現自我價值的成就感,得到了自我身份認同。簡在社會既定規則中反抗,又在反抗中尋求社會規范的認同。當簡找到了自我身份認同與社會身份認同的平衡,她步入婚姻,定居于芬丁莊園。至此,簡漂泊的前半生畫上了句號。《閣樓上的瘋女人》一書提到,天使與妖婦是出現于男性筆下的兩種極端女性形象,卻在文學中無處不在,成為男性強加于女性的形象枷鎖。j而夏洛蒂·勃朗特筆下的簡·愛無疑為我們呈現了一個與文學史上所有女性都不相同的形象:簡既不是天使也不是妖婦,她不再是符號化、概念化的女性,而是有自我意識的有血有肉的人。在自我意識的支配下,簡不斷化解身份困境,最終獲得了身份認同。
結語
本文運用身份理論對簡·愛形象進行闡釋,從而反思簡·愛形象的矛盾性及其原因,對簡·愛身份變化過程與探尋歷程進行觀照。簡·愛的人生歷程是尋求身份認同的過程,對身份認同的渴望促使簡在不同身份之間做出抉擇。從幼年開始,簡不斷遭遇身份危機,陷入身份困境。簡·愛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女性,性格中的反抗精神使簡拒絕委曲求全,一次次踏上探尋身份認同的道路;同時,根植于簡內心的社會文化使簡的抗爭限定在社會規則的框架下,使其反抗行為不至于超越社會容忍。面對鬼堡般的蓋茨海德府,簡選擇尋機離開,而非采用如伯莎燒毀桑菲爾德府一般的極端方式。簡·愛性格中反抗與保守的調和正是其形象獨特性與同一性之所在,也正因此,簡·愛最終能夠達到了自我身份認同與社會身份認同的統一。
a 肖瓦爾特在《她們自己的文學》一書中將女性寫作分為三個階段:出現男性筆名的19世紀40年代到1880年喬治·艾略特去世的時期被定為“女性階段”(the Feminine phase),這一時期女作家模仿主導傳統的流行模式并把它的藝術標準和對社會角色的觀點國際化;1880年—1920年爭取婦女選舉權的時期被定為“女權階段”(the Feminist phase),女作家對傳統標準和價值觀進行抗議,提倡少數群體的權利和價值,要求獲得自主權;1920年后被定為“女人階段”(the Female phase),是女性作家的自我發現階段,尋求身份認同,1960年左右進入自我意識的新階段。出版于1847年的《簡·愛》是女性文學不自覺時期的產物,以女權主義的性別意識來譴責簡·愛反抗行為之中存在的妥協顯然是一種苛責。
bcdi 張淑華、李海瑩、劉芳:《身份認同研究綜述》,《心理研究》2012年第1期。
e 〔英〕夏洛蒂·勃朗特:《簡·愛》,祝慶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6頁。(下文有關該作引文均出自此書,不再另注)
f 程巍:《倫敦蝴蝶與帝國鷹:從達西到羅切斯特》,《外國文學評論》2001年第1期。
g 〔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宋素鳳譯,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41頁。
h 劉慧英:《走出男權傳統的藩籬:文學中男權意識的批判》,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30頁。
j 〔美〕桑德拉·吉爾伯特、蘇珊·古芭:《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家與19世紀文學想象》,楊莉馨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9頁。
參考文獻:
[1] 肖瓦爾特.她們自己的文學[M].韓敏中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2] 張淑華,李海瑩,劉芳.身份認同研究綜述[J].心理研究,2012,5(1).
[3] 趙一凡等主編.西方文論關鍵詞[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
[4] 夏洛蒂·勃朗特.簡·愛[M].祝慶英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
[5] 程巍.倫敦蝴蝶與帝國鷹:從達西到羅切斯特[J].外國文學評論,2001(1).
[6] 朱迪斯·巴特勒著.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M].宋素鳳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
[7] 劉慧英.走出男權傳統的藩籬:文學中男權意識的批判[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
[8] 桑德拉·吉爾伯特,蘇珊·古芭.閣樓上的瘋女人:女性作家與19世紀文學想象[M].楊莉馨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作 者: 范予柔,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2018級在讀本科生,研究方向:文藝學。
編 輯: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