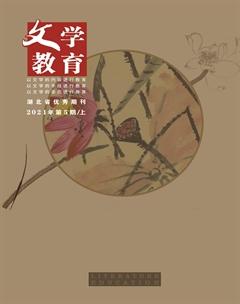詩歌教學(xué)淺探
楊曉慧 李玉君
內(nèi)容摘要:詩歌是極具概括性的文學(xué)作品,我們從字面上理解只能膚淺地了解一下作品,很難在心靈深處受到洗禮,當(dāng)我們深入作家生活的軌跡,結(jié)合作家生平的點點滴滴,我們就能對作家的思想情感產(chǎn)生深切的領(lǐng)悟,才能真正讀懂作品。
關(guān)鍵詞:詩歌 賞析 教法
宋朝大詩人陸游在逝世前一年,曾對他的兒子說:“汝果欲學(xué)詩,功夫在詩外。”這是陸游對其一生寫作經(jīng)驗的概括與總結(jié)。其實,寫詩如此,作為一個教師,在引導(dǎo)學(xué)生學(xué)習(xí)詩歌的時候,亦是如此。因為僅僅是把字面意思解釋解釋,往往會越解釋越像白開水,單薄而缺乏感染力。而當(dāng)我們具有既“博”且“專”的深厚學(xué)養(yǎng)時,能真正結(jié)合作家的豐富經(jīng)歷、結(jié)合作品中主人公的人生軌跡,就能把作家文章中極具概括性的幾個抽象的字眼,變成極富感染力的思想、情感潮流,滋潤學(xué)生的心田,震撼學(xué)生的靈魂。我們才能發(fā)現(xiàn)文字背后蘊藏的豐富內(nèi)涵和情感激流。對詩的剖析才能更豐滿,更有感染力。本文擬以杜甫《登高》詩中的兩句為例加以探討。
《登高》的首聯(lián)、頷聯(lián)以寫景為主,景中含情。教師一般多能聯(lián)系當(dāng)?shù)貧夂颦h(huán)境加以詮釋,而對于頸聯(lián)、尾聯(lián)的首句,分析往往不很到位。因為頸聯(lián)、尾聯(lián)的末句是作者當(dāng)時情況的實寫,并不難解,而頸聯(lián)、尾聯(lián)的首句即“萬里悲秋常作客”、“艱難苦恨繁霜鬢”不僅是當(dāng)時的寫實,更是詩人一生飽含血淚的總結(jié),因此它的內(nèi)涵豐富,這兩句也是全詩的核心所在。然而很多教師卻沒有認(rèn)識到這一點,往往對全詩平均用力,或只從字面上解釋這兩句,而沒有從深處挖掘這種情感的根源,因而在講解中缺乏深度,使這首被楊倫贊為“杜集七言律第一”(《杜詩鏡銓》),被胡應(yīng)麟在《詩藪》中認(rèn)為是“曠代之作”的名篇并不能深深地感染學(xué)生。這也是一種遺憾。
大部分教師在講“萬里悲秋常作客”這一句時,多是按照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的思路來講:“萬里,地之遠(yuǎn)也;秋,時之凄慘也;做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遲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迴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對于研究杜甫的專業(yè)人士來講,這個解釋相當(dāng)貼切,但對于學(xué)生來講卻缺乏感染力,因為他沒有使“常作客”這三個字落到實處。學(xué)生們對杜甫的了解是有限的,對他“常作客”的具體生活更是知之甚少,我們之所以要強調(diào)“常作客”的具體情況,是因為杜甫的羈旅生活不僅長久,而且充滿了苦難,只有了解了這些,我們才能理解句中的“悲”字,才能與詩人產(chǎn)生共鳴。
在這里,讓我們勾畫一下杜甫的行跡圖,我們就會知道杜詩中的“常作客”意味著怎樣的苦難。從天寶五載到天寶十四載,杜甫在長安住了十年,過著屈辱的生活,他“賣藥都市,寄食友朋”,(《進(jìn)三大禮賦表》)生活貧窮,“多數(shù)時間都在客舍里度過的”。他在《白絲行》詩中說:“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十年的長安困守,即天寶十四載,杜甫才被任命為河西縣(今云南祥云附近)的縣尉,后改任為右衛(wèi)率府兵曹參軍,管理東宮宿衛(wèi),此時他已四十四歲。
十年的長安生活以屈辱的“作客”為主,而隨著天寶十四載末安史之亂的暴發(fā),杜甫的生活更是顛沛流離,甚至掙扎在死亡線上。安史之亂暴發(fā)時,杜甫剛從長安回到奉先縣(今陜西蒲城)探望妻兒,當(dāng)他聽說肅宗在靈武(今寧夏回族自治區(qū)靈武西北)繼位,便冒著生命危險前去投奔,半路上被叛軍俘獲,押回長安,過了八個月的俘虜生活。757年趁草木茂盛之際,他逃出了長安,經(jīng)歷了千辛萬苦,終于逃到了肅宗進(jìn)駐的鳳翔。正如他自己所說:“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同年,因營救房琯之事,杜甫被肅宗疏遠(yuǎn)。這年閏八月,肅宗建議他回鄜州(今陜西富縣)探家,這實際上是有意疏遠(yuǎn)他。九月長安收復(fù),十一月,杜甫全家遷回長安。至此,杜甫才和家人在一起過了一段短暫的仕宦生活。然而好景不長,第二年,即公元758年(乾元初年)杜甫又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公元759年(乾元二年秋天),杜甫便棄官把全家遷往秦州(今甘肅天水西南)投親靠友。其中關(guān)內(nèi)饑荒是一個重要原因。然而秦州以及后來隴蜀道上的旅程卻更加艱難。
在秦州,杜甫生活貧困,難以維計,親友也未能給予幫助,不得已又離開秦州前往同谷(今甘肅成縣)。他在《發(fā)秦州》一詩中寫道:“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到同谷后的情況和他的預(yù)料完全相反,那位邀請他的縣令也沒有伸出援助之手,杜甫一家在冰天雪地中靠拾橡栗生活,幾乎凍餓而死。無奈之中,杜甫攜全家頂著風(fēng)雪艱難地行進(jìn)在通往成都的崎嶇山道中,《發(fā)同谷縣》詩里說:“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
公元760年,杜甫一家才終于抵達(dá)成都,開始了飄泊西南的生活。在親友的資助下,杜甫先在浣花溪畔建草堂暫居。公元762年,因劍南兵馬使叛亂,杜甫輾轉(zhuǎn)于蜀中。以后又曾短暫入嚴(yán)武幕府,他在兩川流寓,總計五年多,好友嚴(yán)武病死之后,他在成都無依無靠,便舉家東下夔州、荊楚,于公元770年,病死于湘江舟中。
可見,杜甫半生窮困潦倒,流寓遷徒,因此他的“常作客”是其辛酸痛苦的人生寫真,它飽含著詩人無限的凄苦。我們只有了解了他的“常作客”的一生,才能深切體會詩人在“萬里悲秋常作客”中蘊含的深沉悲慨之情。
同樣,很多教師在講尾聯(lián)的“艱難苦恨繁霜鬢”時,只是籠統(tǒng)地說詩人備嘗艱難潦倒之苦,國難家愁,使詩人苦不堪言,本欲借酒消愁,但由于因病斷酒,悲愁就更難以排遣,這又給詩人增添了一層惆悵和慨嘆。而實際上,這種概述易流于蒼白、枯燥,不能撼動學(xué)生的心,畢竟那個時代離他們太遠(yuǎn)了。他們所能接受的也只是“艱難苦恨”這四個字的表面含意,至于其中包含的詩人對家國的深哀巨痛并不能深切領(lǐng)會。如果教師能通過杜甫各個時期典型的作品加以論述,就會給學(xué)生更多的真實感,“艱難苦恨”這四個字就會深深地撼動學(xué)生的心靈。
我們知道,杜甫出生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他稟承“奉儒守官”的素愿,懷抱“致君堯舜上,再使風(fēng)俗淳”(《奉贈韋左丞》)的理想,以“濟時敢愛死”(《歲暮》)的赤膽忠心步入社會,然而在長安的遭遇卻是“處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從長安回到奉先家中,映入眼簾的不是溫馨的笑臉,而是“入門聞號兆,幼子餓已卒”。(《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當(dāng)國家處于生死存亡、他不顧家人和自己的安危,欲報效國家,卻信而見疑,忠而被貶,以至于全家糊口都成問題,因而在寒冬臘月走上了艱難的隴蜀之道。其間幾乎“餓死填溝壑”,正如他后來總結(jié)的:“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其七)在成都草堂,他的生活雖暫時平靜,但“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茅屋為秋風(fēng)所破歌》)即便如此,他還想著天下的寒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同上)然而這種貧窮的寧靜都是奢侈的,在蜀中,不斷有軍閥混戰(zhàn)和叛亂,杜甫也因此輾轉(zhuǎn)蜀中。在《草堂》一詩中他寫道:“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魚。”而他的貧窮依然如故:“往時文采動人主,今日饑寒趨路旁!”(《莫相疑行》)在流離荊湘的路上,戰(zhàn)亂與貧病亦時時追隨著杜甫:“今年開州殺刺史,明年渝州殺刺史”。(《三絕句》)“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逃難》)臨終前,杜甫貧窮到了極點:“烏幾重重縛,鶉衣寸寸針”(《風(fēng)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對于杜甫的死因,有一些不同說法,有人認(rèn)為是病死的;有人認(rèn)為是被困舟中太過饑餓,多吃了幾口別人送來的牛肉,撐死的;也有人認(rèn)為,因天氣太熱,牛肉變質(zhì),致詩人死亡等等。不管哪種說法,但可以肯定的是詩人是在貧病交加中離開人世的。
杜甫的悲劇不僅源于個人的貧病潦倒,更有對國家與人民的無盡熱愛與憂慮。安史亂前,他曾寫過《兵車行》、《麗人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憂國憂民之作。安史亂中,更是不顧個人安危追隨朝廷。被囚長安時,他面對破碎的山河,“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春望》)他寫出了《哀王孫》、《悲陳陶》、《悲青坂》、《哀江頭》等長歌當(dāng)哭的詩篇。即使在艱難的隴蜀道上,他也難忘國事:“東郊尚格斗,巨猾何時除?”(《五盤》)在荊楚道上,面對混亂的時局,他憂心忡忡,“不眠憂戰(zhàn)伐,無力正乾坤!”(《宿江邊閣》)他思考并憧憬著“安得務(wù)農(nóng)息戰(zhàn)斗,普天無吏橫索錢。”(《晝夢》)即便在臨終前,他還憂念著蒼生與時局:“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歲宴行》)“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戰(zhàn)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風(fēng)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當(dāng)我們了解了詩人的悲哀以及“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nèi)熱”的巨痛之后,我們才能較深入地理解“艱難苦恨”這四個字背后的悲劇。
很明顯,如果我們把《登高》詩中這兩句詳細(xì)解剖,使其真正落到實處,那么,一來可以加深學(xué)生對原著的理解程度,使學(xué)生更接近詩人的情感。二來拓寬了學(xué)生的視野,使學(xué)生對這位詩人有了更深入的認(rèn)識。然而要達(dá)到這種效果,教師必須具有深厚的學(xué)養(yǎng),這當(dāng)然不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教師長期的積累,也需要教師在備課時做大量細(xì)致的準(zhǔn)備工作。
中國當(dāng)代語文教學(xué)專業(yè)委員會溫立三曾指出,語文教師知識結(jié)構(gòu)應(yīng)“既博且專”,“博”指既知曉人文科學(xué),又略通自然科學(xué)。“專”即在語言或文學(xué)的某個或某些方面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對于溫先生的觀點,筆者在多年的實踐中有切身的體會,只有教師的既“博”且“專”,才能使教師避免成為課本的翻板,才能使教師的教學(xué)豐滿、靈動、有吸引力、有感染力。所以教師必須不斷提高自身的專業(yè)素養(yǎng),才能使學(xué)生在有限的時間內(nèi)收獲最大。
參考文獻(xiàn)
1.劉開揚《杜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08月第19頁。
2.本文所引杜詩,均出自楊綸:《杜詩鏡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朱東潤:《杜甫敘論》,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年版。
4.莫礪鋒:《杜甫評傳》,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3年版。
項目:1.陜西省教育科學(xué)課題:基于素質(zhì)教育的中小學(xué)語文閱讀及批判性思維能力培養(yǎng)研究(課題編號:SGH18H299);2.西安文理學(xué)院教改課題:古代文學(xué)課程思政建設(shè)。
(作者單位:西安文理學(xué)院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