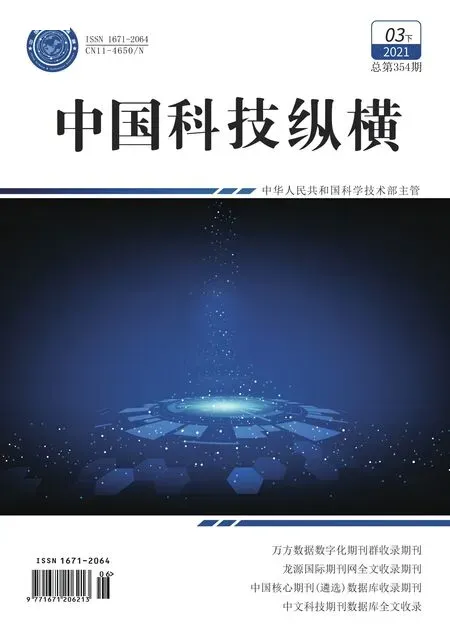算法強權下的受眾困境探討
焦婉瀅
(鄭州大學,河南鄭州 450046)
1.“流量通貨”與“算法霸權”
信息爆炸時代,注意力資源已經成為最稀缺的經濟資源之一,也因而成為財富分配的重要砝碼,在將注意力轉化為經濟價值的過程中,信息聚合平臺與各大社交App作為大眾注意力的主要擁有者,天然成為了注意力這種經濟資源的“流量池”。當“吸引人們的注意力”成為了一種能夠贏得利益的商業價值,其自然而然成為資本爭奪的中心并被催化成為一種現代網絡社會特有的“通貨”。
有流量意味著有受眾注意力,也意味著其變現能力。MCN機構簽約網紅時根據其現有粉絲數、日活量進行商業價值的評估,正是流量“通貨”性的體現,即其不僅能夠在線上進行“引流”等流量交換,還能夠在線下量化為真正的資本。2020年11月,藏族小伙丁真在網絡走紅,據四川新聞網報道,丁真走紅之后,國內某旅游平臺上“理塘”熱度從11月20日起大漲。到11月最后一周,“理塘”搜索量猛增620%,比國慶翻4倍[1]。這種“名人效應”,正是流量已經成為資本流通內在邏輯的最有力證明。
如果說“流量通貨”是“經濟基礎”,流量算法就成為了經濟基礎支撐起的“上層建筑”,在流量算法優化過程中,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不符合流量聚合與排序邏輯的算法被淘汰,流量算法最終被精化為最優推薦路徑—在最大程度上明確用戶畫像并進行個性化推薦與信息配送。然而,算法的專業性、復雜性和不透明性導致的“算法黑箱”“大數據殺熟”的出現,則將算法演進為一種社會權力。當資本以尋求流量與注意力收益為導向,通過算法掌控把關權力,受眾不得不在算法推薦的信息流沖擊下接受著符合資本利益的“信息塑造”。把關權利讓渡到商業性的流量算法手中時,“算法霸權”就加速形成。用戶看似從“個性化推薦”與“定制信息分發”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實則早已被量化為一個個虛擬數據并接受著算法霸權對自我和社會的重塑。
2.算法霸權下的“人性”退化
李錄在其《文明、現代化、價值投資與中國(2020)》[2]中講到,人身上大約有六七成的動物性、三分人性和半分神性。“比如我們的先天智力,這是我們的動物性,動物就會聰明地順應自然做一些基本調整。但是我們發明的教育制度、學習方法,就是人性的部分。”—如果說我們獨立的思考力、自覺的判斷力、獨特的創新力都是人性強化的結果,那算法“算計”的就是人類動物性的底層欲望,受算法操縱,受眾發展“人性”的能力也會隨之退化。
面對超強的算法,人的動物性是最容易被捕獲的。算法善于喚起人類心理底層的獵奇、窺視欲、貪便宜、走捷徑、食色性等訴求,并能夠借此篡取受眾的注意力。動物性的本能即厭惡任何讓自己“高耗能”的事,如學習、深度思考、健身減肥,其實都是反人性的,在算法拋出的誘惑下,反人性的抉擇就更加難以打敗動物本性,更容易選擇“低耗能”且“有快感”的活動來執行。
以各平臺公號文章起標題為例,要提高文章的點擊率,標題要有足夠的吸引力。前大V咪蒙被封號前的運行模式為全公司員工共同為推送文章起標題,放100個標題到群里進行PK,以此得出那個“百里挑一”。這其實就類似于商業“選品”,基于對用戶的理解建立用戶畫像,以此來推測其購買行為。而引入算法之后,這種預測建立在了海量數據的整理與分析之上,使得寫作者能夠根據“算法標注”創造內容。屏幕前讀者的每一次點擊,都相當于做了一次“數據標注”,幫助推薦算法模型不斷優化、持續學習,用戶面對內容產生的任何動作,點擊或是略過,都直接參與了模型的優化。
由此,內容的生產越來越向工業化、流水線化方向發展,超強的算法通過“透視”每一個用戶,為其提供獨一無二無法拒絕的內容。事實上,用戶在任何一個擁有算法推薦機制的平臺上的點擊與操作,很大一部分意味著那些因為演化而依附于人類本能的欲望,大多難以經得起資本精心營造的誘惑。如表1所示,某top20自我提升類微信公號一個月微信收藏文章top10統計,都是人們不想錯過又懶得點開看的東西,最終便只能被“丟進收藏夾里吃灰”,想走捷徑的“動物性”,側面反映了“避免高耗能”的“人性退化”。

表1 某top20微信公眾號十月收藏文章top10統計
3.算法霸權下的信息窄化
今日頭條的創始人張一鳴曾表示,“只有讓用戶越方便、越偷懶的應用,才能體現出真正的個性化推薦”[3]。現實也確實是,產品定制化程度越高,受眾需要投入信息尋找的資金和時間就越少,但相對的,由此引起的“過濾器氣泡”“信息繭房”等現象也隨之而來,關于這些個性化信息推薦為用戶帶來的負面影響,學界已經有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在此不再贅述。學者認為,算法霸權下的信息窄化,至少還催生了兩大值得關注的現象:一是“掠奪式廣告”的大行其道;二是“文化折疊”現象,而兩者進一步加強了算法在當今社會的霸權地位。
3.1 掠奪式廣告
如前文所述,算法在資本支持下,基于受眾在網絡上的行為偏好制造用戶畫像,并設置模型將潛在用戶進行評估與分類,以此來進行合法的廣告營銷,但同時也催生了非法地帶的“掠奪式廣告”。2020年10月,江西都市頻道報道當地一名61歲的女子黃月離家出走,理由是自己已經和“靳東”在抖音上相戀多年,對方答應給她100萬和一套房子[4]。據查證,演員靳東本人沒有注冊官方賬號,但抖音上“假靳東”數不勝數,視頻內容多為:剪輯演員靳東的影視片段,配上符合中老年審美的背景和藝術字,請求“姐姐們”點贊關注并在直播帶假貨。先是引流漲粉,獲取信任,讓對方感覺被關心和依賴,再賣貨變現,這是所有網紅博主的常規套路,不同的是,在算法加持下,針對信息時代弱勢群體的騙局更加“精準打擊”,假靳東的“姐姐們”往往是中老年群體,信息閉塞且缺乏關懷,這就給了掠奪式廣告以可乘之機,其利用算法精確找出有迫切需求的群體,利用這種信息不公掠奪受眾的信任與財富[5]。
這種掠奪完美闡釋了“魔彈論”的卷土重來,算法霸權下的掠奪式廣告具有的強大力量,直接速效地左右人們的態度并支配他們的行動。而現代信息社會,掠奪式廣告最大的受害者、“注意力經濟”下最脆弱的人往往是不具有分辨水平的弱勢人群和面對灰暗現實的群體,掠奪式廣告將更進一步促成其信息渠道、生活水平的惡性循環并鞏固現有社會分層[6]。
3.2 文化折疊現象
在現有社會分層不斷鞏固的情況下,提出于1970年的“知溝理論”(Knowledge Gap Theory)將表現得更加顯著:信息壟斷加劇階層分化。郝景芳在《北京折疊》中設定了3個互相折疊的世界,隱喻上流、中產和底層3個割裂階層,在算法經濟的大背景下,現代社會文化的割裂與折疊已經成為現實。
文化折疊源于最根本的經濟折疊,一二線城市與四五線縣鎮的認知鴻溝被拉開后,由算法主導的信息分發會加固圈層間的壁壘,從而出現“回音壁效應”。而當移動端新技術快速發展,為中國社會實現“村村通網”,原本沉浸于不可接觸的底端話語忽然擁有了媒介渠道,由經濟撕裂引發的文化折疊現象也自然浮出水面。北上廣深和三四五線長久接受不同的信息內容與文化符號,前者無法感知后者關注的流行神曲和病毒式傳播的短視頻,后者也沒有興趣觸及前者追的藝人和脫口秀綜藝,這種圈層壁壘造成了兩者迥異的精神消費習慣和文化認同符號,前者無法下沉,后者無法上觸。
2020年9月4日,克里斯托弗·諾蘭執導的《信條》在中國大陸上映,據藝恩數據顯示,《信條》之前,諾蘭所有作品的一二線城市票倉占比都在70%以上,其中《盜夢空間》高達85.3%,這種諾蘭電影在中國一二線城市的火爆被稱為“諾蘭現象”。而時隔三年,《信條》依舊沒有改變諾蘭現象在三四五線城市的缺失狀況,其票倉狀況在三四五線城市占比僅為27%。
算法的廣泛應用,也無疑加深了這種文化割裂,在“搜索—推送”系統中,三四五線沒人關注諾蘭,算法由此設立畫像與模型,自然不會給三四五線的用戶推送諾蘭相關內容,由此形成的循環鏈,實際上是一種無形的“內容偏見”。這種偏見也將進一步強化算法的霸權地位,正是因為算法擁有選擇與篩除的權力,算法根據用戶動作形成的決策越“偏見”,所謂的“個性化”程度就越高,信息窄化越嚴重,算法的霸權地位就越穩固。最終,“下里巴人”和“陽春白雪”對立的文化折疊現象就越嚴峻。
4.算法霸權下的群體極化
群體極化(group polarization)指在群體決策中往往表現出一種極端化傾向,即當人們在群體討論中發現別人與自己的觀點相似時,他們不愿停留在一般水平上,而傾向于采取極端立場,以表明自己比一般水平更高一些。
不管在線上還是線下語境,大部分用戶都是為了尋找共鳴而非異見。在算法的幫助下,當公共事件發生時,用戶更容易快速通過“話題”“轉贊評”等方式找到“同僚”,進而推動輿論主場向煽動性氛圍發展,群體極化現象越普遍,上文所述的文化割裂就越嚴重。不幸的是,極端內容意味著爭論,爭論與矛盾意味著“通貨”流量,而算法遵從流量,很多微博大V為了爭取流量,便往往選擇輸出更為極端的內容“博眼球”,由此產生惡性循環[7-8]。
5.結語
在“流量即盈利,關注即收益”的互聯網盈利模式下,許多新媒體平臺以“技術中立”“算法無罪”為擋箭牌,逃避自身擔負的社會責任。當把關權利被不加規范地讓渡到資本掌控的流量算法手中,“算法霸權”引發的人性退化、信息窄化、群體極化等倫理失范問題將變得更為嚴峻。高超的算法永遠在進化,而用戶正如井底之蛙,非但難以透視算法機制,跳出井口,還會被不加以道德、法律規制的算法限制視野和發展路徑。算法本身沒有價值觀,但算法應當有價值觀。如果一昧以流量至上作為基本邏輯,“智能算法”便不算真正的智能,也注定不會長久發展下去。建立怎樣的法律法規規制算法、監管能力如何跟上技術發展、相關檢察機關如何發揮能動性,都是亟需學界后續探討和考察的重要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