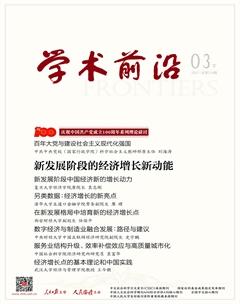人的城鎮化:內涵、問題與對策
李源 郭祥林
【關鍵詞】 新型城鎮化? 人的城鎮化? 民生? 公共服務
【中圖分類號】C912/F29?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6.012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展了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城鎮化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經濟發展,也極大地提升了人民生活的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型城鎮化發展要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更加注重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更加注重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更加注重環境宜居和歷史文脈傳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和幸福感。人的城鎮化是以高質量發展為導向的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核心,是挖掘內需潛力,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關鍵。新形勢下,根據新型城鎮化新情境、新態勢和新要求,我國政府將進一步推進人的城鎮化發展。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總結“十三五”時期發展成就和“十四五”時期主要目標任務并指出:“深入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戰略,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到65%,發展壯大城市群和都市圈,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實施城市更新行動,完善住房市場體系和住房保障體系,提升城鎮化發展質量。”
新時代人的城鎮化內涵
升級的人口城鎮化。物的城鎮化與人的城鎮化不同。物的城鎮化主要表現為空間城鎮化、土地城鎮化、人口城鎮化;[1]而人的城鎮化注重進城農民和居村農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側重在“質”上達到與市民相同的水平。雖然人的城鎮化仍需減少農業人口,促進更多農業人口進城,并使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空間城鎮化相協調,但人的城鎮化不僅對人口城鎮化有“量”上的要求,更有“質”上的要求,即賦予進城農民和居村農民與市民相當的權益,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加快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將擴大規模的城鎮化升級為提高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質量的城鎮化。
城鄉融合發展的城鎮化。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是重城市、輕鄉村,重市民、輕農民的經濟社會結構,不對等的“制度屏蔽”結構力阻礙著農業人口進城、身份轉變和市民化的實現。有學者認為當前城鄉二元結構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由過去的剝削性結構變成保護性的結構,“變成保護進城失敗農民仍然可以返回農村的權利的結構”,[2]并且能防止或避免城市出現貧民窟,有效維護城鄉社會秩序穩定。然而,從本質上看,城鄉二元結構具有的一些正面功能和“善”,只能維護進城農民的生存權,不能保障進城農民及其家屬的發展權。因此,只有消除城鄉分立,促使農村與城市對接、并軌,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才能真正實現人的城鎮化。
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的內在要求之一是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而公共服務均等化是人的城鎮化的價值訴求,其程度高低是檢測人的城鎮化發展的重要指標。公共服務是以政府為主體向民眾提供的非排他性、非營利性服務,分為基本公共服務和非基本公共服務,其中城鄉居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務應該均等。人的城鎮化發展有賴于基本公共服務覆蓋城鎮所有常住人口,而向進城農民提供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務是城鎮政府的重要工作。只有進城農民真正擁有與市民均等、同質的公共服務,切實享有與市民相同的權益和福利,他們才能順利地進行并完成市民化。
居村農民市民化的城鎮化。城鎮化發展不僅改善了進城農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讓他們過上市民生活,而且推進了農業農村的現代化發展,倒逼農村承包地流轉和農業生產規模化經營,促進農村居民生產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城鎮化發展促使農村居民轉變身份。除多數離土進城、轉身為城市市民的農民外,居住在農村的農民一部分在承包地流轉中專門從事農業生產,成為全職的體面的農業勞動者;一部分進入城鎮非農企業工作,成為產業工人;一部分從事“三農”的相關服務工作,成為農村服務人員。未來的中國農民不再是傳統“小農”,無論其在農村從事農業或非農業工作,都將過上與市民相同質量的體面生活。
新時代人的城鎮化現狀與問題
部分農民市民化意愿不強。近年來,國家為了促進人的城鎮化發展,不斷深化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改革,取消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性質區分,減少了進城農民向市民轉身的障礙,[3]但有些打工者和居村農民仍不愿成為城鎮居民。筆者對全國13個省市、40多個市、區、縣的1450份相關調查問卷的統計顯示,41%的農民工明確表示不想將農業戶口轉變為非農業戶口。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和國家持續提高強農、惠農和富農力度,越來越多的農民將不愿轉變其農民身份,同時,越來越多的外出打工者將返鄉居住、創業,并在鄉村安享晚年。這將成為影響人的城鎮化深入推進的重要因素。
進城農民在大城市落戶仍舊困難。就我國當前農業轉移人口集中程度看,有關調查顯示,近40%的進城農民聚集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并且這個比例還在不斷提高。大城市的進城農民集中,人的城鎮化難度大;特大城市的進城農民最集中,農民市民化與人的城鎮化難度最大。[4]人的城鎮化進一步發展需要破解大城市、特大城市農民市民化瓶頸。然而,當前我國戶籍制度改革沒有正面回應農民進入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市民化要求,也幾乎沒有有效措施引導進城農民向中小城市分流。同時,多數中小城市的教育、就業、住房、養老等公共服務仍不能完全覆蓋進城農民,甚至進城農民享有的公共服務數量和水平比在大城市、特大城市更少更低。因此,進城農民對大城市的選擇偏好在短期內難以改變,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口空間壓力還將進一步加劇,引導大城市的農民到中小城市居住、生活任重道遠。
公共服務沒有全面覆蓋進城農民。人的城鎮化應有之義之一即進城農民與居村農民享有城鄉均等化公共服務。然而,在筆者的相關調查中,84.2%的農民工感覺自己與市民在公共服務的享有上差距較大,要求政府解決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問題。該調查顯示,農民工對公共服務的需求由高到低依次是基礎醫療衛生、子女義務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基本住房保障、勞動力就業與培訓、養老保險、法律援助、社會治安、公共基礎設施、公共文化服務、公共交通服務。其中,在基礎醫療、子女義務教育和最低社會保障這三項農民工最迫切需求的公共服務方面,進城農民享有的服務數量與水平仍很不足。
住房是進城農民實現市民化的最大障礙。[5]大中小城市都存在一定數量的進城農民沒有穩定住所的問題。多數地方城鎮政府并未重視進城農民的住房問題,進城農民通常依靠自身能力或單位的有限幫助解決住房,因此多數進城農民為降低居住成本選擇環境和條件較差的房子,甚至部分打工者住在地下車庫、簡易工棚中。筆者調查的農民工中,78.2%沒有得到雇主或單位的住房補貼,29%住在單位提供的簡易宿舍,40%住在自己租賃的房子,只有11%在打工地買了房子。有近45%的農民工認為城鎮生活的最大問題是房子貴、買不起。如何解決進城農民住房問題成為人的城鎮化發展中最棘手的問題。
鄉村留守老人被城鎮化發展遺忘。城鎮化的快速發展造成鄉村出現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等留守“人”的問題。隨著部分留守兒童的父母或留守婦女的丈夫在城鎮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越來越多的留守兒童和留守婦女進入城鎮求學、打工、居住,獨自留守鄉村的老人問題更加突出。一些地方的留守老人既是農業勞動的主力軍,也是村莊最終的“看守人”,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既不能進入城鎮生活,也不能在村莊安享晚年。
深入推進人的城鎮化相關對策
再助力,增強農民市民化意愿。據2019年國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首次超過60%,有2.9億多農民工在城鎮居住、生活、工作。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沖擊我國城鎮經濟,加劇了進城農民工城鎮就業的結構性問題和現實挑戰,或使其工作不穩定、頻繁變換工作,或使其因生活困難無奈返鄉。農民工失去城鎮就業崗位、返鄉從事農業生產,給進一步推進城鎮化發展造成困難,亟需國家再助力,推動城鎮經濟高質量發展,為農民工提供更多、更穩定的就業崗位。此外,國家需要繼續推進農村綜合體制改革,在農村承包地、宅基地確權基礎上,鼓勵農民流轉土地、進城居住,[6]提高進城農民的財產獲得感。再者,國家和城鎮政府需要進一步優化進城農民的生存環境,推進城鎮公共服務全方位、立體式覆蓋城鎮常住人口,努力讓“新市民”“準市民”轉變為名副其實的“真市民”。
再探索,尋求進城農民落戶新途徑。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的《2020年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要求,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城市落戶限制,基本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上城市重點人群落戶限制,促進農業轉移人口等非戶籍人口在城市便捷落戶,推動城鎮基本公共服務覆蓋未落戶常住人口,大力提升農業轉移人口就業能力,加大“人地錢掛鉤”配套政策的激勵力度。然而,就筆者問卷調查顯示,被調查農民工中對落戶政策表示“支持”“反對”“不好說”的各占1/3。一些中小城市曾嘗試以“三置換”政策推進農民市民化,但因置換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換而被否定。一些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采用“積分落戶”政策限制人口過度擴張,雖不利于農民市民化,但因可控制城市規模仍被推行。“三置換”和“積分落戶”不能被簡單評價,都有其適用區間與條件。“三置換”主要適用于城郊、村鎮,針對的是農民就地轉移或就近轉移。如果政府給予進城農民足夠多的“置換”補償,農民就可以在利益不受損的情況下即時享有與城鎮市民一樣水平的社會保障。“積分落戶”主要適用于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對象是異地或外出遠距離打工的農民。然而,就目前各個大城市積分落戶分值及權重設置看,只有極個別農民能落戶,致使占城市外來人口多數的農民難以市民化。大城市需要博士、碩士學歷的“文化人”,需要海歸、專家等高層次人才,也需要大量進城農民做“藍領”“灰領”,因此要進一步探索進城農民落戶新途徑。
再賦權,保障進城農民享有高水平公共服務。筆者的相關調查顯示,約44%的進城農民認為其市民化真正需要落實的是公共服務均等化,戶口僅僅是獲取公共服務的手段。公共服務是農民工的基本權益,人的城鎮化發展需要城鎮公共服務全面、深度地覆蓋全體農民工及其家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個長期過程。就進城農民的公共服務需求迫切程度看,政府應著力解決其就地看病問題,以便其能低成本、方便地在打工地看病、治病;解決農民工子女讀書問題,讓其能接受與城鎮孩子一樣水平的教育;解決進城農民再就業培訓、低保等問題,保障其基本生活,以便將其留在城鎮。
再讓利,解決進城農民居住問題。進城農民住房問題不僅是關系城鎮化建設與發展的經濟問題,還是關涉中國農村社會向城鎮社會轉型的社會問題。房子是進城農民能否進行、實現市民化的關鍵性制約因素。筆者調查顯示,農民工對農民工公寓、租賃住房以及用工單位提供住房等都有一定要求(被調查農民工中,37.2%勾選“建設經濟適用房”,18.5%勾選“完善信貸體系,推動限價商品房建設,幫助農民工購買自有產權房”,兩項相加達到51%以上)。鑒于此,政府應盡可能給予優惠政策,以便進城農民在打工地擁有自己的住房。
再振興,促進居村農民市民化發展。居村農民可以經過市民化改造轉化為市民,路徑有兩條。其一,將鄉村振興重點放在村鎮,打造村鎮公共服務“高地”,引導農民向村鎮,尤其向縣城集中,從事非農職業,過城鎮化生活;其二,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促進居村農民轉變為職業農民。隨著農村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進一步推進,部分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和種田大戶等農業生產者、經營者將成為職業農民,部分居住在農村的農民,其主要職業將是為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打工。人的城鎮化關切重點之一即居村農民,政府應在美麗鄉村建設、鄉村振興中改善鄉村居住和生活條件,促進鄉村公共服務與城鎮對接或并軌,促進城鄉融合發展,進而促進居村農民生活水平質的提高。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公共服務均等化視閾下‘人的城鎮化實踐問題與體制創新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5ASH015)
注釋
[1]任遠:《人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的本質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4期,第134~139頁。
[2]賀雪峰:《城市化的中國道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第11頁。
[3]吳業苗:《戶籍制度改革與“人的城鎮化”問題檢視》,《學術界》,2016年第4期,第45~57頁。
[4]吳業苗:《“人的城鎮化”困境與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社會科學》,2017年第1期,第72~81頁。
[5]文軍:《農民市民化:從農民到市民的角色轉型》,《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第55~61頁。
[6]任常青:《進城落戶農民“三權”問題研究》,《河北學刊》,2017年第1期,第109~114頁。
責 編∕桂 琰(見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