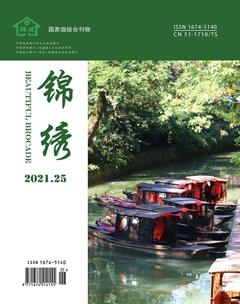霍去病墓石雕群的哲學思想探究
鄭宇
摘要:雕塑是三維空間展開的三維藝術,通過對空間的能動占據而實現自身的形體存在。“以形寫意”的漢代霍去病墓石雕是我國雕塑史上的偉大杰作,作品展現了大漢帝國的時代風貌。本文通過研究漢代霍去病墓石雕的藝術表現手法,探尋中國古代傳統哲學思想在霍去病墓石雕群作品中的體現。
關鍵詞:霍去病墓石雕群;審美思想;藝術價值
霍去病墓石雕群是迄今為止我國最大的石雕建筑群,也是一組紀念碑性質的大型石刻群,存于陜西省興平縣道常村,系漢武帝元狩六年少府屬官左司空署內的優秀石刻匠師所雕造。霍去病18歲受到漢武帝的重用,參加了反擊匈奴的戰爭,后升任驃騎將軍,五年之內,六次出擊匈奴均獲勝,還說出“匈奴未滅,無以為家”的千古名句。但是將軍英年早逝,漢武帝令中府工匠為他雕刻巨型石人石獸置其墓前和墓上以表彰他的功勛。
關于霍去病墓石雕的擺放位置,具有參考價值的是馬子云先生的指出“霍墓與各石雕,字漢至明初大約完整無損。以后至嘉靖年地震,墓上豎立之薄而高者,即傾倒墓下,后而大者則仍在原處。如石馬、初起馬、臥牛、蝙蝠等均為原置之所處;臥虎、臥牛、殘野人、野人抱熊、臥象等由原處傾倒于墓下;異獸食羊在原處。”
這一組石雕有馬有象有虎。倘若我們把霍去病墓石雕比作一則經年的故事,翻開第一章《馬踏匈奴》映入眼簾,它恢宏的氣勢讓我們為之驚嘆,匈奴首領的頭被按壓在戰馬身下,手里握弓握劍卻分秒不可動彈,戰馬威武雄健、傲然挺立。戰場的激烈已然呈現在我們面前,就這么直觀的,我們進入了新的世界。緊接著,《躍馬》和《臥馬》悄然而至,或靜或躍,身姿矯健,在古代戰爭當中,馬的意義尤為重要,這兩匹駿馬象征著驃騎將軍麾下勇猛的戰士,來之必戰,戰之必勝的深刻決心。一個個石雕、一幕幕場景、一章章故事情節,無限驍勇,將象征與寫意巧妙融合,造就了千古不朽的藝術巨作。古樸的雕刻手法象征著樸實的文字表現藝術,循石造型藝術擴大了其大自然的造物力量,沒有華麗的裝飾,用最平淡天真的方式傳達了藝術的蒼茫與渾厚。
霍去病墓石雕群凝聚的是人的思維方式和哲學基礎在特定的造型方式中的表達,它是渾厚與質樸。但透過事物看本質內涵,我們又能發現其內在的哲學思想,頗與我們所了解的原貌又有一些不一樣之處,下面我們來談談霍去病墓石雕所飽含的哲學思想:
一. 感物吟志
創作者在審美創作心理動機中是注重了自然的助力作用。“感物”是社會生活決定審美創作的意蘊和風貌,漢代在秦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各項制度,從而也促進了藝術的繁榮發展,創作者也是依據統治者要求,進行了一定的風格展現。“吟”“志”強調創作者在審美活動中的作用,離開了創作者能動的心、情、志、意等精神活動,就不會有審美創作活動體驗與構思活動的發生。紀念人物、描述歷史融入的是主觀的情與志,是時代之光在創作者心中的折射,儒家圣人“寫天地之輝光”是為了“曉生民之耳目”,亦是抒發亦是表達。
思想的起源大概要追溯到西漢之前的《樂記》。關于審美創作的形成,《樂記》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又說:“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還說:“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分析起來,其中大致包括三種含義:第一,審美創作活動是人的心理需要,“由人心生”,故審美創作的形成必須具備主體方面的條件,事件的發生觸動創作者本身;第二,審美創作動機的形成又需要一定外物的條件,是“物使之然”,創作的本身為了紀念人物與事件;第三,審美創作的形成過程是“人心之感于物”——“感于物而動”,心動而感物便是石雕群的最好闡述,人心使然,自然與精神的美化相結合,應運而生了石雕群的大漢氣勢。
二.神與物游
中國自古以來關于“形神”就有很多的思考,本質上是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問題。這其中,就普遍見于莊子的眾多論點中,并提出神重于形、神貴形輕的美學思想。 這也便與石雕群“循石”藝術相得益彰,以原石的形狀去稍加雕刻,取其神似,而不作細致雕琢,保留了原石的質樸與古拙,神態更重于外形,讓創作者心靈的構思顯得格外重要。
漢代《淮南子》的作者劉安繼承了莊子的思想,指出:“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為”,神與物遷。沒有精神的主宰與制約僅具形體軀殼,毫無氣息,無異于喪失生命,是精神支配并決定著形體,精神也依賴于形體。霍去病墓石雕采取了線雕、圓雕、浮雕等藝術手法,依照石材天然的質地、外形,結合雕塑對象特點順勢而作,體現了漢代雕塑的內涵是意至而形不至,這種大體隨性而為的創作方式極大突出所描繪物象的真實神態和逼真動感,將精神的表現展現到了極致。
三.貴在虛靜
在藝術創作的活動當中,創作者當時的心境顯得越為重要,主張超越俗我。“虛靜”,以空明澄澈的心靈去輝映萬物,提倡“靜以體道”,由“虛靜”以達“道”、合“道”,達成緣在構成、觸目道成、“與道合一”的境域。石雕創作者運用簡潔的刀法營造了空靈的虛靜,而作為審美活動的觀者也需澄清凈化心懷、洗滌心胸、澡雪靈府,進入“虛靜”之境,以獲得心靈的澄凈和心懷的寧靜。漢雕區別于秦,少了實物的描摹,卻帶給觀者更多的遐想空間,觀者的心靈超然于物外,進入一種和諧平靜、沖淡清遠的審美心境,“通以萬物”使“物無隱貌”,能夠清晰的印現出特定的審美對象——物與場景,體悟到蘊藏其深處的生命意義。大象無形,大美無言,它似有似無,若恍若惚,以一種靜寂空明的審美心態和審美心境才能使作品清晰浮現,更展現大漢氣魄。
即如張彥遠所指出;“守其神,專其一,合造化之功,假吳生之筆,像所謂意存筆先,畫盡意在也。”氣和心定、虛明空靜的哲學思想能使創作者的各種審美能力都集中到審美構思上來。停止和淡弱主體意念中的其他活動,使其服務于即將開始的審美創作活動,通過澄懷靜慮以創構出一幅宛在其中的雕塑群像,是心、思、神、想的整體投入,這種境界的營造卻也是境界的表達。
雕塑可以使觀者、雕塑創作者及雕塑作品三者進行意念碰撞,雕塑作品的內涵得益于觀者的精神共鳴,源于雕塑創作者的思維走向。我國當代的一部分雕塑作品是集審美、教育、宣傳、紀念于一身,有很大的現實意義。霍去病墓石雕群雖然年代久遠但是也具有一定的時代意義,但它代表了一個民族的精神力量。在今天,它同樣啟迪我們,也讓我們今天通過它可以跟先祖對話,體會漢文化的雄渾力量和別樣的藝術表達,這種表達內在美的藝術承載了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力量,是一種不可取代的精神氣質。
相較于秦俑展現的求真風格而言,漢雕則是率真的表現。而且霍去病墓石雕群更多源于勝戰心理,是大漢民族向胡人展示西漢的威武和強大。當時漢朝是以霍去病墓石雕群的藝術表現來向胡人證明漢朝的偉大優秀和歷史傳奇,運用的藝術表達方式是基于漢人的民族心理,所以造就了霍去病墓石雕的表達風格古樸而有深意,向胡人宣告勝利來的更加具有代表性和說服性,對于現世雕塑藝術的創作也具有無比深遠的意義。
再者,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造成中西方藝術之間有著嚴格的界限,各有其特定的表現方法。中國的藝術是相互聯系和貫通的,而西方的則不然。它的雕塑有特定的創作方法和表現手段,中國的雕塑表現出與繪畫的密切結合,中國提倡“傳神寫照”、“以形寫神”重神輕形,西方格外注重造型,就如同嚴格的程式。所以說漢代雕塑傳達的更是一種中國文化的內涵。人和人之間總是有區別的,藝術表現也是如此。霍去病墓石雕群在表現方式上更注重線的表現,每一條線都具有獨立的意義與內涵。就其感悟而言,不僅在雕塑方面,而且在繪畫當中,中國文人都可以多加運用我國傳統運筆的線紋之美。
總結
通過對霍去病墓石雕群,我們認識到霍去病墓石雕群在中國美術史以及雕塑史上具有的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不是因為它歷史年代的久遠而產生的價值,而是還有更多的哲學思想值得我們去深究。有創作者“感物”的思想傳遞,表神顯氣的創作構思以及“虛靜”的創作活動。也有了更加成熟的中國式的紀念碑雕刻風格,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我們也從中感受到更多的精神力量。
參考文獻
[1]梁思成.《中國雕塑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
[2]王志杰.《茂陵與霍去病石雕》.陜西:三秦出版社,2005.
[3]馮春田.《文心雕龍釋義》.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
[4]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5]薛永武.《樂記精神研究》.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20.
[6]劉安.《淮南子全注全譯》.北京:團結出版社,2015.
[7]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上海:商務印書館,2003.
[8]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9]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指導教師:周松竹
(長江大學藝術學院 ?湖北 ?荊州 ?434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