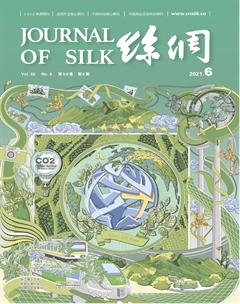明朝與日本勘合貿(mào)易中的織金錦研究
周佳 趙豐



摘要: 明朝在與日本的勘合貿(mào)易中,賞賜了許多織金錦,這些織金在日本廣受喜愛并以名物裂金襕的形式保存下來,但學(xué)界少有人將二者聯(lián)系起來。文章以勘合貿(mào)易中的重要文獻(xiàn)《大明別幅并兩國勘合》中的織金錦信息為基礎(chǔ),采用文獻(xiàn)研究法、對(duì)比研究法,綜合文獻(xiàn)圖像和名物裂金襕實(shí)物等多重證據(jù)對(duì)其中的織金錦進(jìn)行研究,旨在為探討中日絲綢文化交流作出貢獻(xiàn)。研究結(jié)果顯示,其中的織金胸背與蒙元制相似,織金與渾織金為同類織物即用片金線顯紋的織物,有全越與半越、地絡(luò)與別絡(luò)等方式。在織金圖案的選擇上,明朝政府會(huì)根據(jù)日本國情和文化的特殊性作出武官補(bǔ)紋和梧桐葉紋等的針對(duì)性給賜。
關(guān)鍵詞: 明朝;日本;勘合貿(mào)易;織金錦;金襕;絲綢交流
中圖分類號(hào): TS941.12;K892.23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 B
Abstract: During the tributary trade with Japan, the Ming dynasty rewarded many gold brocades. These gold brocades were very popular in Japan and preserved in the form of the Kinran of Meibutsugire, but few scholars have mad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about gold brocade in the important document The Great Ming Scroll and Tributary Trade between Two Countries in the tributary trade, this paper analyzes gold brocade in them,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comparative study and multiple evidence, such as intergrated document images and Kinran of Meibutsugire with a view to discuss silk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the gold brocade patterns in front of the chest and behind the back are similar to the style in the Mongolian Yuan dynasty. Gold brocade and gold-doped brocade are similar fabrics that show patterns with gold threads. There are full-cross and semi-cross, weft-knitting and warp-knitting, etc. Regarding the choice of patterns of gold brocade, the Ming government tended to give targeted reward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particular culture of Japan, such as square patterns on the military officers court dresses and phoenix leaf patterns.
Key words: Ming dynasty; Japan; tributary trade; gold brocade; Kinran; silk exchange
明朝政府與各國的朝貢貿(mào)易中,絲綢交流是十分重要的部分,各番邦外夷對(duì)明朝賞賜的織金錦十分喜愛,乞賜不斷。據(jù)《大明會(huì)典》的不完全記載,獲賜織金錦的有十多個(gè)國家,且以日本尤多。這些織金錦到了日本,被用來點(diǎn)飾裝束、裝裱佛經(jīng)和書畫,而后在茶道文化的興盛中,成為名物裂的代表織物金襕,深刻地影響了日本染織文化。
關(guān)于明代織金錦的研究,學(xué)界已有不少討論,最主要的有沈從文先生[1]介紹了實(shí)物遺存狀況及明代織金錦的風(fēng)尚,還有熊瑛[2]依據(jù)實(shí)物與文獻(xiàn),梳理出明代飾金風(fēng)格和使用的演變并探究其成因。而針對(duì)名物裂中金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學(xué)界,日本學(xué)者明石染人[3]明確指出日本的金襕是在明代初期傳入日本的。小笠原小枝[4]探討了元明時(shí)期通過舶載貿(mào)易傳入日本的絲綢即名物裂,對(duì)其中織金的組織結(jié)構(gòu)進(jìn)行了分析整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chǔ)上,提出以《大明別幅并兩國勘合》中記載的明代傳入日本的織金錦為文獻(xiàn)基礎(chǔ),結(jié)合明代佛經(jīng)經(jīng)面和名物裂中的金襕加以考證,以期從官方貿(mào)易交流中明代織金錦在日本的傳播與保存角度,為中日絲綢文化交流提供一些例證。
1 《大明別幅并兩國勘合》中織金錦記錄
明代初期,由于海禁政策的執(zhí)行,使得中日兩國的貿(mào)易以官方勘合貿(mào)易為主,從永樂二年(公元1404年)兩國的第一次勘合貿(mào)易開始,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最后一次勘合貿(mào)易的這百余年間,明朝的絲綢作為最主要的商品大量流入日本,并深受日本貴族的喜愛,對(duì)日本的社會(huì)風(fēng)氣和紡織業(yè)都起到了不容小覷的影響。其中織金錦占有極大比例,如《大明太宗文皇帝實(shí)錄》中記載有,永樂三年“賜王九章冕服,鈔五千,錠千五百緍,織金文綺、紗、羅、絹三百七十八匹”,但記載十分簡略。
記錄最為詳細(xì)的為現(xiàn)藏于日本妙智院的《大明別幅并兩國勘合》抄本,如圖1所示。這些內(nèi)容也被附載于《善鄰國寶記》與策彥周良的《入明記》中,在永樂元年、永樂四年、宣德八年與正統(tǒng)元年這四次勘合貿(mào)易的皇帝頒賜清單中記有大量織金錦信息(表1),共計(jì)有44類織金錦名目。從表1可以看到,織金錦的基本組織主要有纻絲、紗、羅三種,這也與明代的織金錦主要品種相符。文獻(xiàn)中織金的名目信息包含三類,分別是織金、渾織金與織金胸背。
明朝與日本室町幕府開展的勘合貿(mào)易,使得大量明代絲綢流入日本。在日本學(xué)界一般認(rèn)為,從室町幕府至江戶初期通過官方貿(mào)易及私人貿(mào)易從海外舶來的織物,即是流傳至今的以名物裂命名的織物,其中大部分為中國明代織物[4],其中的織金被稱作金襕。這些織物首次被系統(tǒng)羅列在松平不昧[5]編撰的《古今名物類聚》中,共有166件紡織品,其中金襕就有49種。在上述織金錦文獻(xiàn)信息的基礎(chǔ)上,輔以日本保存的名物裂金襕,筆者將從種類及圖案兩個(gè)角度對(duì)中日勘合貿(mào)易中的織金錦進(jìn)行比對(duì)考證,討論織金錦對(duì)日本染織文化的影響。
2 織金錦種類
織金錦可與各類織物結(jié)構(gòu)搭配,圖案精美,變化靈活。因而明代在蒙元織金錦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其織造技術(shù),讓金線應(yīng)用更廣,與中原設(shè)計(jì)相融合,使織金錦盛行。本文針對(duì)上述中日勘合貿(mào)易中明代的織金織物種類進(jìn)行分析。
2.1 概念區(qū)分
從文獻(xiàn)記錄可以看出,明朝賞賜給日本的織金錦主要有織金、渾織金與織金胸背三類稱謂,并分別與不同的地組織相結(jié)合,羅列在皇帝賞賜物的清單中。
2.1.1 織金胸背
織金胸背在賞賜清單中數(shù)量較多,極具明代特色。首先要確定胸背一詞的含義。關(guān)于胸背的定義,筆者贊同趙豐老師在《蒙元胸背及其源流》中的觀點(diǎn)[6]:胸背指的是在前胸后背上織出一塊方形圖案,胸背與織物連在一起,與整件服裝連為一體,后來的補(bǔ)子是胸背的延續(xù)和發(fā)展。胸背主要流行于元代和明代早期,明初也有花樣的說法,但補(bǔ)子的出現(xiàn)則要到明代后期了。其次,日明勘合貿(mào)易中皇帝頒賜給日本的織金胸背信息包含有織物組織纻絲、紗、羅三類;顏色紅、青、綠三類;紋樣獅子、麒麟、虎豹、海馬、白澤、犀牛六類。這與李東陽所撰《大明會(huì)典》中對(duì)明朝官員常服花樣與用色的規(guī)定相符,“一品至四品、緋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綠袍。”這些織金胸背的信息都表明此處的胸背應(yīng)是先織后縫的絲綢匹料。這是一種承襲蒙元胸背的工藝,是在面料織造之前先計(jì)算設(shè)計(jì)出胸背的紋樣和位置,在織造中一并完成。再將帶有胸背紋樣的面料縫制成衣,因此這種方法成衣胸背紋樣中間會(huì)有縫合拼接的痕跡,這意味著胸背在織造面料時(shí)一定在布邊位置織就成半個(gè)胸背紋樣[7]。克利夫蘭博物館的一幅作于正統(tǒng)九年(1444年)前后的波斯細(xì)密畫,在這個(gè)表現(xiàn)宴會(huì)場景的畫面中出現(xiàn)了三名來自明朝的使臣,這三名明代官員身上所穿的服裝上便是所謂的織金胸背,如圖2所示。
2.1.2 織金與渾織金
此外,勘合貿(mào)易中還有另外兩類稱謂,織金與渾織金。從文獻(xiàn)中的絲綢信息來看,可以區(qū)別這二者與織金胸背的不同,即織金胸背的織金紋樣位于胸背處。而關(guān)于織金與渾織金的區(qū)別,筆者有兩種猜測,一是不同年份賞賜時(shí)稱呼不同,二者并無實(shí)質(zhì)區(qū)別;二是根據(jù)明朝承襲蒙元織金,二者的不同之處可能是紋樣的布局形式差異,即織金為紋樣散點(diǎn)排布,渾織金為遍地金。
首先,根據(jù)上述整理可以發(fā)現(xiàn),織金這一稱謂僅出現(xiàn)在永樂元年的賞賜中,彼時(shí)明朝與日本還未正式締結(jié)勘合貿(mào)易。而在正式開展勘合貿(mào)易后,皇帝頒賜物中的織金除織金胸背外,其余均被稱作渾織金,可以看出這里的渾織金僅是與織金胸背做出了區(qū)分,即織金胸背為織金紋樣位于胸背處,而渾織金則應(yīng)是織金紋樣根據(jù)不同組織規(guī)律散布于整件織物,其中可能包含散點(diǎn)排列或遍地金。
其次,與上述織金名稱有密切關(guān)系的兩類染織群,分別是明代佛經(jīng)經(jīng)面中的織金經(jīng)面及日本名物裂中的金襕。這二者中有眾多織物與上述渾織金織物的信息吻合。因此可以通過整理這兩類織物群中與表1織金錦名稱相吻合的實(shí)物,來分析日明勘合貿(mào)易中織金錦的組織結(jié)構(gòu)與藝術(shù)風(fēng)格。由于篇幅限制,僅列出部分美國費(fèi)城藝術(shù)博物館館藏的佛經(jīng)經(jīng)面實(shí)物信息對(duì)比,如圖3所示。在該館佛經(jīng)經(jīng)面藏品的收藏中,僅有一件遍地金織物,四合如意云雜寶紋遍地金(1940-4-151),其余均為紋樣散點(diǎn)排布的織金織物,這也說明遍地金的占比是較少的。
再者,通過查閱松平不昧編撰的《古今名物類聚》中49種金襕,并比對(duì)東京國立博物館館藏的明代《古裂手鑒》中的實(shí)物,如圖4所示。可以得出,日本名物裂中的金襕中織金妝花類、遍地金的織物占比極少,幾乎均為素色地上織入金線顯花的織金。因此,由上述分析可以推斷日明勘合貿(mào)易中皇帝頒賜給日本的織金、渾織金應(yīng)為同種織物,即織金錦,指將金線織入絲綢來表現(xiàn)紋樣的織物,織物效果華麗精美。這里的渾織金不指遍地金,而是指織金紋樣散點(diǎn)排布的模式。
2.2 織金錦組織結(jié)構(gòu)
根據(jù)日明勘合貿(mào)易中的記載,賞賜的織金錦主要有三種地組織,分別是纻絲、紗、羅。從數(shù)量上看,纻絲即緞地的織金最多,織金紗與織金羅相差無幾。織金纻絲即織金緞,明代的織金緞是在五枚經(jīng)面緞地子上用片金織成華美的金花,在明代存世的各類織物如佛經(jīng)經(jīng)面中就有大量織金緞。明代的織金紗、織金羅的組織結(jié)構(gòu)與花紗花羅基本相同,只是用片金替代了紋緯來顯花。圖5為勘合貿(mào)易中三類常見地組織的織金錦組織結(jié)構(gòu)。
明代織金錦使用的金線以片金為主,片金織入的方法上有全越和半越。全越是織一根地緯織一根金線,半越是織兩根地緯織一根金線。此外,金線固結(jié)的辦法有由地經(jīng)壓和另絡(luò)間絲經(jīng)壓。一般把織物表面表現(xiàn)紋樣的金線用部分地經(jīng)固結(jié),地緯與其余的地經(jīng)進(jìn)行組織的叫作地絡(luò)。而金線由另外的經(jīng)絲固結(jié)的叫作別絡(luò),類似于納石失這類的特結(jié)錦,如圖6所示。明代的織金錦以地絡(luò)為主,別絡(luò)的織金錦在元代以后就比較少見了。
至于本文討論的勘合貿(mào)易中的織金組織結(jié)構(gòu)光從文獻(xiàn)所給的名稱信息是無法判斷的,但可以根據(jù)日本名物裂中保存的明代金襕的組織結(jié)構(gòu)來推斷。表2為部分名物裂金襕的織物組織信息,且均為明代織物。從表2可以看到,明朝傳入日本的織金錦基本上均為片金,日本學(xué)界也普遍認(rèn)為明朝傳入日本的織金錦即指片金織金錦。在金線的織入中既有全越也有半越,對(duì)于金線的固結(jié),則不僅有地絡(luò)的方式,還有別絡(luò)的織金錦。可見盡管明代的織金錦以地絡(luò)為主,別絡(luò)十分少見,但在名物裂金襕中別絡(luò)織金錦的存在表明了織金工藝的多樣性。
盡管皇帝頒賜給日本的這些織金錦以緞、紗、羅三類組織為主,但在名物裂金襕的實(shí)物中還有大量斜紋地的織金織物。這也說明在當(dāng)時(shí)的明朝與日本的絲綢交往中,各類的織金錦通過其他方式大量傳入日本,包括官方貿(mào)易和私人貿(mào)易。從對(duì)文獻(xiàn)中織金錦的概念區(qū)分到組織結(jié)構(gòu)分析,可以推斷勘合貿(mào)易中的織金錦均為明朝流行的織金種類,金線織入的方式均以片金為主,有全越和半越,盡管金線固結(jié)以地絡(luò)為主,但也有少量別絡(luò)固結(jié)的織金。由于染織品的歷史遺存率較低,加上其易損性,因此從以上有限的資料中想要作出關(guān)于勘合貿(mào)易織金錦組織結(jié)構(gòu)的確切結(jié)論仍是困難的。
3 織金錦的圖案
明朝頒賜給日本的織金錦中,有大量的纏枝花卉、云紋和各類吉祥圖案。其中也有元代納石失所留下的影響,如織金胸背中的象征官品等級(jí)的禽獸,織金與渾織金中大量的纏枝牡丹、梧桐葉、金蓮等花卉,還有數(shù)量較多的云紋搭配吉祥八寶等。這些紋樣多為元代舊樣,在明朝繁盛的絲綢生產(chǎn)中得到進(jìn)一步的發(fā)展。
3.1 胸背禽獸紋
明朝在與日本的勘合貿(mào)易中,賞賜的織金胸背紋樣有其特殊性。從文獻(xiàn)記載來看,胸背紋樣共提到以下六類:麒麟、獅子、白澤、虎豹、海馬、犀牛。明代的胸背花樣的品種與品官等級(jí)之間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大明會(huì)典》中明確記載了以禽、獸紋樣區(qū)分文武職員及官品等級(jí),將文武職司分為九等。日明勘合貿(mào)易的記錄中,明朝輸入日本的織金胸背名稱最早出現(xiàn)于宣德八年(1433年),最后的記錄出現(xiàn)在正統(tǒng)元年(1436年)。不難發(fā)現(xiàn),明朝賞賜的這些胸背紋樣除了麒麟、白澤以外,其余均為武官紋樣。
筆者推測這與當(dāng)時(shí)日本的武士通過幕府實(shí)行的政治統(tǒng)治相關(guān),在明代,中日之間的交往實(shí)際是明朝與日本室町幕府之間的交往。因此,明朝賞賜的胸背紋樣均為武官紋樣也不足為奇了。但頒賜的織金胸背的紋樣與色彩并不完全按照《大明會(huì)典》的規(guī)定而制,有許多出現(xiàn)了等級(jí)的隨意搭配,如織金胸背犀牛紅、織金胸背海馬藍(lán)等。《明武宗實(shí)錄》的正德十三年春正月乙巳記載有“賜群臣大紅纻絲羅紗各一匹其彩繡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蠎四品麒麟五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級(jí)。”這些記錄也表明明代的胸背花樣的濫觴,因此在朝貢貿(mào)易中的胸背紋樣織物賞賜,并沒有太多等級(jí)的考量。
3.2 植物云氣紋
上述提到的織金錦中,從紋樣題材來看,纏枝花卉和云氣紋占了較大篇幅,多與八寶紋組合構(gòu)成吉祥寓意。這些織金在日本名物裂的金襕中均能找到相符紋樣的實(shí)物。
花草植物紋樣自唐宋以來便日益成為絲綢圖案的主要題材,這也在明朝賞賜給日本的織金絲綢中體現(xiàn)出來,有牡丹花、蓮花、西番蓮、梧桐葉、寶相花等種類,形式則以纏枝為主。云紋不僅在上述織金錦中出現(xiàn)較多,更是在整個(gè)皇帝賞賜絲綢中占有重要篇幅。有骨朵云、連云、挹腳云、瓢腳云等,以骨朵云即四合如意云紋最多。明代的云紋繼承宋元的傳統(tǒng),云紋變得更加模式化,常見的有四合如意朵云、四合如意靈芝連云、四合如意八寶連云等[8],這在名物裂金襕中也可以體現(xiàn)出來。筆者將部分名物裂金襕中帶有纏枝花卉和云紋的實(shí)物進(jìn)行整理(表3),這些被珍存于日本的明代織物,正是中日勘合貿(mào)易絢爛的絲綢交流的見證。
除以上這些明代絲綢中常見的花卉云紋外,在中日勘合貿(mào)易中,明朝還向日本賞賜了數(shù)量不少的梧桐葉紋樣的織金錦。可梧桐葉紋樣在明代絲綢中十分少見,在對(duì)其他藩夷的賞賜中也并不多見,可見這是對(duì)日本國的特殊賞賜。在日本,梧桐紋由于其高貴的特質(zhì),被用在了帝王的御衣上,在鐮倉末期更是被用作皇族紋章。進(jìn)入室町時(shí)代,足利尊氏因?yàn)樽吭焦儯缓篚旎寿n予了五七桐紋,如圖7所示。
此后,除天皇賞賜外,每代大將軍都會(huì)將桐紋作為獎(jiǎng)勵(lì)賞賜給有功績的大名,桐紋開始擴(kuò)散至天下。時(shí)至今日,桐紋依然可以在日本皇室及政府機(jī)構(gòu)中看到。眾所周知,日本皇室的家紋是十六八重菊紋,而副紋便是桐紋。由此看來,明朝賞賜給日本將軍和王妃的織金錦中有大量的梧桐葉紋樣也合情合理,可見明朝廷在賞賜絲綢時(shí)充分考慮受賜國的國家特點(diǎn)進(jìn)行針對(duì)性的給賜。日本名物裂金襕中也有此類產(chǎn)于明朝的梧桐葉織金,如圖8所示,分別是丹地桐唐草紋金襕(黑船裂)和大內(nèi)桐金襕。其中大內(nèi)桐金襕是戰(zhàn)國大名大內(nèi)義隆特地從明朝訂購的桐紋織金緞,絲綢上的桐紋為橫向緊密排列的五七桐紋,大內(nèi)氏為當(dāng)時(shí)的大名,被賞賜五七桐紋也是正常的現(xiàn)象,特意從明朝高級(jí)絲綢工匠處訂購這種具有特殊意義的織物。
4 織金錦中的中日文化交流
織金錦在中國的制作年代可以追溯到宋朝,但真正大量傳入日本則是從明朝的中日勘合貿(mào)易開始。中日勘合貿(mào)易中,皇帝頒賜的織金錦僅代表了明朝流入日本的織金錦的一部分,還有大量華麗的織金錦通過其他途徑流入日本,經(jīng)過日本茶道文化及美學(xué)的選擇,最終形成了日本名物裂中極具代表性的金襕染織群。
一方面,經(jīng)過日本茶道文化選擇出的這部分金襕織物,與中國的織金錦有著微妙的差異。在日本名物裂的金襕中,被重視的幾乎都是用金線織造的單色紋樣的織金,那些華麗多彩的織金幾乎沒有被日本茶道所采納。這也能看出日本文化對(duì)外來文化的一個(gè)主動(dòng)選擇過程。
另一方面,日本名物裂中的金襕對(duì)明代的織金錦進(jìn)行了再詮釋。產(chǎn)自中國的高級(jí)絲綢在日本以名物裂這一形式被大量保存和再創(chuàng)作,這是一種文化交流的奇跡。這些珍貴的織物到了日本,原來的名稱被忽略,被冠以新的名稱,且命名法不同尋常。有以收藏者或愛好者的名字命名的;有以購買染織品的人名命名的;有以產(chǎn)地或收藏地命名的;有以織物紋樣命名的等[9]。在其中最多的便是以特殊人群對(duì)染織品的命名了,這也是體現(xiàn)了織物與茶道文化中茶人的權(quán)威之間的聯(lián)系。在中國,這些織物的用途多是以功能性為主,如服飾用、器物用等,但在日本隨茶道文化的興盛,織金不僅成為茶道裝點(diǎn)用具,并最終成為了鑒賞對(duì)象。
此外,明代織金錦傳入日本不僅對(duì)日本的染織紋樣產(chǎn)生了影響,對(duì)日本的絲綢生產(chǎn)技術(shù)也起到了重要的促進(jìn)作用。這些流行紋樣如花卉紋、云紋等在日本染織中得到了較為廣泛的運(yùn)用。日本在發(fā)展自己紋樣的過程中,也借鑒了大量中國紋樣的主題,但其名稱、表現(xiàn)形式及情感色彩象征意義都有所變化[10]。如日本的“寶盡紋”與中國的“八寶紋”或“雜寶紋”有著明顯的因襲關(guān)系。日本的絲綢生產(chǎn)技術(shù)也因織金織物的傳入得到了進(jìn)步。使得日本到了江戶年間,開始掌握織金及其他高級(jí)絲綢的生產(chǎn)技術(shù),后來經(jīng)過發(fā)展,成為日本著名工藝代表西陣織中的一類。西陣織技術(shù)的建立,設(shè)計(jì)的完善,也使得西陣成為日本最新、最大的絲綢生產(chǎn)地,成為世界一流的高級(jí)紡織品產(chǎn)區(qū)。
5 結(jié) 語
本文通過對(duì)《大明別幅并兩國勘合》中織金錦記錄的整理分析,推測出明代中日勘合貿(mào)易中,明朝賞賜日本的織金胸背應(yīng)是與蒙元制相似,動(dòng)物紋樣與面料連為一體,先織后縫型的胸背匹料,而非后來的補(bǔ)子。織金與渾織金應(yīng)為同類織物,即用金線顯紋的織物。在種類的選擇上,官方給賜均為纻絲、紗羅質(zhì)地,織金方式均為片金,有全越與半越、地絡(luò)與別絡(luò)等方式。在圖案的選擇上,胸背的禽獸紋均為武官花樣,這與日本室町幕府的武士階層統(tǒng)治相關(guān),織金匹料的紋樣則主要為纏枝花卉植物紋和云氣紋等象征吉祥寓意的紋樣。此外,明朝還根據(jù)日本國情和文化的特殊性,賞賜有梧桐葉紋的織金。以上各種結(jié)論均能在同期的明代織金絲綢實(shí)物和日本名物裂金襕中得到印證。
明代中日勘合貿(mào)易中進(jìn)行的絲綢交流,是日本大量引入外來染織品的一個(gè)歷史階段的開始,其中的織金錦更是龐大絲綢群體的一個(gè)部分。以明代染織品為主的日本名物裂的保存與鑒賞,是對(duì)中日絲綢文化交流的見證,也是對(duì)中國染織藝術(shù)輝煌歷史的注腳。
參考文獻(xiàn):
[1]沈從文. 明織金錦問題[M]//沈從文集. 北京: 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 2007: 215-226.
SHEN Congwen. Problems of Gold-Wefted Brocade of the Ming Dynasty[M]// Shen Congwens Collectio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7: 215-226.
[2]熊瑛. 明代絲綢飾金演變及其原因探析[J]. 絲綢, 2016, 53(8): 66-71.
XIONG Ying. The evolution of silk gold decor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reason analysis[J]. Journal of Silk, 2016, 53(8): 66-71.
[3]明石染人. 染織文様史の研究[M]. 京都: 思文閣出版, 1977.
AKASHI Kunisuk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Dyed and Woven Patterns[M]. Kyoto: Shibunkaku Publishing, 1977.
[4]小笠原小枝. 舶載の染織[M]. 東京: 中央公論社, 1983.
SAE Ogasawara. Japanese Meibutsugire[M]. Tokyo: Chuokoron-Shinsha, 1983.
[5]松平不昧. 古今名物類聚[M]. 東京: 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huì), 1938: 12.
MATSUDAIRA Harusato. Kokon Meibutsu Ruiju[M]. Tokyo: Japanese Classical Collectio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38: 12.
[6]趙豐. 蒙元胸背及其源流[C]//趙豐, 尚剛. 絲綢之路與元代藝術(shù): 國際學(xué)術(shù)討論會(huì)論文集. 香港: 藝紗堂/服飾出版, 2005: 143-159.
ZHAO Feng. A study on Xiong Bei Badge during the Mongol and Yuan period[C]//ZHAO Feng, SHANG Gang. Silk Road and Mongol-Yuan Art: Paper Coll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Hongkong: Yishatang(Costume) Publishing House, 2005: 143-159.
[7]劉瑞璞, 劉暢. 明代官服從“胸背”到“補(bǔ)子”的蒙俗漢制[J]. 藝術(shù)設(shè)計(jì)研究, 2020(4): 59-62.
LIU Ruipu, LIU Chang. On the Mongolian custom and Han system of Ming dynasty official uniform from "Xiongbei"[J]. Art and Design Research, 2020(4): 59-62.
[8]黃能馥, 喬巧玲. 衣冠天下: 中國服裝圖史[M]. 北京: 中華書局, 2009.
HUANG Nengfu, QIAO Qiaoling. History of Chinese Clothing[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
[9]守田公夫. 名物裂の成立[M]. 奈良: 奈良國立文化財(cái)研究所, 1970: 26.
KIMIO Morita. Establishment of Meibutsugire[M]. Nara: Nara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ultural Properties, 1970: 26.
[10]王志惠. 中、日傳統(tǒng)染織工藝及其紋樣的傳承與保護(hù)研究[J]. 藝術(shù)設(shè)計(jì)研究, 2015(2): 54-60.
WANG Zhihui. Protection of heritage & China, Japan & the patterns of the traditional dyeing process[J]. Art & Design Research, 2015(2): 5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