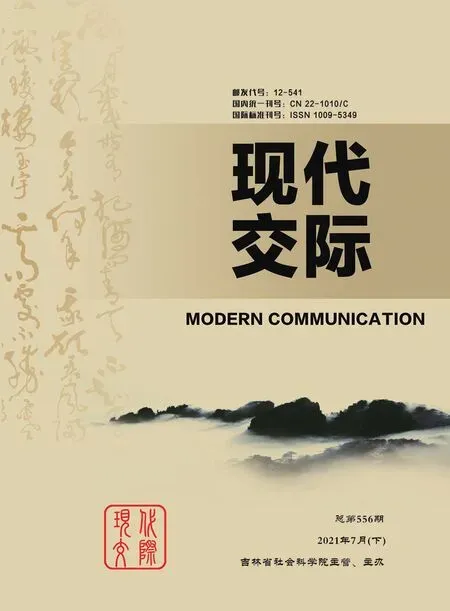道德認知發展理論對我國高校德育工作的啟示
段芊羽
(東北師范大學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 吉林 長春 130000)
青年作為國家的未來,民族的希望,正處于大有可為、大有作為的階段,引導大學生群體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激發其善良的道德意愿與道德情感,提高其道德實踐能力,無疑是對我國高校德育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科爾伯格的道德認知發展理論將為我國高校德育工作提供重要的借鑒作用。
一、道德認知發展理論的基本概述
(一)道德認知發展理論的主要內容
勞倫斯·柯爾伯格是繼皮亞杰之后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他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根據兒童對道德兩難問題的判斷與回答,提出了著名的道德認知發展理論,即“三水平六階段”的道德發展理論。該理論所包含的基本內容如下:
1.前習俗水平(0—9歲)
(1)懲罰與服從道德定向階段
這個階段的兒童沒有是非善惡觀念,他們以是否受到懲罰作為評判行為好壞的標準。因此,這個階段的兒童對權威的服從僅是為了逃避懲罰,是以懲罰和服從為導向的階段。
(2)相對功利主義道德定向階段
這一階段的兒童不再向權威屈服,而是從自身利益出發,趨向服從獲得獎賞。他們開始意識到規則并不是絕對的,開始以自身利益出發去做相應行為。雖然這種行為也會惠及他人,但這種行為可能不是建立在慷慨與同情基礎上的,是以利益交換作為代價,他們本質上還是為了滿足自身需要。
2.習俗水平(10—20歲)
(1)尋求認可定向階段
這個階段的兒童已經擺脫了對權威和懲罰的服從,進而轉向認可與贊揚。凡是可以受到他人喜歡、贊揚與認可的行為都是好的行為。因此,這個階段也稱“好孩子”定向階段。這個階段的兒童還沒有普遍的社會秩序觀念。
(2)維護權威或秩序的道德定向階段
兒童以是否符合社會秩序作為評判行為好壞的標準,并盲目地認為只要符合特定的社會規則就可以免受指責。這個階段的兒童以服從社會規則為導向,尊重和維護法律的權威。
3.后習俗水平(20歲以后)
(1)社會契約的道德定向階段
青年意識到社會規則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契約,但這并不是絕對的,是可以應大多數人的要求而改變的。因此,考慮到價值觀的多樣性,青年考慮行為時會結合法律與道德雙重考量,具有一定的靈活性。
(2)普遍原則的道德定向階段
這個階段也被稱為原則或者良心道德階段,只要其行為的出發點為善意的,其行為就可被定義為正確。科爾伯格指出,雖然道德認知發展有著嚴格的先后順序,但由于文化或環境因素的改變,也會打破這個發展順序。
(二)道德教育方法
科爾伯格認為,道德是可以被教授的,但是單一的灌輸不能促進學生道德水平的發展。因此科爾伯格根據道德認知發展理論,提出了兩個著名的道德教育方法——道德討論法和公正團體法。
1.道德討論法
道德討論法又稱課堂討論法,是科爾伯格第一個道德教育干預策略。它是將學生置于道德兩難的情境中,通過道德問題的討論,激發學生積極思考,在道德問題的分析與交流中,提高其道德認知水平并形成自己的道德觀。在個體的交流過程中,可以根據學生對道德兩難問題的思考與判斷,測量其道德認知發展水平,進而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這種道德教育方法的突出貢獻在于為道德認知發展水平找到了衡量標準,但其本質上仍是以提高學生的道德認知為歸宿,而忽略了與道德行為的統一。同時,這種帶有極強抽象性的教育方法并不適用于全部學生,不利于具體操作。因此,為了彌補道德討論法的缺陷,科爾伯格提出了第二種教育方法——公正團體法。
2.公正團體法
公正團體法是科爾伯格在訪問一所以色列農莊學校時提出的一種干預策略,他發現那里的集體道德教育建設了很好的集體規范與團體意識,有利于道德認知向道德行為的轉化。科爾伯格深受啟發,并在對柏拉圖、杜威、涂爾干等教育思想的吸收與重新評估,以及自己“監獄實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公正團體法。這一方法是通過師生民主參與活動,使學生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營造出一個公正團體的教育環境,使集體中的每個人都能參與民主決策和管理,并自覺遵守共同規則,做到知行合一,提高其道德水平,完成從他律向自律的轉化。在公正團體法中,老師和學生擁有相同的基本權利,學生要在遵守共同規則中進行自我教育與自我管理,而教師的職能也從單純道德認知的傳授者開始向道德行為的推動者轉化。
二、大學階段是道德認知發展的重要時期
人無德不立,國無德不興。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指出:“青年要把正確的道德認知、自覺的道德養成、積極的道德實踐緊密結合,不斷修身立德,打牢道德根基,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正、走得更遠。”[1]隨著市場經濟高度發展,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產業層出不窮,大學生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利己主義、功利主義等錯誤思想也隨之而來。提高大學生的道德水平,使其在多樣化的價值觀念中始終保持定力,明辨是非,這對于整個國家、民族及大學生個人發展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基于科爾伯格的道德認知發展理論,對不同受教育水平的422名學生進行了“道德兩難”問題的調查,他們分別來自小學及以下(1.0),初高中(2.0),大專及本科(3.0),碩士及以上(4.0),通過spss數據分析得出受教育水平與道德認知發展階段之間的關系。
表1不同受教育水平學生的道德認知發展階段顯示,受教育水平為小學及以下的道德認知發展水平平均值為3.71,初高中為3.52,大專及本科為4.17,碩士及以上為4.22。可見,道德認知發展確實與受教育水平成正比,受教育水平也是影響道德認知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初高中到大學階段的道德認知發展水平相較于其他三個受教育階段的道德認知發展水平而言,其增長幅度最大(見表2),由此可以表明,大學階段是道德認知發展的重要時期。

表1 不同受教育水平學生的道德認知發展階段

表2 多重比較因變量:道德發展水平階段
三、道德認知發展理論對我國高校德育工作的啟示
培養德才兼備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是我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重要價值目標導向,如今高校德育單一的教學方式、傳統的教學手段,以及落后的教學理念,致使學生出現言行不一、知行脫節等問題,高學歷大學生違法犯罪現象屢見不鮮。科爾伯格的道德認知發展理論在不同時代、地域、文化背景下的貢獻都是有目共睹的,我國高校德育可借鑒國外優秀經驗,促使我國德育工作煥發新的活力。
(一)改進教學方法,發揮學生主體性
柯爾伯格提出“兒童是道德教育的哲學家”的命題,這個命題在教育學上的邏輯結論必然是:灌輸是無效的。[2]在我國傳統德育中,單向灌輸與機械記憶是德育的主要方法,使我國德育工作停滯不前,學生出現知行脫節,言行不一等現象。因此,教師要借鑒國外德育方法,結合我國實際,改變傳統教學模式,及時轉變教師角色,并充分尊重和發揮學生在課堂上的主體性,這無疑是給教師德育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高校教師自身要不斷豐富學識,提高個人魅力。隨著網絡化的發展,教師已不再是唯一的知識傳播者,學生可以通過網絡自主學習,這就削弱了教師在知識傳播中的權威性。教師只有不斷提升自身素質,與學生互相學習,共同進步,才能用自己的才能、品行潛移默化地感化學生。另一方面,高校教師要改變灌輸式的教學方法,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提倡師生間雙向、平等的對話,引導學生在交流互動中提高道德水平。
(二)更新教學觀念,發揮同輩群體的正面力量
同輩群體存在于大學生周圍,其作用體現在大學校園生活的方方面面,對大學生的思想觀念、價值標準和行為習慣都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同輩群體之所以會對個體產生影響,是因為不同個體的道德認知水平不同,在日常交往中會出現沖突性,柯爾伯格認為這種帶有沖突性的日常交往最適合促進個體道德判斷能力的發展。道德認知平均水平較高的同輩群體會對個體道德認知水平較低者產生一定影響。因此,德育工作要發揮同輩群體的正面教育力量,運用“課堂討論法”與“公正團體法”引導學生通過對假設性道德兩難問題進行討論,使學生道德認知發生沖突,引發學生積極思考,使其被高于自身道德水平的道德觀念所同化,拒斥低于自身道德水平的道德推理,使學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充分發揮學生的自主性與同輩群體的積極作用,把集體力量作為一種教育資源,促進學生道德的發展。
(三)以發展的眼光看待學生,遵循學生身心發展規律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發展的普遍性原理要求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學生進入大學階段,他們的道德水平發展并不會停止,而是隨著自身的獨立發展不斷變化,這與柯爾伯格提出的“道德具有發展性”是一致的。因此,在對大學生進行道德引導時,要求教師可以依據“三水平六階段”理論,有針對性地分析學生道德認知發展的特點和規律,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德育規劃。我國傳統道德教育多以“一刀切”的形式對待不同年級的學生,大學生被灌輸了正確的道德理念,卻無法形成成熟的道德判斷,其道德行為也一定是停滯不前的,這種德育方法對于提升大學生的道德認知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大學生的德育工作要以階段性為依據,根據學生現有的道德水平,找準每一階段德育的起點和目標,進行有條不紊地、由淺入深的教育。
(四)重視隱性課程的作用,不斷更新教育手段
柯爾柏格認為,德育應發揮隱性課程的力量,隱性課程是實現德育的橋梁。教育過程不僅存在于課堂教學,更存在于學生所處的環境中,良好的校園環境與班級氛圍對學生道德認知發展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因此,高校的德育工作不僅要重視文化課的建設,還應注重校園和班級的建設,為學生的發展塑造健康的成長環境。在這個教育過程中,教師的教育手段也應與時俱進,尤其是對網絡的運用。隨著科技水平的高速發展,網絡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大學生更是運用網絡的主要群體,大學生德育工作可以以網絡為載體,充分利用網絡信息傳播的時效性與交互性,利用多種教育宣傳平臺,以網絡手段作為傳統手段相補充,將隱性課程與顯性課程相結合,為學生創造一個由內到外的健康成長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