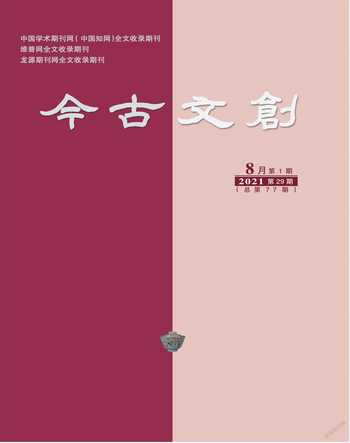淺談博物館文物保護教育
【摘要】 作為公共文化空間,以博物館為場所的文物保護教育機構具備公共性與文化性的特質。這一場所包含兩類開展博物館文物保護教育的要素,一類為文物、空間、人力等教育活動所需的資源,另一類為包含文物保護從業者、教育者、受教育者、旁觀者在內的教育活動參與者。
【關鍵詞】 博物館教育;文物保護;公共文化
【中圖分類號】G260?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29-0117-02
教育是博物館的主要職能之一。隨著博物館參觀人數的日益增多,大量博物館教育活動隨之配套開展。與此同時,完善博物館教育體制、突出教育特色、改善教育方法、強化教育效果也成為博物館教育工作者關注的問題。
一、作為場所的博物館文物保護教育
(一)公共文化空間中的文物保護教育
博物館的公共文化屬性,體現為公共性與文化性兩個方面。博物館作為公共空間,是大眾能夠參與、集結、交流的場所。這里的大眾與私人相對,強調了空間的廣泛性。
因此,博物館不僅是簡單的文物陳列場所和地理空間概念,還是富有深刻文化意義和生命力的城市意象空間與人們的精神家園。
而這一場所中的文物保護教育,也具備公共性與文化性的特點。作為公共的文物保護教育,活動的客體是社會大眾,這要求教育活動能夠讓社會中的所有個體享受到有關文物保護的基本教育機會;同時,個體之間的差異決定了保護教育的多元化結構與形式。作為文化的保護教育,其目的在于輸出一類特定的文化體驗,從而樹立一種社會性的行為規范與價值理念。后者體現了文物保護教育過程中的博物館作為公共文化空間,不僅是價值符號的載體,也是文化生產的場所。博物館輸出的文物保護文化,“生產和再造著新型的城市文化”[1],成為社會變革的陣地。因此,相較于學校教育,博物館中的文物保護教育參與的受眾更廣泛,教育行為本身被賦予了一定的文化意義。
(二)博物館文物保護教育資源
博物館這一場所擁有得天獨厚的文物保護教育資源。作為文物收藏、保護、陳列、研究的場所,博物館自身擁有的文物資源,為文物保護教育提供了基礎素材。
文物保護活動針對的實體為文物,保護行為的對象為文物,由文物展陳構成核心內容的博物館空間,本身即為保護行為的結果展現。這種展現涵蓋了“核心文化、符號系統和動態展演”[2]三個方面。
博物館空間的核心文化是文物保護教育活動的靈魂,同博物館空間的文化性相關聯,決定了文物保護教育的旨趣風格。符號系統是核心文化的載體,決定了空間的物質形態,是文物保護教育開展的物質基礎。最后,博物館這一場所具備開展文物保護教育的人力資源。
博物館作為直接接觸文物的組織,是文物保護活動實踐的前線,配備有相應的文物保護專業人員。博物館的文物保護教育活動,以這類專業的人力資源為基礎,使教育活動具備現實性與前沿性。
(三)場所中的教育參與者
文物保護教育的參與者可以分為從業者、教育者、受教育者,旁觀者。文物保護從業者既可以是單獨的保護知識顧問,也可以兼任文物保護教育中的教育者。教育者對教育活動中的受教育者起到引導作用。博物館這一場所的資源是開放性的,其間文物保護教育的組織者并非僅限于博物館官方。受教育者是在活動中獲得有關文物保護相關體驗之人。旁觀者是教育活動直接參與者之外的人。借用維特根斯坦有關“游戲”的論述,文物保護教育的旁觀者與教育活動的直接接觸者共同參與了保護教育。
這些教育參與者使文物保護教育呈現出不同層次。文物保護從業者的工作過程,即使僅僅作為一種視覺映象,被觀眾觀察到,便具備教育意義。這種潛移默化的感官教育,是一類經驗性的傳播過程,以具有空間形態的視覺形象為傳播載體。
二、博物館文物保護教育的內容
(一)意識培養:法律與道德
對文物保護意識的培養途徑,是文物保護法律與道德的教育。文物保護是我國所有公民應盡的義務,也是社會道德對個人行為的基本要求之一。法律與道德是約束社會人的行為準則,通過強制與非強制的途徑,互相促進、轉化,維護社會秩序。
在立法方面,博物館開展文物保護法律教育,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社會普法教育,通過“博物館”這一品牌化運營,在沉浸情境內的體驗式宣傳,對不同公眾的分眾式覆蓋,大眾社交化傳播,最終形成一個“繹法空間”式的社會化普法機制[3]。
在道德教育層面,隨著公眾的民主意識、權益意識不斷提高,文物保護勢必成為公民的基本道德素質,這也是社會民主進步的重要標志[4]。文物保護法律與道德教育的目標,在于培養對文物的敬畏之心、探索之心、愛護之心,培養壯大公眾文物保護的意識。
(二)價值塑造:原則與理念
不同時代地域的人群,關于文物保護的原則與理念是存在差異的。博物館文物保護教育的文化性在于其對受教育者價值觀念的塑造,這是文化生產的一部分。
在具體的教育活動中,既需要傳播在國際上受到廣泛認同的文物保護原則與理念,又需要對本土人群固有的價值觀念進行揚棄。
我國文物保護中,基于真實性與完整性的最低限度干預原則、過程可逆原則、歷史可讀性原則、與環境統一原則、修復前后存檔原則[5]都與國際上的相關協議相統一。意大利文物保護修復理論家布蘭迪認為,所謂修復,是對藝術作品的物質性存在和其美學、歷史兩方面性質的認識,并考慮將其向未來傳承的方法論[6]。
因此,不同文化傳承對文物的認識不同。文物的保護方式更多地體現了社會的價值觀和認知判斷,隨著理論發展,文化價值、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越來越受到重視。這要求博物館的文物保護原則與理念教育,不能機械照搬國際上通行的一般性原則,要在深入了解本地文化的基礎上,進行保護原則與理念的形塑整合,引導受教育者思考、討論文物保護的價值觀念。
(三)知識提升:技術與方法
就教育活動內容而言,文物保護的具體知識,是應用于文物保護的技術與方法。文物保護知識教育的形式包含理論知識講授與實踐體驗操作兩種。
文物保護知識教育須注重實踐性,多做動手的教育活動。在普通的科普教育中,實踐體驗的目的并非是使受教育者掌握文物保護的相關技術與方法,更多的是進行意識培養與價值塑造。
在專業教育中,實踐教學是人才培養體系與培養學生動手能力和相關技能必不可少的關鍵環節[7],實踐操作能夠進一步深化理論知識的掌握水平,培養更接地氣的從業人才。
同時,文物保護知識教育應當注重傳統技藝與現代科學的結合。許多固有的文物保護修復技藝,既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也是工匠精神的體現。通過教育活動,使受教育者正確認識二者的價值與關系,有助于促進傳統修復技藝的“活態”發展與傳承、“靜態”整理與保存[8]。
三、博物館文物保護教育的意義
博物館文物保護教育以博物館為場所,完成文物保護意識、價值、知識三方面的教育,對個人、博物館、社會都具備積極意義。博物館文物保護教育中的個人身份多樣,包括從業者、教育者、受教育者、旁觀者等,人們在教育活動中完成了有關文物保護的自我展現,實現了個人價值與經驗的增長。作為機構的博物館,通過文物保護教育活動,實現了其公共文化空間的文化傳播與文化生產功能,從而營造了利于博物館文物保護發展的社會環境,形成教育與自身發展的良性循環。
在我國,個人與博物館的發展,最終將促進社會中有關文物保護的公民意識、輿論環境、價值觀念的進一步發展,為傳承發揚優秀傳統文化、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起到重要推動作用[9]。
四、結語
博物館文物保護教育受到空間屬性與要素的雙重影響,具備公共性與文化性的特質。這一類教育活動是文物保護從業者、教育者、受教育者、旁觀者在整合博物館文物資源、空間資源、人力資源的基礎上開展的。教育活動內容可分為文物保護意識培養、價值塑造、知識提升,對個人、博物館、社會均具有積極意義。
參考文獻:
[1]周根紅.博物館與城市文化的空間生產[J].東南文化,2010,(06):108-111.
[2]李海娥.基于文化空間理論的博物館旅游優化研究——以湖北省博物館為例[J].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7(02):222-226.
[3]俞靜賢,萬玲娣.社會普法教育的實踐與思考——以靜安“繹法空間”項目為中心的分析和展開[J].中國司法,2016,(08):29-35.
[4]劉敏.天津建筑遺產保護公眾參與機制與實踐研究[D].天津大學,2012.
[5]郭宏.論“不改變原狀原則”的本質意義——兼論文物保護科學的文理交叉性[J].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2004,(01):60-64。
[6]切薩萊·布蘭迪.文物修復理論[M].詹長法,田時綱譯.羅馬:意大利非洲與東方研究院,2006.
[7]張宏彥,凌雪.文化遺產實驗(實踐)教學體系的探索與建設[J].實驗室研究與探索,2012,31(08):171-174.
[8]俞蕙,劉守柔.傳統修復技藝類“非遺”項目的保護與傳承研究[J].遺產與保護研究,2017,2(03):61-67.
[9]中共國家文物局黨組.全面加強文物保護利用 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N].中國文物報,2017-03-17(001).
作者簡介:
海東平,男,回族,甘肅人,本科,研究方向:文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