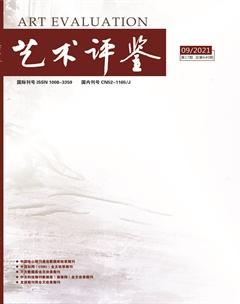關于傳統音樂文化保護與傳承的思考
龔永紅
摘要:傳統音樂保護傳承關系重大,但實踐中面臨一些困惑和分歧,一定程度影響了傳統音樂文化保護傳承工作。本文就其中關注度較高、認識分歧較大的“田野”作業、“活態”傳承、傳承主體、人才培養等問題結合重慶實際作了粗淺的思考。
關鍵詞:傳統文化? 保護? 傳承
中圖分類號:J6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359(2021)17-0001-03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戰略高度,相繼在不同場合就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創新發表了系列重要講話,將其意義提升到了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層面。傳統音樂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國家和民族對自身特性和自豪感的認同以及被世界認可的重要載體。重慶有著豐富且多樣化的傳統音樂文化遺產,是重慶人揮之不去的鄉愁。
一、關于現狀和形勢
隨著我國正式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尤其是隨著文化產業定位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文化產業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重慶積極作為,在傳統音樂文化傳承研究和實踐方面都得到長足發展,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一是搶救的速度趕不上消失的速度,很多傳統音樂品種已經滅絕,有的瀕臨滅絕,有的還等待我們去發現和發掘;二是發掘不足與過度開發的矛盾問題;三是市場化與原生態的矛盾問題;四是文化傳承后繼無人的問題等。如何站在民族文化的高度看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如何將保護和傳承重慶本土的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從人們趨于模糊或淡忘的記憶中重新拾回;如何用一些有效的手段和方法促使更多人去喜愛、掌握并發展、革新民族音樂的技能;如何將重慶傳統音樂類文化遺產體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這些都對我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二、關于“田野”作業和“活態”傳承
傳統音樂生長于田間地頭,與外面的世界相對隔絕。人們的生活方式變了,它可能還“躲”在田間地頭;莊稼人進城了,它可能仍然寂寞地“躲”在田間地頭,或許永遠不會被人發現。所以,非遺研究和保護人員應深入傳統音樂的原生環境中,開展田野調查,去捕捉原生態文化藝術的真實面貌。中國藝術研究院苑利教授將非遺研究稱為“需要用腳走出來的學問”。他認為“深入細致的田野作業,是發現新項目的重要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如“啊啦調”是重慶國家級傳統音樂非遺項目“酉陽民歌”的重要內容之一,它就是被酉陽縣文化局退休干部采風時偶然發現,從而引來政府和專家學者的研究關注,并逐漸進入非遺保護項目,并且唱上央視大舞臺,唱向國際大舞臺的。
音樂是時間的藝術。傳統民間音樂由于歷來尊崇口傳心授的傳播方式,幾乎沒有留下什么可以文字記錄的只言片語。對這個“聲響”更需要“活態”的傳承,并將與這種音樂彼此依存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一并予以全面保護,整體傳承。現實中,一些民間樂社在演出中加上電子琴、黑管等現代樂器,演出的曲目也增加了一些網紅歌曲、流行的影視歌曲等,似乎不加點流行元素就不夠“時髦”。筆者擔憂,長此以往或將加速傳統音樂文化的消亡。傳統音樂本應該更多的屬于生活,而不是舞臺,即使因為當前傳承的需要而不得不主要依靠舞臺,但最終必須回歸生活,才能從腳下的土地獲取連綿不斷的生命養分。
三、關于傳承人
音樂教育家郭乃安曾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撰文指出,“拯救聲音絕不是簡單地把錄音錄像放在博物館里,像標本那樣保護……所有外部條件對于音樂的影響力,都是通過人來實現的”。因此,必須建立完善傳承人保護制度,建立相應機制,解決傳承人的后顧之憂,使其愿意沉下心來研究和推廣傳統音樂。要為傳統音樂的表演推廣提供陣地、打造舞臺,要在全社會營造傳統音樂文化保護傳承的濃厚氛圍。
民族傳統音樂傳承人直接掌握傳統文化基因密碼,是我們當代人與祖先溝通的使者。筆者通過《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查詢,目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項目共3145項,國家級傳承人3068項;其中傳統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項目共401項,而國家級傳承人380人,平均一個項目不足一個傳承人,不僅數量少,而且年齡堪憂,基本都在七八十歲以上,每年還有不少傳承人相繼離世,相應的非遺項目隨時可能“后繼無人”。政府也在積極推動新增非遺的傳承人,但哪怕新增的傳承人也都是老年群體。據國家文旅部公開信息,2018年全國新增非遺傳承人平均年齡達63.29歲。一旦傳承人離世,年輕人又不愿接手,此項技藝將就會因此斷掉“香火”。事實上有的傳統歌種正是因為傳承人青黃不接,甚至都沒能被研究者發現和發掘,沒能納入非遺項目就走向了滅絕。
重慶市巴南區木洞鎮具有豐富的傳統音樂文化資源,其中包括木洞山歌、接龍吹打等多項國家級傳統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那里每年都會組織豐富的傳統音樂文化賽事和展演活動,還經常應邀到全國各地甚至國外展示風采。那里的黨政領導經常帶領群眾演唱山歌,營造濃厚的社會氛圍。因此,當地群眾基礎好,民間歌手多,傳統音樂文化保護傳承成效突出,早在1990年就被重慶市文化局命名為“山歌之鄉”。木洞山歌市級傳承人秦萩玥從小在濃厚的山歌氛圍中長大,對木洞山歌有著深厚感情。音樂學院畢業后,放棄了外面光鮮時尚的工作,回到家鄉,全身心投入到木洞山歌傳承事業。她最終選擇留下來,很大程度是因為從小的耳濡目染和環境熏陶。她說她忘不了老一代傳承人當時看她那種悵然若失的眼神,她無法割舍木洞山歌的情節。如今,秦萩玥把很多精力都用在了培養下一代上面。
四、關于保護和傳承的主體
提及傳統文化傳承主體,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傳承人。正如前面所述,傳承人在傳統音樂文化保護傳承中的作用至關重要,但非遺保護傳承絕對不能僅僅依靠幾個傳承人,因為責任太大,擔子太重。況且保護傳承的是本民族本地區共同的精神和文化基因,每個人都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原國家文化部副部長、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王文章曾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主體,指負有保護責任、從事保護工作的國際組織、各國政府相關機構、團體和社會有關部門及個人。它包括國際組織、國家政府、各級各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機構、社區與民眾”。傳統音樂文化的傳承保護,歸根到底,生活在當地、工作在當地的每一個人都應該是傳統音樂文化傳承的主體,而不僅僅是幾個傳承人的事情。很多人感慨傳統音樂在年輕人中“不受待見”,年輕人不喜歡傳統音樂真是他們的錯嗎?我們這些家長、教師、媒體工作者、社會工作者自己有聽傳統音樂嗎?在我們主導的這個社會氛圍里有民族音樂讓孩子們去耳濡目染嗎?氛圍的營造需要大家共同的關注、關心和參與。保護傳統音樂最好的方式就是讓它存活在百姓中間。非遺保護政策要求“見人、見物、見生活”,但連本地人都不愿意入行、不愿意參與,哪來“見人”?更不要奢談“見物、見生活”。所以,必須重新定義傳承主體,人人有責、人人參與、人人擔當,才能真正讓傳統音樂等非遺文化走進百姓生活。
在傳統音樂保護傳承的事業中,政府、學校、企業、家庭要各盡其責,誰也不能缺位。如,在重慶巴南區木洞鎮,黨委、政府主要領導親自參與木洞山歌相關活動成為傳統。其中一名黨委書記親自帶領群眾唱山歌,帶領鐵姑娘隊打石頭,修渡槽,鼓舞民間歌手們勵精圖治,傳為佳話。此外,要充分發揮社區作用,用傳統音樂文化遺產融入社區文化生態,重構民眾生活倫理關系。在重慶市政府支持下,木洞山歌非遺傳承基地于2009年6月成立。截止2018年,已經有5所學校,5個村被確立為木洞山歌傳承基地。10余年來,以木洞山歌非遺基地為依托,經常開展非遺公益課堂和公益活動,多次參加央視及各大電視臺節目錄制和文化交流展演,木洞鎮已經連續3次被評為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
從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生活的角度而言,政府主導的文化服務體系能否真正作用于民眾生活,取決于是否真正將非物質文化遺產植根于社區文化生態。傳統音樂文化來自基層、來自民眾,它本身屬于民眾,自然應該更多的服務基層、服務民眾,而不是漸行漸遠。所以,要發揮基層社區的作用,首先要讓傳統音樂文化在基層社區“活”起來、“用”起來,成為社區居民生活的一部分,在基層社區站穩腳跟。若干社區的“星星之火”連成一片,逐漸形成“燎原之勢”,這樣的“非遺”傳承基礎會更加牢靠。
五、關于傳承與開發
當前,隨著社會的飛速發展,生活方式迅速改變,傳統音樂文化原始的存在形態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傳統音樂的社會功能逐漸退化、娛神功能基本喪失,取而代之的應該是一定程度去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追求和對美的向往。傳統音樂文化在當下的功能定位必須把握準確,否則很容易迷失方向,傳統音樂將難以生存。
傳統音樂文化的開發利用也必須在把握這一功能定位基礎上進行。但何為“開發”,怎樣“開發”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目前,各地將傳統音樂文化與當地旅游資源充分結合,大興“非遺”旅游項目開發。如重慶武隆區將本地傳統民間歌舞與經典景點巧妙結合,由知名導演親手打造的大型實景歌會“印象武隆”,巧妙實現了中國傳統工藝的現代化新生和中國文化的世界化表達。其中,武隆藝術團搭檔知名歌手譚維維全新演繹的《踏歌千江》,尤其讓人耳目一新,意猶未盡。媒體評價“號子從生活喊到舞臺、從武隆喊到國外,號子富了武隆,富了村民,可謂文化、經濟雙豐收”。
但有的文化開發則完全為了迎合觀眾,為了經濟利益,將原本純粹質樸的傳統文化項目改得面目全非,甚至對觀眾造成誤導。熱鬧有了,但“文化”沒了,令人扼腕。如,有的將侗族大歌改造成美聲唱法;有的將苗族舞蹈改造成現代霹靂舞,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其實早在1995年,鞏漢林和趙麗蓉央視春晚表演的小品《如此包裝》,就通過穿著馬褂跳熱舞唱平戲的“麻辣雞絲”,對這種沒有文化的胡亂“包裝”進行了辛辣諷刺。有學者感嘆,“文化遺產”一旦綁上“商品經濟”的戰車,便會朝著利益的目標勇往直前,直至不可收拾。
六、關于人才培養
為解決非遺項目繼承人青黃不接的問題,一些地方近年實施了“非遺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組織各類非遺傳承人進行集中學習,由高等藝術院校教授進行授課。音樂方面必須統一學習美聲“科學”發聲方法,美術方面必須學習臨摹世界名畫等。這種標準化、同質化的培訓模式遭到了質疑。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陳竟毫認為,大規模培訓的方式培養非遺人才,不符合草根文化的傳承規律,像這樣的集中統一學習培訓實際“不是培訓,而是異化和改造”。事實上,一些民間歌手,經過所謂“科學發聲方法”訓練后,喪失了原有的個性和風格。從傳統和文化多樣性角度看,實際是退化了,并不是進步了。
人才培養從娃娃抓起,從青少年抓起,不僅是培養他們基本的民族傳統音樂文化知識,更要激發他們學習研究傳統音樂的興趣和責任心,要充分整合本地傳統音樂文化、傳承基地和傳承人的資源,打造好民族音樂文化學習體驗基地,逐漸輻射引導,將傳統音樂文化融入他們的生活,用濃厚的氛圍滋養他們的人生。如,重慶巴南木洞鎮小學早在1978年就將本地傳統音樂木洞山歌編成鄉土教材,納入到音樂教學內容,數十年來始終堅持著眼為木洞山歌傳承人才培養,如今,木洞山歌早已進入中學和大學課堂。
對人才培養方式而言,專業院校要俯下身子虛心向傳統音樂文化學習,而不是以西方化的標準來衡量我國傳統音樂文化的優劣,高高在上等著民間藝人前來求教。因為,就傳統音樂文化而言,所謂“專業”音樂院校可能遠不如民間藝人更“專業”。綜合性大學應開設本土民族民間音樂公共課,音樂專業院校要開設民族民間音樂專業,理順機制,打破固有的職稱、學歷等限制,聘請造詣深厚的民間藝人、非遺傳承人站上高校講臺,甚至承擔相關專業導師工作,引導師生們建立起對傳統音樂文化的榮譽感和自豪感。傳統音樂文化的課堂可以靈活設置,比如設在田間地頭、山野村莊等,既務實深入,又能激發學生的興趣。
七、結語
傳統音樂文化保護傳承工作任重道遠,在發展的道路上必將不斷出現新情況、新問題。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持續關注、關心、支持和參與傳統音樂文化的保護傳承,重拾文化自信,促進文化振興,讓中華文化滋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參考文獻:
[1]苑利.一門需要用腳走出來的學問——非物質文化遺產學田野作業的必要性與需注意的幾個問題[N].中國藝術報,2017-01-25.
[2]郭乃安.音樂學,請把目光投向人[J].中國音樂學,1991(02).
[3]韓業庭.國家級非遺傳承人新增1082人平均年齡63.29歲[N].光明日報,2018-05-17.
[4]李如海.南澗蓋瓦灑彝族“啞巴會”的傳承與保護[J],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3(03).
[5]藍雪菲.關于非物質音樂文化遺產保護的學術探討[J].音樂研究,2008(02).
[6]非遺傳承培訓爭議:標準化、同質化、去中國化[DB/OL].半月談網,2016-10-19.